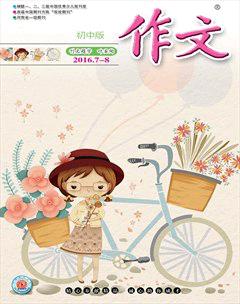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節選)
《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是村上春樹第一次寫自己的書。村上在30歲時決定做一名職業小說家,與此同時,他開始了長跑。他到世界各地參加馬拉松比賽,并將自己在跑步時的思考記錄下來,于是就有了這部隨筆集。在這本書里,村上講了自己對公平、痛苦、堅持、名譽等的看法、感悟。這本書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真實又幽默的村上,他的生活是如此簡單、自律,清晨5點起床,10點就寢,這是普通人的一天。寫作之外,他堅持運動。長久的堅持和鍛煉,提升了他的集中力和耐力,循序漸進中,日積月累中,他的身體一天天強壯,他完成了一部又一部小說,這是大作家區別于普通人的地方。村上說:“在個人的局限中,可以讓自己有效地燃燒——哪怕是一丁點兒,這便是跑步一事的本質,也是活著一事的隱喻。”生命是短暫的,與其渾渾噩噩,不如積極奔跑。奔跑時,你能感受到生命的運動,肉體的不適讓你體驗活著的感覺,體會生命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痛快。
(魏金梅)
跑步有好幾個長處。首先是不需要伙伴或對手,也不需要特別的器具和裝備,更不必特地趕赴某個特別的場所。只要有一雙適合跑步的鞋,有一條馬馬虎虎的路,就可以在興之所至時愛跑多久就跑多久。網球可不能這樣,每次都得專程趕到網球場去,還得有一個對手。游泳雖然一個人就能游,也得找一個適宜的游泳池才行。我關店歇業之后,也是為了改變生活方式,便將家搬到了千葉縣的習志野。那一帶當時還是野草茂密的鄉間,附近連一處像樣的體育設施也沒有,道路卻是齊齊整整。因為自衛隊的基地就在附近,為了方便車輛來去,道路建得很是完備。恰好我家近處有一個日本大學理工學部的操場,大清早那兒的400米跑道可以自由地(或說擅自地)使用。因此,在眾多體育項目中,我幾乎毫不猶豫地——也許是別無他選——選擇了跑步。
此外還戒了煙。每天都跑步,戒煙便是自然而然。戒煙誠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但是你沒法一邊吸煙一邊堅持跑步。“還想跑得更多”這一自然的想法,成了戒煙的重要動機,還成了克服脫癮癥狀的有效手段。戒煙,仿佛是跟從前的生活訣別的象征。
…………
開始跑步之后,有那么一段時間,我跑不了太長的距離。20分鐘,最多也就30分鐘左右,我記得,就跑這么一點點,便氣喘吁吁,幾乎窒息,心臟狂跳不已,兩腿顫顫巍巍。因為很長時間不曾做過像樣的運動,本也無奈。跑步的時候被鄰居看到,也覺得有些難為情,就和為那個偶爾加在姓名后面的、帶括號的“小說家”頭銜難為情一樣。然而堅持跑了一段時間后,身體積極地接受了跑步這事兒,與之相應,跑步的距離一點一點地增長。跑姿一類的東西也得以形成,呼吸節奏變得穩定,脈搏也安定下來了。速度與距離姑且不問,我先做到堅持每天跑步,盡量不間斷。
就這樣,跑步如同一日三餐、睡眠、家務和工作一樣,被組編進了生活循環。成了理所當然的習慣,難為情的感覺也變得淡薄了。我到體育用品商店去,買來了合用而結實的跑步鞋、便于奔跑的運動服、一塊秒表,還買了專為初練跑步的人寫的入門書,讀了。如此這般,人漸漸演變成了跑步者。
…………
已經說過,我是那種不予過問的話,什么事兒都不做也會漸漸發胖的體質。我太太卻不管吃多少(吃得不多,可一有點啥事就吃甜點心),不做運動,也根本不會變胖,連贅肉都不長。我常常尋思:“人生真是不公平啊!”一些人不努力便得不到的東西,有些人卻無須努力便唾手可得。
不過細想起來,這種生來易于肥胖的體質,或許是一種幸運。比如說,我這種人為了不增加體重,每天得劇烈地運動,留意飲食,有所節制。何等費勁的人生啊!然而倘使從不偷懶,堅持努力,代謝便可以維持在高水平,身體愈來愈健康強壯,老化恐怕也會減緩。什么都不做也不發胖的人無須留意運動和飲食。并無必要,卻去尋這種麻煩事兒做的人,為數肯定不會太多,因此這種體質的人,每每隨著年齡增長而體力日漸衰退。不著意鍛煉的話,自然而然,肌肉便會松弛,骨質便會變弱。什么才是公平,還得以長遠的眼光觀之,才能看明白。閱讀此文的讀者,也許有人抱有這樣的苦惱:“啊呀呀,一不小心體重馬上就增加……”應當動用積極正面的思考,將此視為上天賜予的好運:容易看清紅燈,就夠幸運了。不過,這么去思考問題也不容易。
這樣的觀點或許也適用于小說家的職業。天生才華橫溢的小說家,哪怕什么都不做,或者不管做什么,都能自由自在寫出小說來。就仿佛泉水從泉眼中汩汩涌出一般,文章自然噴涌而出,作品遂告完成,根本無須付出什么努力。這種人偶爾也有。遺憾的是,我并非這種類型。此言非自夸:任憑我如何在周遭苦苦尋覓,也不見泉眼的蹤影。如果不手執鋼鑿孜孜不倦地鑿開磐石,鉆出深深的孔穴,就無法抵及創作的水源。為了寫小說,非得奴役肉體、耗費時間和勞力不可。打算寫一部新作品,就必得重新一一鑿出深深的孔穴來。然而,長年累月地堅持這種生活,久而久之,就技術或體力而言,我都能相當高效地找尋到新的水源,在堅固的磐石上鑿穴鉆孔;感覺一個水源變得匱乏時,也能果決而迅疾地移到下一個去。而習慣僅僅依賴一處自然水源的人,冷不丁地這么做,只怕輕易做不來。
人生基本是不公平的。此乃不刊之論。即便身處不公之地,我以為亦可希求某種“公正”。許得費時耗力;甚或費了時耗了力,卻仍是枉然。這樣的“公平”,是否值得刻意希求,當然要靠各人自己裁量了。
我說起每天都堅持跑步,總有人表示欽佩:“你真是意志堅強啊!”得到表揚,我固然歡喜,這總比受到貶低要愜意得多。然而,并非只憑意志堅強就可以無所不能,人世不是那么單純的。老實說,我甚至覺得每天堅持跑步同意志的強弱,并沒有太大的關聯。我能夠堅持跑步20年,恐怕還是因為跑步合乎我的性情,至少“不覺得那么痛苦”。人生來如此:喜歡的事兒自然可以堅持下去,不喜歡的事兒怎么也堅持不了。意志之類,恐怕也與“堅持”有一丁點瓜葛。然而無論何等意志堅強的人,何等爭強好勝的人,不喜歡的事情終究做不到持之以恒;做到了,也對身體不利。

所以,我從來沒有向周遭的人推薦過跑步。“跑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大家一起來跑步吧”之類的話,我極力不說出口。對長跑感興趣的人,你就是不聞不問,他也會主動開始跑步;如若不感興趣,縱使你勸得口燥舌干,也是毫無用處。馬拉松并非萬人咸宜的運動,就好比小說家并非萬人咸宜的職業。我也非經人勸說、受人招聘而成為小說家的(遭人阻止的情況倒是有),而是心有所思,自愿當了小說家。同理,人們不會因為別人勸告而成為跑步者,而是自然地成為的。
話雖如此,也許真有人讀了這篇文章,陡然來了興趣:“好啊,我也跑它一跑試試。”當真練起跑步來。“呵呵。這不挺好玩兒嗎?”這當然是不錯的結果。果真發生了這等事,作為本書的作者,我也非常高興。然而每個人都有對路與不對路之事。既有人適合馬拉松,也有人適合高爾夫,還有人適合賭博。看見學校上體育課時,讓全體學生都練長跑的光景,我便深感同情:“好可憐啊。”那些絲毫不想跑步的人,抑或體質不適合跑步的人,不分青紅皂白讓他們統統去跑長跑,這是何等無意義的拷問。我很想發出忠告:趁著還沒有出現問題,趕快取消讓初中生和高中生一律跑長跑的做法。當然,我這樣的人出面說這種話,肯定無人理會。學校就是這樣一種地方:在學校里,我們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最重要的東西在學校里學不到”這一真理。
任怎么說長跑和自己的性情相符,也有這樣的日子。“今天覺得身體好沉重啊。不想跑步啦。”經常有類似的日子。這時候便尋找出形形色色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想休息,不想跑了。我曾經采訪過奧運會長跑選手瀨古利彥,在他退役就任S&B隊教練后不久。當時我問道:“瀨古君這樣高水準的長跑選手,會不會也有今天不想跑啦、覺得煩啦、想待在家里睡覺這類情形呢?”瀨古君正所謂怒目圓睜,然后用了類似“這人怎么問出這種傻問題來”的語氣回答:“那還用問!這種事情經常發生。”
如今反思起來,我覺得這確是愚問。當時,我也明白。然而,還是想聽到他親口回答。即便膂力、運動量、動機皆有天壤之別,我還是很想知道清晨早早起床、系慢跑鞋鞋帶時,他是否和我有相同的想法。瀨古君的回答讓我從心底感到松了口氣。啊哈,大家果然都是一樣的。
請允許我說一點私事。覺得“今天不想跑步”的時候,我經常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你大體作為一個小說家在生活,可以在喜歡的時間一個人待在家里工作,既不需早起晚歸擠在滿員電車里受罪,也不需出席無聊的會議。這不是很幸運的事兒么?與之相比,不就是在附近跑上一個小時么,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腦海里浮現出滿員電車和會議的光景,再度鼓舞起士氣,我就能重新系好慢跑鞋的鞋帶,較為順利地跑將出去。“是啊,連這么一丁點事兒也不肯做,可要遭天罰呀。”話雖然這么說,其實心中有數:甚多的人,認為與其每天跑一個小時,還不如乘著擁擠不堪的電車去開會。
閑話休提。我就這樣開始了跑步。33歲,是我當時的年齡,還足夠年輕,但不能說是“青年”了。這是耶穌死去的年齡,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凋零從這個年紀就開始了。這也許是人生的一個分水嶺。在這樣的年齡,我開始了長跑者的生涯,并且正式站在了小說家的出發點上——雖然為時已晚。
(摘自村上春樹《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稍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