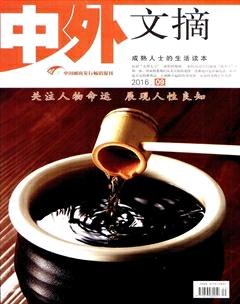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演講
阿列克謝耶維奇 呂寧思

福樓拜稱自己是人們的筆;我會說,我是人們的耳朵。當我走在街上,記錄下聽到的各種詞匯、短語和感嘆時,我都會在想:有多少小說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消失了啊!消失在黑暗中。人們還不能捕捉生活中的對話,把它作為文學記錄下來,因為我們不懂得去欣賞這些對話,也不會因為讀它們而感到驚訝或者快樂。但它們卻讓我著迷,甚至俘虜我。我喜歡人們交談的方式,我喜歡寂寞的人聲。這是我最大的愛好和激情。
通往領獎臺的路很長,幾乎有四十年那么長——經過一個又一個的人,一個又一個的聲音。說實話,我沒有力量一直堅持走下去——很多次,人們讓我震驚,讓我恐懼。我體會過狂喜和厭惡,我也曾想忘記聽到的東西,回到無知的狀態。然而,我也一次又一次看到了人的美好,為此喜極而泣。
我相信,人們本來多可以過上不一樣的生活,但他們還是選擇了蘇聯生活。為什么?我很長一段時間搜索了這個問題的答案,我跑遍了前蘇聯的各個國家,并錄了幾千盒磁帶。這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它就是我們的生活。我一點點地回顧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回顧它對人的影響。我發現人類其實是很小的概念,尤其具體到我們每一個人。但在現實中,人使得一切都有可能發生。
令我感到困擾的是,真實不是存在于一顆心靈、一個頭腦中的,真實在某種程度上破碎了。有很多種真實,而且各不相同,分散在世界各地。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人類對自己的了解,遠遠多于文學中記錄的。那么我在做的是什么?我收集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思考和話語。我收集我所處時代的生活。我對靈魂的歷史感興趣——日常生活中的靈魂,被宏大的歷史敘述忽略或看不上的那些東西。我致力于缺失的歷史。
經常有人說,我寫的不是文學,是文獻。今天,文學是什么?誰能回答?我們生活的節奏空前地快。內容打破了形式,也改變了形式。一切東西都在超出了原有的邊界:音樂、繪畫,甚至文獻中的語言也在逃離原本的邊界。在真實和虛構之間沒有界限,它們相互流動。見證者不是中立的。講故事時,人們會進行加工創造。他們與時間角力,他們是演員,也是創作者。
我對小人物感興趣。我認為他們是渺小卻偉大的人物,因為痛苦能塑造人。在我的書中,他們講述自己的歷史.更宏大的歷史也從中顯現。我們沒有時間來理解已經發生以及正在發生的事情,但是我們需要說出來。首先,我們需要清楚地表達出來。(但)我們害怕這樣做,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我們的過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中,沙托夫一開始就對斯塔夫羅金說:“在無限無窮的世界里,我們是最后一次相遇的兩個生物……別用那種腔調,像個人一樣說話吧。至少,用人的聲音說一次話。”
我和我的主角們差不多也是這樣對話的。人們從自己的時代發聲,但人類的心靈是難以抵達的,這條路被電視、報紙以及這個世紀的迷信、偏見、謊言阻隔。
我得承認,我也不是突然間就獲得了自由。我真誠地對待我的受訪者,他們也信任我。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通向自由的一條路。當我從阿富汗返回,我不再抱任何幻想。
許多人從阿富汗回來,就獲得了自由。但也有特例。那時在阿富汗,一個年輕人教訓我:“你是個女人,你懂什么戰爭?你以為成千上萬的人是怎么死的,和書里和電影里一樣?昨天我朋友被殺了,他腦袋中槍,然后還跑了幾米,想去接住被打出來的腦子……”七年后,同樣是這個人,已經成了一個成功的商人,喜歡四處講阿富汗的故事。他說我:“你干嗎把書寫成那樣?太嚇人了。”他變了,不再是以前我在死人堆里遇到的、二十歲的怕死的年輕人了……
我有三個家:我的白俄羅斯祖國,它是我父親的祖國,我一輩子都生活在這里;烏克蘭,我母親的祖國,我出生在那里;以及俄羅斯的偉大文化,沒有它,我無法想象現在的自己。這些對我都很寶貴,但是在今天,已經很難再談論愛了。
(摘自《中國青年》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