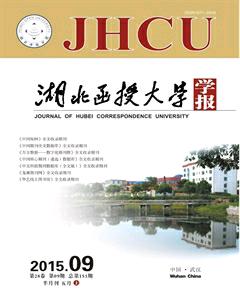善為意外之舉的劉半農
佚名

魯迅在評價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時,曾專門比較過陳獨秀、胡適和劉半農,說道:“如果將韜略比作武器倉庫的話,陳獨秀的風格是倉庫門大開,里面放著幾支槍幾把刀,讓別人看得清清楚楚,外面則豎一面大旗,旗上寫著:‘內皆武器,來者小心!胡適的做法,是庫門緊關,門上貼一張小紙條,說:‘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兩位都是高人,一般人見了,望而生畏,不上前。可劉半農沒有什么韜略,他沒有武庫,就赤條條的一個人,沖鋒陷陣,愣頭愣腦。所以,陳、胡二位,讓人佩服,劉半農卻讓人感到親近。”
劉半農就是這樣一個人,愣頭愣腦,整個人生都沒有規劃,時不時讓你大吃一驚,但吃驚過后,卻又為他的“意外之舉”大為折服。
劉半農出生于江蘇江陰縣一個教師家庭,自幼聰明絕頂,在小學和中學都是屢創紀錄的超級學霸,正當所有人都認為他將順利考取北大、清華時,他卻選擇了退學,一個人跑到上海去謀生路。
在上海,劉半農找了一份編輯的工作,并開始大量地創作小說,不過千萬別以為這位學霸是想實現文學的夢想,其實他寫的都是些不入流的艷情小說、消遣小說,目的無非是為了多賺稿費。
幾年后,報社停業整頓,劉半農的編輯工作也走到了盡頭,只得回老家。沒有了收入,一家人過得非常艱難。然而,就在這時,老天爺卻扔下了一塊天大的餡餅——北大校長蔡元培竟然給他寄來了教授的聘書!這個大餡餅砸得劉半農半天緩不過勁兒來,不過這就是事實,一個中學還沒畢業的寫艷情小說的人,竟然當上了北大的教授!
老劉的人生夠出人意料了吧?別急,這才剛開始呢!
在北大,劉半農迅速從一個艷情小說作者,變成了一個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當時,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剛嶄露頭角,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第一塊陣地,劉半農為了更徹底地打擊復古守舊派,就找到好友錢玄同,跟他說了自己的計劃。
錢玄同也是出了名的急先鋒,一聽老劉的計劃,立刻同意了。于是,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發表了一篇署名“王敬軒”的文章:《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以一個守舊派衛道士的身份,對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大肆辱罵。而在同一期,還有一篇文章,名為《復王敬軒書》,署名“本社記者半農”,對王敬軒的觀點進行了痛快淋漓的批判。
其實這位“王敬軒”,就是錢玄同,故意跟劉半農一唱一和,將守舊派衛道士的丑陋嘴臉展現得淋漓盡致,同時也將新文化運動的先進性襯托得無比偉大。
這兩篇文章,迅速成了導火索,點燃了舊派與新派的一場驚天動地的大論戰,其首功,無疑應屬劉半農。蘇雪林曾說:“(劉半農)雖不足與陳、胡方駕,卻可與二周并驅。事實上,他對新文學所盡的氣力,比之魯迅兄弟只有多,不會少。”
然而,就在劉半農在北大聲名鵲起,以“中學肄業的大學教授”的身份成為傳奇人物的時候,他卻再一次出人意料,選擇了出國留學,要考一個響當當的博士學位回來。
當時,歐洲剛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蕭條,劉半農在巴黎的生活極為拮據,經常吃不上飯,頭發也沒錢理,長得像個野人,連同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都看不下去了,罵他為中國人丟臉。但劉半農生性灑脫,絲毫不以為忤,還把住的地方起名叫“花子窩”。有一次趙元任夫婦去看他,想拍張合影,劉半農竟然讓大家坐在地上扮乞丐,伸著手作乞討的樣子,讓趙元任哭笑不得。
在英國倫敦留學時,劉半農還寫過一首歌,叫《教我如何不想她》,被趙元任譜上了曲子,迅速成為流行歌曲,影響極大。值得一提的是,“她”這個字也是劉半農首創的,原本漢字中沒有表示女性的第三人稱,到了清末民初,通常用“伊”來表示,劉半農便專門造了個“她”字,還有表示物的“它”,一直沿用至今。
這首歌在當時極為流行,很多女生都以為詞作者是一位風度翩翩的佳公子,對他很是崇拜,然而等見到了本人,卻是又黑又土的一個半老頭子,都極為失望。劉半農聽說后,風趣地寫了一首打油詩:“教我如何不想他,請來共飲一杯茶。原來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