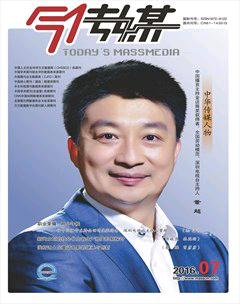視覺傳播時代圖像的呈現方式及符號化功能
吳雨霜?
摘 要:文字是人類傳播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文字都占據著傳播的中心地位。但隨著互聯網和攝影技術的革新,圖片開始擠壓文字的地位。在“無圖無真相”的感性網絡空間,圖片的作用越發凸顯,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圖片的情感引導功能甚至直接影響事件的走向。悲情、戲謔、憤怒的傳遞依賴于圖片作為符號的特性。本文通過對網絡事件中圖像的符號化分析,發現觀者對悲情的一致解讀更容易平息,在呈現方式上,圖像使用隱喻表現悲情,使用轉喻升華事件,具有知點和不穿透的刺點,能夠最大程度引導觀者情緒。
關鍵詞:圖片;符號;視覺傳播;情感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07-0018-03
一、研究緣起與文獻綜述
新媒體時代,是一個碎片化傳播時代,短、平、快是其內容消費的主要法則。圖片容易理解,適合分享,吸引眼球,在海量信息不斷更迭的網絡空間,能更大程度抓住需要強烈感官刺激的受眾。尤其是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圖片往往能成為事件發展的轉折點,甚至成為一個事件的符號和記憶。早在1998年,楊小彥、鐘健夫等為《紅風車經典漫畫從書》作序時就引入“讀圖時代”這一概念[1]。如今,圖像已經成為了日常司空見慣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有圖有真相”成為觀者的共同追求,這意味著我們已經進入“讀圖時代”。
圖像不斷壓縮文字的空間,在廣告、雜志甚至新聞中,占據重要位置,也滋生了許多問題。在商業利益、個人企圖等因素的驅動下,圖像可以通過被裁剪、PS等方式,強化弱勢群體、激化矛盾,操控受眾的情感,導致圖片傳播的亂象。由于圖像承載的信息有限,曲解帶來的極端情感極易掩蓋對事件來龍去脈的關注,“有圖無真相”的現象層出不窮。很多圖片甚至直接呈現血腥、暴力、色情等,單純追求視覺刺激,缺乏人文關懷。情感是影響圖像傳播的重要因素。偏激的情感帶來圖像傳播的亂像,而合理的情感承載,將對公共事件的發展產生重要意義。
“我們這個世紀的浮沉變遷是由幾張劃時代的經典照片總結出來的。[3]”西方很早便意識到圖像的重要性,并率先將符號學運用到圖像研究中。近年來,我國將符號學運用于圖片的研究,涉及美術、新聞傳播、哲學等多個領域。
吳瓊認為巴爾特的圖像零度本質上是死亡詩學的一個另樣表述[4]。陳力丹、王亦高則從柏拉圖的摹仿理論著手,提出圖文關系的總趨勢應是圖像與文字各自的符號價值,從被遮蔽逐漸走向被彰顯;圖與文的關系,從必然一致可能走向相互抵觸[5]。鄧尚將符號學引入對美術圖像的研究中,一方面圖像符號化的解讀幫助接受者理解美術作品,使其由精英化走向大眾化;另一方面卻使接受者容易滿足于符號所表征的意義,疏于對作品本身的重視,美術創作呈現符號化、扁平化傾向[6]。而在新聞圖片方面,李瑋、蔣曉麗將羅蘭·巴爾特的意指實踐與隱喻、轉喻等符號修辭所建立起來的涵指、元語言、神話等不同意指方式,引入到新聞圖片的意指分析中,并認為這是一種必然趨勢[7]。韓叢耀認為,新聞圖片的修辭手法主要有象征、隱喻、譬喻[8]。
目前,符號學在圖像研究中的應用,主要集中在對圖文關系的探討,對新聞、美術等其他領域圖像的符號意義研究,但較少關注圖像的符號化功能——對情感的引導。網絡是情感宣泄的平臺,是感性的凝聚地,網絡事件也更多遵循情感動員邏輯,憤怒 、悲情、戲謔等情感已成為其發展的重要線索[9]。因此,不應忽視情感引導對網絡公共事件的影響。身處“讀圖時代”的觀者對圖像的接受度已經超越文字,在理性引導的基礎上,如何通過圖像的符號化功能實現對情感的引導,將為網絡公共事件的治理帶來新的啟示。
二、圖像的隱喻、明示意和轉喻呈現及效果
20世紀30年代,海德格爾認為,“視覺圖像時代”是世界進入現代的本質。如今,我們正處于一個圖像生產、流通和消費急劇膨脹的“非常時期”,處于一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圖像資源富裕乃至“過剩”的時期[9]。互聯網誕生后,圖片的傳播更加便捷,網民碎片化的閱讀習慣,成就了圖像在傳播中的地位。
網民在網絡公共事件中表現出的三種主要情緒悲情、戲謔與憤怒則是圖像在網絡傳播中承載的主要情感。高度一致的戲謔可能導致“全民狂歡”,同仇敵愾的憤怒可能導致線下公共事件的爆發。相較而言,悲情是人們不愿再度體驗的情感,因此,只有集體悲情可能會隨時間逐漸平息。
2015年11月8日,沈陽遭遇6級嚴重霧霾污染,8日晚間,一張圖片開始在微信朋友圈迅速傳播,濃濃霧霾中只能看見5個孤零零的霓虹燈大字“東北餃子王”,被網友們調侃為“天空飄來五個字”。戲謔是網絡中常見的情感,也是極易擴散,引起共鳴的情緒。11月9日,有關“天空飄來五個字”的微博熱議已過七千。10日,對該事件的戲謔和關注度逐漸減少,但到11月12日,“天空飄來五個字”再掀高潮。而此次引起關注的是一張類似的圖片,遠處的建筑物完全被霧霾遮擋,只剩下“國賀大飯店”五個紅字。此次戲謔引發的微博關注甚至超過了8日那張照片的關注量。與悲情相比,戲謔容易衍生出新的狂歡點,一旦遭遇刺激,就會再次引發熱議,出現反復不息的現象。
網絡是情感的宣泄地,網民的憤怒常常導致攻擊、謾罵等不良網絡行為,甚至引發線下社會運動。法國雜志《查理周刊》則因為刊登與伊斯蘭教及先知穆罕默德相關的諷刺漫畫,遭到武裝襲擊。不斷累積的一致憤怒可能為媒體、社會帶來禍端。
由于三種情感自身的特性,圖像承載不同的情感直接影響情感引導的效果。如果圖像主要渲染戲謔、憤怒,則不易控制事件走向,甚至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而悲情是人們不愿再度提起和經歷的情感,隨著時間的推移,集體悲情會逐漸消解,歸于平靜。
1.圖片呈現的隱喻與明示意
(1)隱喻。符號學興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但索緒爾、皮爾斯兩位符號學先驅并未將注意力集中在視覺層面的符號學研究。符號學家羅蘭·巴爾特卻將視野擴展到攝影、繪畫、電影等,他認為,這些都是一種言談,因此也屬于符號學范疇。羅蘭·巴爾特提出符號含有兩個層次的表意系統。索緒爾的“能指+所指=符號”只是表意的第一個層次,而將這個層次的符號又做為第二層表意系統的能指時,就會產生一個新的所指。巴爾特把他稱作內蘊意義,也叫隱喻[10]。雅各布森和霍爾認為,隱喻和轉喻確定了訊息發揮其指稱功能的根本方式。隱喻使用熟悉的詞匯表達不熟悉的內容,并同時利用二者之間的相似和相異之處[11]。隱喻如同遮擋在圖像前的薄紗,使直白的圖像多了婉約,也適當減緩了圖像對心靈的沖擊。
2015年6月1日晚21點30分左右,從屬于重慶東方輪船公司的“東方之星”由南京駛往重慶途中,突遇龍卷風在長江中游湖北監利水域翻沉。事故發生后,網民們對事故原因、責任人、救援不力等質疑聲此起彼伏,引發熱烈的討論。直至6月5日晚19點39分,《長江日報》記者陳卓在《長江日報》官方微博上發布了用手機拍攝了船體扶正的現場照片,引發大量的轉載和評論,網民情緒幾乎一致的急轉悲傷、哀悼。灰暗主色調的圖像中,一抹溫暖的夕陽,迅速抓住了觀者的眼球。
《說文解字》中“夕,莫也”,意思是傍晚或黃昏,與晨相對。早在唐代,詩人李商隱便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名句。以夕陽喻老人遲暮,古已有之。“夕陽”與“老人”都具有即將逝去的特點,因而可以被歸入同一詞匯域。而照片中,夕陽正好在扶正的船體上方,使人聯想起此次“東方之星”翻沉事件中,乘客多是老人,更生悲涼。照片沒有表現慘烈的現場,而是通過一抹夕陽將刺痛的悲傷變得柔和。
圖像本是直接了當的機械化再現,隱喻卻軟化了刺激直白的情感。朝陽是剛經歷美好時光的青少年;蠟燭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老師;梅是抗衡風雪的傲骨;菊是遠居深山的淡雅……隱喻承載的情感婉約,不易滋生憤怒、戲謔,更能形成平穩的一致性解讀。
(2)明示意。羅蘭·巴爾特認為在照片中,明示意和隱含意的差別是清楚的,明示意是相機所指向的物體在膠片中的機械性再現,隱含意則是這一過程中人為的部分[11]。
2015年8月12日晚,天津濱海新區危險品倉庫發生爆炸。事件發生后,網絡上媒體不報道、政府不作為的質疑聲不間斷。8月22日,新浪微博平臺頭條新聞報道了消防員甄宇航犧牲前致電母親的消息,并配有兩張圖片。一張是家人為已逝甄宇航過生日的圖片。另一張是寫著甄宇航基本信息的半身黑白照。照片發布后,引發大量的評論轉載。本文從中抽取1000條評論研究網民的情感傾向發現,表示憤怒,要求追責的網友竟占15.9%,甚至有網友直指媒體過度煽情。以明示意和隱含意來衡量,消防員犧牲的這兩張圖片中情感的呈現屬于明示意。
黑白的半身遺照、親人們悲痛的表情,直擊人心,情感傳達準確。本該充滿喜悅的生日現場,卻是哭泣的臉龐,強烈的反差更顯悲情。圖像通過場景的機械化再現,將悲傷赤裸裸的擺在觀者面前,減少了需要通過文化解讀的環節,使觀者感受到的情緒更加深刻、震撼。
明示意是照片中常用的表現方式,照片中人物的面部表情直接反映了照片傳遞的情緒。 笑臉代表喜悅、眼淚代表悲傷,雙目圓瞪代表憤怒……在網絡塑造的虛擬環境中,網民的情緒急躁而易波動,圖片直接將情感呈現在觀者面前,可能滋生憤怒、戲謔等不易控制的情緒,媒體也易陷入“為煽情而煽情”的指責中。“東方之星”翻沉事件與天津濱海區爆炸事件都是意外發生的安全事故,且發生時間相近,具有類似的網民基礎,但正是由于圖像的呈現方式不同,使得兩個事件在情緒引導方面出現了較大的差異。對比而言,帶有隱喻的圖像承載的情感較為委婉,更容易形成接受式解讀。
2.圖片呈現的轉喻
費斯克認為在視覺語言中較少使用隱喻,多使用轉喻[11]。轉喻是將同一層面的不同意義聯系起來,其基本定義是以部分代替整體。圖片承載的信息是有限的,卻能通過轉喻使傳遞的內容不局限于圖片。
2015年9月2日,3歲的敘利亞小男孩艾蘭的尸體被沖到土耳其的一處沙灘的照片在Facebook、twitter、新浪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掀起輿論高潮。艾蘭和家人為躲避國內戰亂偷渡歐洲,卻不幸遭遇沉船事故,全家四口僅父親存活下來。艾蘭尸體的照片發布后,“被沖上海灘的人性”成為世界探討的話題。不僅如此,德國、英國、法國、奧地利等國家紛紛就此事發聲,國際社會對難民的態度和政策也因此發生改變。照片中,身著紅色T恤和黑色短褲的艾蘭,頭朝下躺在沙灘上,好像陷入沉睡。國內戰亂,加之國際對難民接納制度的缺陷使年幼的艾蘭失去生命。這不僅是艾蘭這個家庭的悲哀,也是和艾蘭一樣,經歷戰爭的所有難民的悲哀。照片以艾蘭的可憐轉喻所有經歷戰爭的難民的不堪處境,將嚴肅的社會問題寄予照片中,最終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
轉喻通過對有限的局部的呈現,引發觀看者的聯想。整齊的閱兵隊伍代表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大;一位災民的困難轉喻所有受災者的困境;一個家庭的“喪子之痛”預示著多個具有同樣經歷的家庭的傷痛。轉喻將事件放于凸透鏡下,因此,被轉喻的部分承載的情感至關重要。由于轉喻以部分代替整體的特點,一幅涉及官、富、警的負面照片無形中會使受眾對整個群體產生偏見,轉喻呈現的極端情感會激化矛盾,將事件推向不可控的方向。而圖像轉喻正能量有利于觀者負面情緒的安撫。
三、圖片的刺點(punctum)和知點(studium)呈現及效果
羅蘭·巴爾特對圖像符號的研究沒有間斷,1980年,巴爾特在《明室——攝影縱橫談》中提出刺點(punctum)和知點(studium)的概念,認為知點是照片呈現的不好不壞的“中間”情感,所調動的是“半個欲望”。刺點是創傷,仿佛是帶尖的工具造成的印記。羅蘭·巴爾特認為,“只要不被吸引我或傷害我的細節(punctum)穿透、刺激和留下斑痕,studium可以造就一類傳播廣泛(世界上傳播得最為廣泛的)的照片,也即單向的照片。[12]”
1.知點
知點從屬于文化,是創作者和消費者簽訂的一種契約。圖片承載的情感要最大限度地被接受和傳播,離不開知點。觀者要辨認知點,就注定要觸及攝影師的意圖,要和攝影師的意圖保持一致,不管是贊成還是不贊成這些意圖,對這些意圖都要了解,并加以思考[12]。對攝影者的意圖和照片知點的理解,則建立在觀看者與攝影者類似的文化背景上。
男女爭斗,女方更容易博得同情。城管與小販的推搡,則多是城管打小販,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欺壓,政府部門對勞動人民的“隨意宰割”。“官二代”、“富二代”桀驁不馴、揮金如土……都是文化和經驗的一致性使觀者達成的共同認識。12月4日,退休老人畢國昌在三亞海邊游泳時,自行車及車上衣物因違停被城管收走。事件發生后,畢國昌身穿泳褲,脖子上套著游泳圈的照片被媒體公布。畢國昌窘迫的樣子加上觀者對城管的集體記憶,瞬間激起網民對城管的譴責與打壓,事件本身的來龍去脈被網民忽視。
知點是一種教育,它使觀者認出攝影師,體驗推動攝影師拍攝并成為其拍攝活動的基本意圖。帶有知點的圖片能夠引起廣泛的興趣,但要知點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則依賴拍攝者和觀看者類似的經驗和文化背景建構的一致的解讀框架。處于不同環境的拍攝者和觀看者,在意圖的理解上則可能出現偏差,難以實現傳播目的。
2.刺點
刺點往往是細節,另照片有生氣。它可能不是拍攝者有意為之,但卻引起觀看者的注意。因此,刺點是因人而異的,偶然的,有時甚至是低俗的。圖片會因為知點引起觀者的興趣,卻會因為刺點被人記起。但并不是圖像的刺點越強越利于情感的傳播,過度的刺點會穿透觀者的情感和心靈,激起觀者的極端情緒。因此,圖像的廣泛傳播除了依賴知點,還依賴于能最大化刺痛觀看者卻不穿透他們的刺點。
10月14日,《新安晚報》官方微博上發布了9月1日一位利辛女子為救女孩,被狗咬至重傷的消息并配有女子的病床照。照片中,被咬女子下半身纏滿繃帶,床邊還有濃重的藥漬和血跡,雖然傷情最嚴重的部分打了馬賽克,但是從手臂上密布的血痂推斷,女子傷情嚴重。斑斑的血跡,觸目驚心的傷口,對觀者造成了強烈的心理刺激。引起網民的極大同情,并強烈譴責獲救女孩和咬人的狗。截至21日,被咬女子已收到募捐超過80萬元。然而,10月19日,這則消息被曝是女子丈夫因無錢醫治制造的謊言,并不存在救人一事。21日對事件的討論和譴責達到頂峰。
照片通過女子傷情的直接呈現對觀者造成心理沖擊,并形成穿透,讓觀者陷入極端的情感中,失去判斷力,失去對事件真相的追溯。血腥的災難照片、暴力的街頭鬧事等圖片都能極大滿足觀者的獵奇心理,這樣具有穿透刺點的照片雖然容易被記住,但也會激起憤怒等極端情緒。“東方之星”船體扶正照片中,沒有能直接穿透觀看者的刺點,艾蘭照片中的元素也都較為柔和的,因此,照片取得廣泛傳播的同時,對網民情緒有一定的安撫作用。
四、結 論
由于互聯網和互聯網使用群體的特性,情感在網絡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無圖無真相”的視覺傳播時代,直接、準確、沖擊力強的圖片更是加速公眾的情緒感染。悲情、戲謔、憤怒三種主要的網絡情緒中,悲情是觀者不愿再次經歷的情緒,因此,集體悲情會逐漸被時間消解。選擇悲情作為圖像承載的主要情感利于網民的情緒引導。
與明示的悲情相比,利用隱喻含蓄的表達悲情的圖片,不易滋生憤怒、戲謔等其他圖像沒有意圖傳達的情緒。轉喻是情感渲染的重要環節,轉喻放大正能量則能安撫觀者情緒,放大極端情緒,則激化矛盾,進一步引發情感宣泄。知點是圖像引起觀者興趣的文化要素,刺點是刺痛觀者的細節,只有知點和不穿透的刺點的結合,才能最大程度發揮圖片引導情感的功能。因此,在圖片的呈現方式上,使用隱喻表現悲情,使用轉喻升華事件,同時具有知點和不穿透的刺點,能最大程度發揮圖片的情感傳播功能,對網民情緒的消解產生一定作用。
參考文獻:
[1] 湯天明.讀圖時代研究[D].南京師范大學,2005.
[2] 張浩達.視覺傳播:信息,認知,讀解[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3] Martine Joly:Limage et les signes—Approche sémiologique de limage fixe[M],paris:Nathan,2002.
[4] 吳瓊.圖像的零度:羅蘭·巴爾特的圖像閱讀[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4).
[5] 陳力丹,王亦高.論圖文關系的歷史變遷——以柏拉圖式的圖文觀為先導[J].現代傳播,2008(4).
[6] 鄧尚.基于符號學語境下的美術傳播思考[J].現代傳播,2014(3).
[7] 李瑋,蔣曉麗.論新聞圖片的符號修辭與意指實踐——試引入一種新聞圖片的符號學分析方法[J].新聞界,2013(22).
[8] 韓叢耀.圖像:一種后符號學的再發現[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9] 郭小安.網絡抗爭中謠言的情感動員:策略與劇目[J].國際新聞界,2013 (12).
[10] 周憲.視覺文化的轉向[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5).
[11] 余志鴻.傳播符號學[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
[12] 約翰·費斯克.傳播研究導論:過程與符號[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3] (法)羅蘭·巴爾特著,克非譯.明室:攝影縱橫談[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
[責任編輯:思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