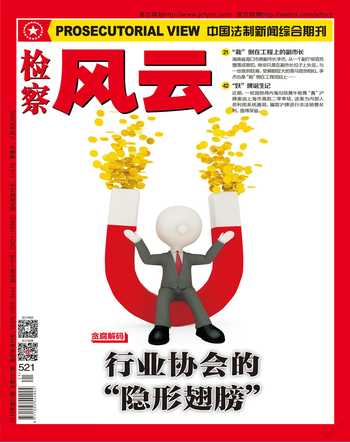摸魚兒
吳秉衡
但凡對宋詞有些了解的讀者,想必不會(huì)眼生于《摸魚兒》這詞牌兒。就著字面,《摸魚兒》嘻嘻嚷嚷地透著股天真爛漫的野趣。城里常有的憂愁煩惱與它是夠不著邊的。然而,這無憂無慮的景致不過是詞牌自身的意境罷了。無論是辛幼安筆下的“更能消幾番風(fēng)雨”,還是元遺山紙上的“問世間情是何物”,當(dāng)《摸魚兒》與騷客相遇時(shí),漁人的歡聲笑語隨之換作文士胸中的“煙柳斷腸”、“暗啼風(fēng)雨”,多少有些矯情,有點(diǎn)兒酸。
雖不喜詞人們借著《摸魚兒》的格律填的那些個(gè)酸曲兒,但我依然樂見那詞牌本初的意境。尤其是在驕陽似火的夏日午后,耳邊播放著《漁舟唱晚》,心中念想著“遠(yuǎn)浦歸帆”,“落花水香茅舍”倒也不遠(yuǎn)。當(dāng)然,此時(shí)手中若是能盤玩上一件舊物,更是樁寧神養(yǎng)心的消夏美事。筆者就恰好有件兒撫之能生涼意的明代龍泉窯瓷鯉可為依賴。
說起那瓷鯉,筆者與它結(jié)緣雖也有些日子了,但每次把玩仍是愛不釋手。這條魚兒不僅釉水青翠欲滴,而且造型也是惟妙惟肖——其口、眼、鱗、鰭、尾準(zhǔn)確到位、活靈活現(xiàn)。若將它放置在玻璃魚缸中,再擺好水草兌上水,立馬栩栩如生。由是可見,制作它的匠人那手藝得有多么厲害。筆者當(dāng)初寧可虧欠荷包,也要堅(jiān)持將之收入囊中,正是傾倒于其神韻所致。畢竟,此等文玩到底是識(shí)貨藏家的心頭好!
孟夫子曾曰:“獨(dú)樂樂不如眾樂樂。”這句古時(shí)圣賢隨口一說的箴言放在今日收藏領(lǐng)域,一樣可以讓今人受用,而且不少知識(shí)也常在不經(jīng)意間,于“眾樂樂”中得到了普及,找到了自身流傳的通途。
那一回,日頭已開始灼人,筆者攜自珍備至的瓷鯉來到滬上多寶古玩城與同好交流心得。席間,某位資歷頗深的古董商在上手過后,笑呵呵地問大家:“你們誰知道這條鯉魚是公還是母?”他這一問頓令大家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就在眾人還沒回過神兒的當(dāng)口,那行家卻已老神在在地揭示了答案:“這可是條從明朝游下來的雄鯉魚。”有人忍不住質(zhì)疑道:“你是咋看出來的?”“因?yàn)槲以?jīng)在老家鄉(xiāng)下跟著親戚養(yǎng)過一年魚。”行家不緊不慢地言道,“那時(shí)候,我們養(yǎng)過也進(jìn)過不少鯉魚,一般都揀雌魚,不要雄魚,為的是能多下小魚回本,所以我能一眼從魚鰭上分辨出公母。”聽罷,大家毫不吝嗇地紛紛向他蹺起了大拇哥。“別急,我還有話要說,”行家抿了口水繼續(xù)說下去,“這件瓷鯉應(yīng)該是當(dāng)初一套瓷器中的一件;我估摸著兒,還有條雌鯉和些個(gè)兒小鯉魚。不過即便如此,能有眼前的這一條也夠難得的了,畢竟現(xiàn)在貨不好收,遇到就遇到,遇不到也就遇不到了。”聽完這番話,眾人更加欽佩其眼力。至于筆者,還多了份兒開心——自己從那行家的經(jīng)驗(yàn)里學(xué)到了新知識(shí),焉能不樂?
自打回來后,筆者又把玩了那瓷鯉好幾回,越發(fā)地喜歡它。尤其是三伏時(shí)節(jié),開著空調(diào)、喝著冷飲、聽著絲竹,看看掌中魚、想想當(dāng)日事,不禁莞爾——真可謂“此時(shí)身自得,難更與人同”。這份閑適、這份愜意,想來也只有藏家才能體會(huì)。
編輯: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