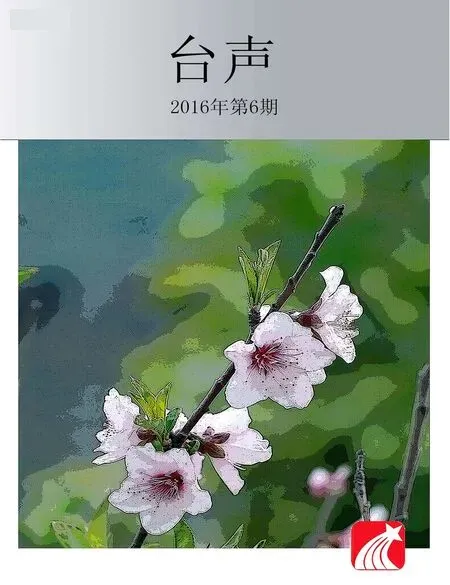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劉奕伶看大陸要零距離的“登陸”體驗
作者丨記者 程朔 實習生 胡張勇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劉奕伶看大陸要零距離的“登陸”體驗
作者丨記者程朔實習生胡張勇
面前這位女生,是5年前到北大攻讀博士學位。在學期間,曾經因為返回臺灣收集學術資料,她碰巧被傳染了甲型禽流感,結果在島內休息了好一陣子才回學校恢復學業。
那一去一來,硬是將她的學程后延了近兩年時間。好在就這次接受我們的采訪之后不太久,她便會獲得博士學位,然后就要回到島內,與相戀多年的男友組建起小家庭了。
劉奕伶,祖籍湖北,出生、長大一直都在臺北陽明山。奕伶的父親是位退休大學教授,母親一直操持家務。奕伶的男朋友是位“理工男”,也曾有過海外留學的經歷,現在做計算機軟件工程師。
到大陸攻讀博士學位
記者:請問您到大陸上學的主要動因是什么?
劉奕伶:在臺灣遠遠地看大陸,與實際來這邊零距離地看,那會是有差別的;都是“登陸”,實際在這邊工作學習,與來觀光過多少次,所能感受到的東西也是有差別的。到這邊生活,才會理解這邊的一些問題,比如為什么大陸這邊的人早上高峰期時會搶著上地鐵呢?經過實際的體會就能明白,大陸的人太多了、生活節奏太快了,大家對工作又極其認真,不能遲到,所以人們都會有搶先的念頭是很自然的事情。
島內有個說法是希望未來大陸實現某種西式的“直接民主”,然后實現所謂統一。我現在就會覺得這個說法很有問題!遑論東西方社會文化傳統大大不同,就大陸本身而言,它沿海省份與內陸省份間的人文環境及發展程度就有很大的區格,怎么可能去實行那種所謂西式的、直接的民主!這個部分,我在臺灣時雖然也有考量,但真正到了大陸,看到的、經歷到的都足夠多了,我的感受才切實深刻、清晰起來。
因此我會說,大家討論如何更好解決兩岸問題時,一定對彼此所處,都先親身體驗過才好;而已到達彼岸的人,則一定要保持最開放的心態,可以接受不同的事物。
記者:請問從小就一直對國際關系感興趣嗎?
劉奕伶:我其實原本是想自己走商業管理路線的,但是這個現實世界好像就是不認同我走那條路,每次想轉出去,我都會被逼回原點。從陽明高中畢業,我考入了政治大學政治系,到英國留學的時候就有申請讀MBA,但MBA的申請全都沒過,過的只是政治類,逼的我不得不在南開普頓大學選學國際關系專業。念完碩士之后,我就去找從事商業的工作了,先后進幾家都沒有做長,最后是進入國民黨智庫去當研究員才穩定下來。
我在國民黨智庫的研究工作,課題涉及到兩岸關系。工作中就感到所學不足,便在2011年到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外交學系攻讀博士學位,然后導師給規定的研究主題是關于“斷交”前后的臺美關系。
老天爺一定要我按照這樣的一條路前行,我也就順著走下去吧。還好導師告訴我,每個人的興趣都是可以后天培養的,比如我原本很排斥去檔案館查資料,但是做博士生這幾年,導師不停地要求我去檔案館查閱各種資料,我去得多了,慢慢地,現在竟已然都習慣了。
記者:來大陸上學,在人文環境方面是否會存在困擾?
劉奕伶:大陸同學之間,因為來自天南海北,個性差異都很大,沒有辦法將他們列為與“臺灣學生”群體相對應的“大陸學生”群體。其實倒是更容易將福建學生、江浙學生,與臺灣學生劃在與“北方學生”相對應的同一個群體“南方學生”中。換句話說,臺灣學生與大陸學生間,其實沒有太多不同。
我要特別提到一個個人體驗,在北京大學入學的時候,我的宿舍是一個套間,套間里面是兩個房間。這個套間中會有4個人入住,其中兩個是臺灣人,兩個是大陸人。很感謝學校的安排,它并不是分別將兩位臺生和兩位陸生分別放在不同一間屋中,而是讓每個臺生分別與一個陸生同一宿舍。如此的安排,像我這樣對大陸許多事物很陌生的臺生,通過同宿間的交流,很快搞懂了大陸的一些社會制度、經濟政策,甚至政黨、政治知識,也很快適應了一些大陸的生活習慣。當然,熟悉學校周邊地理環境的速度也是很快。
北京物價與臺北差不多,但同樣花費所享受到的服務質量,北京相對落后。不過,在網絡金融、網絡購物方面,北京是便捷很多的。
學術研究中的幾點心得
記者:請教您在臺美關系研究中的體會。
劉奕伶:簡單說,感覺美國因素對兩岸關系發展會有影響,但它現在已經不是可以起至關重要作用的那部分了。我最初是做戰略研究的,國家戰略研究。在英國做碩士研究生的時候,我導師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國的國家戰略,所以我會從國家戰略的角度上看問題。
我看歷史檔案,其實1949年左右,美國就企圖搞“兩個中國”。它認為中國統一了、更強大的話,對它不利。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其實還是想同時承認兩邊的,但大陸這邊整體實力發展的很快,那時的局勢逼著美國放棄臺灣,它在國際上表態支持一個中國,但實際上希望兩岸維持分裂局面。
時到今日,中國大陸發生了變化,它的經濟實力正在高速增長,任何外國已經沒有可能去干涉她;臺灣也變化了,首先從“美牛”案中,就可以看出,臺灣社會也早已不是對美國完全俯首帖耳的弱勢一方了,甚至可以說,由于“街頭民主”的作用,臺灣在處理兩岸關系時完全有可能出現自主行事、而并不去“刻意地在乎”美國感受的情況。
記者:請從個人角度對兩岸關系前景作個展望。
劉奕伶:我的父輩是1949年來臺灣的,是比較小的那部分人。因而我在大陸這邊還有很多親屬,所以我當然希望兩岸關系一直向好發展。
可是,我現在對兩岸關系未來的前景,感覺暫時還看不到終點。早年呢,還覺得可能會有一個終點在前邊,但最近幾年那種感覺越來越淡了。從追蹤的數據看,現在傾向“統”的比例在下降,如果將隱性“臺獨”加上主張“臺獨”的聲音加在一起,怕是會過半的。2008年,國民黨智庫就有不斷反映,希望將課綱、將對下一代的教育進行一個改進,可至今卻有17個縣選擇不用新課綱。
2016選舉,民進黨全面獲勝,這個現實情形是比較堪憂的。蔡英文日前曾在美國表明兩岸政策將“維持現狀”,但是,由于其向來否認“九二共識”的存在,所以其心目中的所謂“現狀”,恐怕不會與當年陳水扁時期的“彼狀”有很大的差別。寄希望在民進黨執政期間看到兩岸關系實現進步,恐怕不太現實!畢竟民進黨至今尚不愿放棄其“臺獨黨綱”。
記者:請從專業角度,為推動兩岸關系發展提些建議。
劉奕伶:我最近感覺大陸這邊要重視一個情況,臺灣現在是個多元社會,大家都會有自己的個別想法,其中愿意與大陸這邊接觸的人,刨除特殊情況之外,大多本身就會偏“統”一些,比如我和身邊同學,會選擇來大陸,他主張“獨”的幾率就很低了。如果大陸只接觸我們這些人比較多,總結到的會是“臺灣人很多傾向于反‘獨’”。但我們其實代表不了所有臺灣人,回到臺灣,打開電視看各個臺的節目,就會發現我們絕對不是那個大多數!

劉奕伶
所以呢,建議大陸不能只從我們這一部分人的口中所述出發,去判斷臺灣島內其他人群的心中所愿;而是需要更廣泛地深入臺灣民間,去聽取其他更多人群的真實民意表達,這樣才能完整把握臺灣民眾各種聲音,從而制定相宜的政策。錯估臺灣的民意,就會造成理念與現實之間的落差,那會非常有損于兩岸關系的發展。
用專業的話說,搞調研的時候一定要避免“選擇性傾聽”。調研要分析數據,數據的抽樣就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樣本廣度不夠的話,數據是必然會產生偏頗的,那么調研就必然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