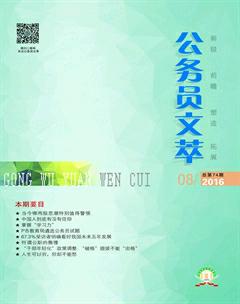中國(guó)人到底有沒有信仰?
劉亞洲
看一看中國(guó)思想史,中國(guó)從來就沒有過真正的啟蒙,中國(guó)人有的只是教化。教化和啟蒙有很大區(qū)別,教化是居高臨下的,而啟蒙則必須要從自己做起,從內(nèi)心做起。
我們從來不注重內(nèi)心,注重內(nèi)心才能建立起信仰。一百年前發(fā)明了照相術(shù),你看看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人的樣子,那種呆滯、木訥、麻木,這就是我們的祖先嗎?
你再看看一些紀(jì)錄片展示的當(dāng)時(shí)日軍侵略中國(guó)的片段,看看在那些鬼子的臉上洋溢的是一種怎么樣的神情。中國(guó)人在電影里不能演日本鬼子,演不出那種精、氣、神來。
為什么姜文拍《鬼子來了》非要找日本演員?為什么陸川拍《南京!南京!》非要找日本人來演?我們到今天都不一定能演出一個(gè)注重內(nèi)心的民族那種飛揚(yáng)的、激越的感覺。
看看當(dāng)時(shí)日本人給自己取的名字,你就能看出內(nèi)心的力量: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大竹英雄、石原莞爾、夏目漱石、官崎滔天……
再看我們?nèi)〉拿郑肥!⒍嚒⒋浠ā⒏毁F……這都是什么名字!這是苦難帶來的。豫劇調(diào)子悲腔哀怨,我一直認(rèn)為這樣的調(diào)子來自中原逐鹿的戰(zhàn)爭(zhēng)和黃河泛濫所帶來的苦難。
我們是因?yàn)榭嚯y太多而缺失了信仰,還是因?yàn)槿笔叛龆鴰砹颂嗫嚯y?食物缺乏,使人饑餓;精神上也有饑渴問題。
大約在一百多年前,中國(guó)一批有識(shí)之士看到了這一點(diǎn),于是開始尋找。最初他們想從國(guó)學(xué)中尋找。
中國(guó)文化博大精深,國(guó)學(xué)里有很多出色的東西,但國(guó)學(xué)能夠解決今天的問題嗎?有人認(rèn)為能。我認(rèn)為這把問題看淺了。
鴉片戰(zhàn)爭(zhēng)和甲午戰(zhàn)爭(zhēng)正是在國(guó)學(xué)最盛時(shí)發(fā)生的。那么,精神層面問題的出路何在?我們的精神家園在哪里?這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終極追問。
中國(guó)革命之初,共產(chǎn)黨人擁有強(qiáng)大的信仰。為了信仰,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惜。
陳覺、趙云霄夫婦從蘇聯(lián)回國(guó),在湖南從事地下活動(dòng),不幸被捕。陳覺很快被殺害,趙云霄因懷孕在身,刑期推到分娩后。
孩子出生后,她只要發(fā)表脫黨聲明,就可出獄,但她決不叛黨,敵人把她也殺害了。臨刑前,趙云霄給孩子寫了一封信,我記得第一句話是“啟明我的小寶寶”。
這封信大義凜然,卻充滿了人間溫情。信中那一聲聲“小寶寶”的呼喚,分明是一曲人間親情的絕唱。我?guī)资昵翱催^描寫這個(gè)故事的油畫,這個(gè)女共產(chǎn)黨員抱著孩子喂最后一次奶。當(dāng)時(shí)我流淚了。這是怎樣的精神和信仰!
這個(gè)只有二十三歲的女共產(chǎn)黨員體內(nèi)蘊(yùn)藏著怎樣巨大的精神力量。肝腸寸斷中卻對(duì)共產(chǎn)主義的明天抱著無限憧憬。過去我們擁有多么強(qiáng)大的精神力量,不奪天下是不可能的。
今天,很多人信仰破滅了。信仰一旦崩潰,比不曾有過信仰更加糟糕,就像文明一旦崩潰,比不曾有過文明還要糟糕一樣。
前幾天,我又看到一封信,是一個(gè)退休多年的老干部寫給兒子的,大意是:你到社會(huì)上工作后,千萬不能講真話,因?yàn)橹v真話是要倒霉的。在領(lǐng)導(dǎo)面前你要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不要輕易相信別人,等等。這封信登在一個(gè)雜志上,你們可以找來看看。這封信,說明這個(gè)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的信念已經(jīng)破滅。這封信也代表了當(dāng)前相當(dāng)一部分父輩的心態(tài)和觀念。
當(dāng)前,精神危機(jī)是最根本的危機(jī)。無精神是無道德的體現(xiàn),無道德是無信仰的體現(xiàn),道德的源頭是信仰。
精神的構(gòu)建在今天比物質(zhì)的構(gòu)建要重要百倍。沒有精神的中國(guó)是不會(huì)過上好日子的。我們已經(jīng)嘗到最初的苦果。
有段子說,中國(guó)人從食品中完成了化學(xué)的掃盲。比如,從大米中認(rèn)識(shí)了石蠟,從火腿中認(rèn)識(shí)了敵敵畏,從雞蛋中認(rèn)識(shí)了蘇丹紅,從牛奶中認(rèn)識(shí)了三聚氰胺。這一點(diǎn),我們對(duì)古人、對(duì)今人、對(duì)未來人都是欠了債的。這個(gè)債一百年也還不清。
今后,我們可能會(huì)嘗到更大的苦果。我已多次講過信仰問題,可應(yīng)者寥寥。我想起了“文革”中犧牲的張志新的那句話。張志新在臨終前嘆息:“我向冰冷的鐵墻咳一聲,還能聽到一聲回音。我向活人呼喚千遍萬遍,恰似呼喚一個(gè)死人。”
(摘自《精神》)
- 公務(wù)員文萃的其它文章
- 微言
- 意林
- 漫畫
- 幽默
- 三個(gè)德國(guó)人
- 人應(yīng)該主動(dòng)選擇糊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