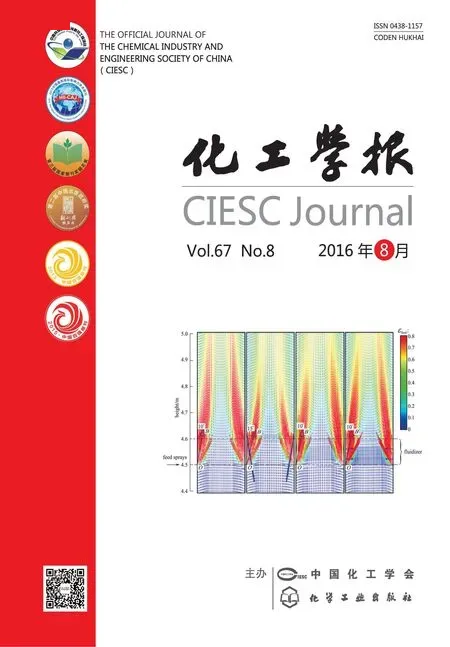CFB提升管等效反應器網絡模型
杜玉朋,趙輝,張海桐,楊朝合
(1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重質油國家重點實驗室,山東 青島 266580;2石油和化學工業(yè)規(guī)劃院,北京 100013)
CFB提升管等效反應器網絡模型
杜玉朋1,趙輝1,張海桐2,楊朝合1
(1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重質油國家重點實驗室,山東 青島 266580;2石油和化學工業(yè)規(guī)劃院,北京 100013)
對氣固循環(huán)流化床(CFB)提升管內的非均相流動行為進行了計算流體力學(CFD)模擬。基于CFD時均流場數據與信息,搭建了用于描述提升管內非理想流動過程的等效反應器網絡(ERN)模型。在ERN模型建立過程中提出了反應器網絡的6個拓撲結構參數和一個等效判據,并系統(tǒng)地分析了等效反應器網絡結構六參數的性質與確定方法,從而形成了一套CFB提升管流動模型建模方法。
循環(huán)流化床;計算流體力學;模型;反應器網絡;等效;模型參數
引 言
過去幾十年間,氣固循環(huán)流化床反應器在石油催化裂化、煤燃燒與氣化以及化工冶金等過程中得到了極為廣泛的應用[1-2]。CFB提升管內的氣固兩相流動屬于快速流態(tài)化的范疇,快速流態(tài)化床層既非均勻散式流態(tài)化,亦非鼓泡流態(tài)化,而是一種散式化了的聚式流態(tài)化[3]。因此,掌握其內的兩相流動行為是提升管反應器設計與裝置放大的關鍵。
在CFB提升管模型化方面,人們曾提出大量的經驗或機理性數學模型,包括一維流動模型(聚集-分散模型、夾帶模型、軸向擴散模型)、一維兩通道模型以及稀密兩相局部模型[4]。然而,這些經驗模型由于過度簡化CFB提升管內的多相流動過程,同時未對氣固流場時空分布各向異性的內在機理進行根本探討而存在較大經驗性,預測提升管內的流場分布能力一般較弱。基于Navier-Stokes方程的CFD模型雖可以細致地描述提升管內的氣固兩相流動行為[5-7],提供給人們既準確又詳細的流場信息,但有些數據在工程上并不是必需的。此外,由于CFD模型方程通常非線性程度高、計算資源消耗大、求解時間漫長等而存在著無法直接用于生產實踐的難題。
可見,一方面,經驗模型方程形式簡單,求解快速,但模型假設與CFB提升管內的非理想流動狀態(tài)存在較大差距,模型準確度亟待提升;另一方面,CFD流動模型雖然在模型精確度方面有了極大程度的提高,但其自身劣勢亦非常明顯,例如傳統(tǒng)的基于平均化處理方式的雙流體模型(TFM)并不能準確描述流化床中的多尺度流動和傳遞行為,且對計算域網格精度要求苛刻,計算耗時耗力。而當CFD流動模型與反應動力學模型相耦合進行反應器內的反應多相流模擬時,對于像石油催化裂化提升管這樣涉及成千上萬種反應物質的反應器來說,模型計算量和計算時間的需求可謂極其嚴苛。因此,亟需開發(fā)既準確又快速的反應器流動模型[8]。
近期,本課題組[9]曾為反應條件下的催化裂化提升管反應器建立了等效理想反應器網絡(ERN)模型,同時實現了FCC提升管反應器的準確模擬與快速計算。本文研究旨在詳細闡述 ERN模型在構建過程中需要特別關注的幾個關鍵性問題,如反應器網絡拓撲結構的描述與等效判定、模型參數的性質與確定方法以及各參數之間的關系,從而進一步完善 ERN模型建模方法,并希冀其能在提升管反應器的設計與放大、循環(huán)流態(tài)化裝置生產調優(yōu)與控制中得到應用。
1 CFD模型
1.1建模對象
圖1所示為一個氣固循環(huán)流化床冷態(tài)模擬實驗裝置中的提升管[10]。該循環(huán)流化床裝置不僅能夠用于測定提升管內壓降和顆粒循環(huán)量,而且還可以通過引入示蹤顆粒的方法,研究固體顆粒停留時間分布和氣固混合等情況。整個提升管高 9.0 m,截面為邊長0.11 m的四邊形。其中,0.1 m和8.5 m高度處分別是固體顆粒的入口高度和固相示蹤顆粒檢測點位置。冷態(tài)模擬實驗過程中所采用的氣體介質為空氣(密度1.2 kg·m-3、黏度1.8×10-5Pa·s),固相顆粒為FCC催化劑(密度1400 kg·m-3、平均粒徑70 μm)。

圖1 CFB提升管[10-11]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CFB riser[10-11]
1.2控制方程、邊界條件與模型求解
考慮到Lagrangian方法的計算量問題,本研究采用Eulerian-Eulerian雙流體模型對CFB提升管進行數值模擬。在雙流體模型中,氣相和固相被認為可相互滲透,并擁有各自的相分率和速度分布,需要對其同時進行連續(xù)性方程和動量方程的求解,其中固相動量方程可通過顆粒動力學理論確定顆粒壓力與黏度和顆粒溫度來封閉。然而,傳統(tǒng)的雙流體模型并未考慮氣固流態(tài)化過程中存在的介尺度結構(如顆粒聚團)與守恒規(guī)律的耦合影響,而僅在封閉由于擬流體化帶來的固相應力和氣固相間作用力時,采用了平均化的處理辦法。近年來部分學者提出若采用考慮介尺度流動結構的 EMMS(energy minimization multi-scale)曳力模型將會得到與實驗數據更為一致的流場分布[11-13]。因此,本研究采用雙流體模型與EMMS曳力模型相耦合的方法對圖1所示的CFB提升管進行了CFD模擬,主要的模型方程見表1。
采用Ansys Fluent軟件對以上模型方程進行求解,主要參數設置見表 2。在提升管底部入口處氣相速度和固相速度被指定,固相分率設為0.5;提升管出口被設置為常壓出口邊界;在提升管壁上,氣相無滑移,固相為部分滑移。待所有邊界條件設置好之后,用Phase Coupled SIMPLE算法對壓力-速度耦合方程進行求解。由于整個模型方程組的求解基于有限體積法,故需對整個提升管計算域進行網格劃分和模型方程的離散,并對網格無關性進行分析。模型中動量方程和相分率的離散分別采用二階迎風格式和QUICK格式。經過網格獨立性分析研究,并考慮到模型計算精度與計算效率等問題,本研究最終采用 16×16×266的結構化網格劃分方案。此外,在進行CFD模擬時,為保證提升管內氣固流動達到穩(wěn)態(tài),共模擬了30 s的物理時長,并取后15 s數據進行了時均處理。

表1 CFD模型方程Table 1 CFD m odel equations

表2 CFD模型參數設置Table 2 Param eters setting for CFD models
1.3CFD模擬結果與討論
圖2(a)、(b)分別給出了由CFD模型預測的氣固循環(huán)流化床提升管內豎直方向上的時均壓力梯度分布和在提升管高度8.50 m處水平方向上的時均固體通量分布情況。由圖2(a)可以看出,在Ug=7 m·s-1和Gs=133 kg·(m2·s)-1的操作條件下,催化劑顆粒相在提升管內呈現出上稀下濃的“C”形分布,模型預測的各豎直方向上的截面平均固相分率與實驗值[10]非常接近。由圖2(b)可以看出,在提升管不同水平位置處的固體催化劑通量呈現中間大兩邊小的分布型式,與實驗數據[10]一致。
圖3(a)給出了CFB提升管內固相分率的瞬時云圖。由該圖可以看出提升管內的氣固非均勻流動過程,固體催化劑以聚團的形式隨著氣相向上流動,并伴隨著顆粒聚團的形成與分散等介觀流動現象,與實驗中常常觀察到的顆粒聚團流動行為一致[3]。圖3(b) 給出了帶有環(huán)核邊界的時均軸向速度云圖。值得一提的是,該圖是在對CFD模擬結果進行后處理時,對固體顆粒速度向上的所有區(qū)域進行了紅色標記,而速度向下的區(qū)域被標記為藍色而得到。因此,由該圖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固體顆粒在提升管內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上運動之間的邊界,即環(huán)核流動邊界。這與諸多研究者實驗所觀測到的氣固循環(huán)流化床提升管內的固相顆粒環(huán)核流動結構的結論相一致[14-15]。

圖2 CFD模擬結果與實驗數據對比Fig.2 Comparisons between CFD simulations and experimental data

圖3 瞬時固相分率云圖和時均軸向速度云圖Fig.3 Contours of transient solids volume fraction at t=30 s and time-averaged axial velocity field
綜上可知,集成EMMS曳力模型的CFD模型能夠準確地描述 CFB提升管內的氣固兩相非均勻流動過程。
2 等效反應器網絡模型
2.1反應器網絡結構與“等效”
等效反應器網絡(ERN)模型是將原非理想反應器進行分區(qū),然后針對每個分區(qū)選用適宜的理想反應器來代替,并將所有理想反應器單元組合起來,用以等效地描述原反應器內的非理想流動過程[9],如圖4所示。等效反應器網絡的概念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了這個概念,但其蓬勃發(fā)展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近年來由于其具有計算簡便、接口靈活與適用性廣等優(yōu)點,而成功應用于化工和能源領域,如攪拌釜、燃燒爐、生物降解池、氣化爐等多種反應器[16-19]。

圖4 等效反應器網絡模型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equivalent reactor network (ERN)model
等效反應器網絡模型的建立關鍵在于確定與原非理想反應器等效的理想反應器網絡拓撲結構,因此首先必須回答好兩個問題:① 如何描述理想反應器網絡的拓撲結構;② 如何判斷所建立的理想反應器網絡與原非理想反應器“等效”。
對于問題①,本文提出了六參數描述反應器網絡結構(structure of reactor network, SRN)的方法,以數學函數的形式可表示為

式中,n為原非理想反應器被分割成區(qū)塊的總數目;s為分區(qū)形狀;V為分區(qū)尺寸或大小;α為分區(qū)內各相分率;F為相聯(lián)結的分區(qū)之間傳遞的流量;t為分區(qū)被何種類型的理想反應器所代替。
對于問題②,由于停留時間分布(RTD)可用于描述反應器中物料返混程度與非理想流動情況,因此本研究采用停留時間分布近似這一原則來判定所建立的理想反應器網絡拓撲結構是否可以等效地描述原反應器內的非理想流動行為,相當于數學概念中的目標優(yōu)化問題,即

綜上,等效反應器網絡模型的建模本質上是圍繞流體穿過所建理想反應器網絡的停留時間分布近似于實驗停留時間分布這一目標(即“等效”)來確定描述反應器網絡拓撲結構六參數的過程。
2.2模型六參數性質分析
首先對ERN模型各參數的性質分析如下:
(1)n是一正整數,可取某一確定的值;
(2)s是一個元素個數為n的一維向量,且向量內各元素的值通常無法量化,可取各種各樣的形狀,但為了模型求解與分析的方便,常取規(guī)則形狀(如三角形、四邊形、長方體、立方體等);
(3)V是一維向量,元素個數為n,各元素值均是實數,取值范圍0~Vmax,Vmax是原非理想反應器的體積;
(4)α 是元素個數為n的一維向量,各元素均為實數,取值范圍0~1.0;
(5)F是一個(n+2)×(n+2)的二維矩陣(其中的2指入口和出口),矩陣內各元素為矢量,具有方向性;
(6)t是元素個數為n的一維向量,各元素值可被認為是字符型變量,一般取值為全混流(CSTR)、平推流(PFR)或死區(qū)(dead region)等理想流型。
在構建理想反應器網絡模型時,因受到反應器網絡“等效”這一優(yōu)化目標的限制,拓撲結構六參數的取值必定緊密相關。在對復雜的非理想反應器進行分區(qū)時,分區(qū)個數(n)與各分區(qū)形狀(s)之間存在著相關關系,分區(qū)個數發(fā)生改變,勢必會導致某些分區(qū)的形狀發(fā)生變化,但這種相關關系只能進行定性地分析,無法量化。然而,分區(qū)形狀(s)與分區(qū)體積(V)、分區(qū)內的各相分率(α)以及分區(qū)間的流量(F)之間的關系是可以唯一確定的,因為一旦區(qū)塊形狀被確定,則區(qū)塊所占有的體積和其內的相分率亦隨之被確定,相鄰區(qū)塊之間的聯(lián)結邊界上通過的各相流量也就相應地被確定下來。此外,分區(qū)形狀(s)與所代替該區(qū)塊的單元反應器型式(t)之間也常常存在某種相關聯(lián)關系,因為區(qū)塊內的流場分布可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需采用何種理想反應器來代替,但這種關系在某些情況下,如為了使所建立的理想反應器網絡達到“等效”這一目標,是可以對其進行優(yōu)選或調整的。綜上分析可知,反應器網絡拓撲結構六參數的確定關鍵在于確定其中3個參數,即分區(qū)個數(n)、分區(qū)形狀(s)與代替分區(qū)的反應器型式(t)。而其他3個參數可以通過實驗或由數值模擬獲得的流場數據來確定。
由本文1.3節(jié)的討論可知,CFD流場能夠提供詳細的反應器內流場分布數據與信息,因而可以根據 CFD流場數據來確定分區(qū)體積(V)、區(qū)塊內部相分率(α)和分區(qū)間流量(F)這3個參數[16]。

式中,Vcell是屬于區(qū)塊i的每個CFD單元格的體積,Acell是位于區(qū)塊i和區(qū)塊j邊界上的每個CFD單元格的面積。
因此,式(1)可進一步簡化為

2.3確定模型參數n、s和t

圖5 CFD時均流場與提升管分區(qū)方案Fig.5 Time-averaged CFD flow field and partition schemes for riser
提升管分區(qū)首先擬按照圖5(a)所示的劃分方案進行。根據Bi等[20]和 Rhodes等[21]對快速流化床內典型氣固流動行為的描述,沿CFB提升管豎直方向可將其內的整個床層分成3段(h1=0.10~5.20 m,h2=5.20~6.10 m,h3=6.10~8.50 m)。如圖5(a)所示,其中提升管高度5.20 m以下的區(qū)段(h1)為環(huán)核流動區(qū)域,6.10 m以上的區(qū)域(h3)為氣固兩相充分發(fā)展區(qū)域,中間段(h2)為環(huán)核流動結構向氣固充分發(fā)展逐步過渡的區(qū)域。
對于h1段,沿提升管豎直方向可被分成4等份,其中位于最底部的為提升管入口段。因提升管底部入口處氣固混合較劇烈,故宜用全混流反應器(CSTR)來代替或模擬;而其余 3等份沿提升管徑向又可進一步分作環(huán)區(qū)與核區(qū)。h1段總共被劃分成了 10個形狀不同的區(qū)塊,如圖 5(b)中分區(qū)標號1~10所示。由于多個CSTR串聯(lián)可到達與PFR等效的緣故,本文對全部分區(qū)均采用CSTR進行替代和模擬。
由于 h2段內氣固兩相混合與相互作用比較劇烈,因此選擇采用CSTR來代替和模擬,如圖5(b)中分區(qū)標號11所示。
對于h3段,盡管氣固兩相均沿CFB提升管軸向向上平穩(wěn)流動,但仍不是絕對意義上的理想平推流流型。因此,為了能夠準確描述該區(qū)域內的流動行為,本文對其進行了豎直方向與水平方向分別 3等分,從而劃分成 9個區(qū)塊(如分區(qū)標號 12~20所示)。同樣,每個區(qū)塊均采用CSTR代替與模擬。
至此,便初步確定了理想反應器網絡的3個最重要的結構參數,即分區(qū)數目(n=20)、每個區(qū)塊的形狀(s)以及替代每個分區(qū)的理想反應器類型(ti=CSTR)。而每個分區(qū)的體積(Vi)、區(qū)塊內的相分率(αi)和各區(qū)塊間的流量(Fij)可以分別由式(3)、式(4)和式(5)求得。
2.4反應器網絡等效判定
經初步確定的6個模型參數所描述的理想反應器網絡模型是否能夠與原提升管內的氣固兩相流動過程“等效”需根據式(2)進行等效判定。其中,固體催化劑顆粒穿過所建立的理想反應器網絡的停留時間分布可通過馬爾科夫鏈隨機模型[19,22]模擬得到。
在使用馬爾科夫鏈隨機模型時,每個CSTR被當作一個過渡態(tài),系統(tǒng)出口流被認作終態(tài)。假定所研究的CFB提升管系統(tǒng)處于定常態(tài),且系統(tǒng)內的流元皆可識別。令隨機變量 Xk是一可識別的流元在t=0以后經過 k次狀態(tài)轉移后在系統(tǒng)內所處的位置(狀態(tài)),于是序列{Xk}可以看成一個馬爾科夫鏈。令pii表示狀態(tài)為i的流元經過一次轉移后仍保留在原狀態(tài)的概率,而pij表示流元從狀態(tài)i轉移到狀態(tài)j的一步轉移概率,qij表示流元從狀態(tài)i轉移到狀態(tài)j的轉移概率強度,該值與反應器網絡模型中的各區(qū)塊間的流量矩陣中的各元素值(Fij)有關。
對于每個 CSTR,選擇一個小的時間間隔或步長Δt,且假定流元的狀態(tài)只在時間為mΔt(m=1,2,…)的瞬間才能從一個狀態(tài)轉移到另一個狀態(tài)。因此經過Δt后,流元仍停留在該CSTR內的概率為

而從第i個CSTR轉移到第j個CSTR的概率為

通過將馬爾科夫鏈隨機模型計算得到的 RTD曲線與實驗值對比,便可驗證所建立的理想反應器網絡拓撲結構或配置方案是否能夠等效地重現原CFB提升管內的非理想流動行為。由圖6(a)給出的理想反應器網絡模型 RTD曲線與實驗數據[10]對比結果可以看出,計算值與實驗值之間存在著較好的對應關系,且由馬爾科夫鏈隨機模型方法計算得到的固體顆粒穿過理想反應器網絡的平均停留時間(6.78 s)與實驗值(6.0 s)基本接近。因此,認為該理想反應器網絡拓撲結構能夠較好地描述原CFB提升管內的非理想流動過程。
為了進一步探索反應器網絡拓撲結構參數之間的關系,對分區(qū)方案類似的前提下對原CFB提升管進行了更為細致地劃分,共分成 50個區(qū)塊(即n=50),如圖5(c)所示。每個分區(qū)仍采用CSTR來模擬。采用馬爾科夫鏈模型計算得到的固體顆粒RTD曲線與實驗值之間的對比見圖6(b)。對比圖6(a)與圖 6(b)可以看出,當 n=50時理想反應器網絡模型RTD曲線與實驗數據更為一致,且計算得到的固體顆粒平均停留時間(6.28 s)也與實驗值更加接近,即其等效性相對更高。
3 結 論
(1)集成了EMMS曳力模型的CFD模型可準確模擬氣固循環(huán)流化床提升管內的兩相流動過程,并提供詳細的流場分布信息。
(2)基于 CFD流場數據而搭建的等效反應器網絡模型能較好地重現原CFB提升管內的非理想流動過程,并反映固相停留時間分布狀況。

圖6 反應器網絡模型RTD曲線與實驗數據對比Fig.6 Comparisons of RTD for ERN models w ith experimental data
(3)在 CFB提升管分區(qū)方案類似的情況下,分區(qū)數目越多,所建立的理想反應器網絡模型與原非理想反應器的等效性相對越好。
符號說明
CD——曳力系數
dp——顆粒直徑,m
E(t) ——停留時間分布密度函數,s-1
e ——碰撞恢復系數
F ——分區(qū)間流量矩陣
Gs——固體循環(huán)量,kg·m-2·s-1
g ——重力加速度,m·s-2
g0——徑向分布函數
K ——相間曳力系數,kg·m-3·s
k ——湍動能
n ——分區(qū)數目
p ——轉移概率
s ——分區(qū)形狀向量
t ——反應器型式向量
Ug——表觀氣速,m·s-1
V——分區(qū)體積向量
Vmax——非理想反應器體積,m3
v——速度,m·s-1
wEMMS——EMMS曳力系數修正因子
α ——相分率向量
γ——碰撞能量耗散系數,kg·m-3·s
ε——湍流耗散率
Θ——顆粒溫度,m2·s-2
μ——黏度,Pa·s
ρ——密度,kg·m-3
τ——應力張量,Pa
下角標
g——氣相
i,j——分區(qū)或狀態(tài)編號
s——固相
References
[1] KUNII D, LEVENSPIEL O. Fluidization Engineering [M]. Amsterdam: Elsevier, 2013.
[2] GRACE J R, KNOWLTON T M, AVIDANA A A.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s [M].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2012.
[3] 郭慕孫, 李洪鐘. 流態(tài)化手冊[M]. 北京: 化學工業(yè)出版社, 2008.
KWAUK M, LI H Z. Handbook of Fluidization [M]. Beijing: Chem ical Industry Press, 2008.
[4] 陳俊武. 催化裂化工藝與工程[M]. 北京: 中國石化出版社, 2005.
CHEN J W. Fluidized Catalytic Cracking Process and Engineering [M]. Beijing: China Petrochem ical Press, 2005.
[5] BENYAHIA S, ARASTOOPOUR H, KNOWLTON T M, et al. Simulation of particles and gas flow behavior in the riser section of a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using the kinetic theory approach for the particulate phase [J]. Powder Technol., 2000, 112(1): 24-33.
[6] ZHANG N, LU B, WANG W, et al. 3D CFD simulation of hydrodynam ics of a 150 MWe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boiler [J]. Chem. Eng. J., 2010, 162: 821-828.
[7] JIRADIALOK V, GIDASPOW D, DAMRONGLERD S, et al. Kinetic theory based CFD simulation of turbulent fluidization of FCC particles in a riser [J]. Chem. Eng. Sci., 2006, 61(17): 5544-5559.
[8] 楊朝合, 杜玉朋, 趙輝. 催化裂化提升管反應器流動反應耦合模型研究進展[J]. 化工進展, 2015, 34(3): 608-616.
YANG C H, DU Y P, ZHAO H. Evolvement of flow-reaction models for fluid catalytic cracking riser reactors [J]. Chem ical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 Progress, 2015, 34(3): 608-616.
[9] DU Y, ZHAO H, MA A, et al. Equivalent reactor network model for the modeling of fluid catalytic cracking riser reactor [J]. Ind. Eng. Chem. Res., 2015, 54(35): 8732-8742.
[10] ANDREUX R, PETIT G, HEMATI M, et al. Hydrodynam ic and solid residence time distribution in a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experimental and 3D computational study [J]. Chem. Eng. Process., 2008, 47(3): 463-473.
[11] HUA L, WANG J, LI J. CFD simulation of solids residence time distribution in a CFB riser [J]. Chem. Eng. Sci., 2014, 117: 264-282.
[12] YANG N, WANG W, GE W, et al. CFD simulation of concurrent-up gas-solid flow in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s with structure-dependent drag coefficient [J]. Chem. Eng. Sci., 2003, 96(1): 71-80.
[13] WANG W, LI J. Simulation of gas-solid two-phase flow by a multi-scale CFD approach - of the EMMS model to the sub-grid level [J]. Chem. Eng. Sci., 2007, 62(1): 208-231.
[14] KIM S W, KIRBAS G, BI H, et al. Flow structure and thickness of annular downflow layer in a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riser [J]. Powder Technol., 2012, 380(1): 48-58.
[15] ZHANG W, JOHNSSON F, LECKNER B, et al. Fluid dynamic boundary layers in CFB boilers [J]. Chem. Eng. Sci., 1995, 50: 201-210.
[16] BEZZO F, MACCHIETTO S, PANTELIDES C C. Computational issues in hybrid multizonal/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models [J]. AIChE J., 2005, 51(4): 1169-1177.
[17] LI C, DAI Z, SUN Z, et al. Modeling of an opposed multiburner gasifier with a reduced-order model [J]. Ind. Eng. Chem. Res., 2013,52: 5825-5834.
[18] LE MOULLEC Y, GENTRIC C, POTIER O, et al. Comparison of systemic, compartmental and CFD modelling approaches: application to the simulation of a biological reactor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J]. Chem. Eng. Sci., 2010, 65(1): 343-350.
[19] DU Y, YANG Q, BERROUK A S, et al. Equivalent reactor network model for simulating the air gasification of polyethylene in a conical spouted bed gasifier [J]. Energy & Fuels, 2014, 28(11): 6830-6840.
[20] BI H T, GRACE J R. Flow regime diagrams for gas-solid fluidization and upward transport [J]. Int. J. Multiphas. Flow, 1995, 21(6): 1229-1236.
[21] RHODES M J, SOLLAART M, WANG X S. Flow structure in a fast fluid bed [J]. Powder Technol., 1998, 99(2): 194-200.
[22] 戎順熙, 范良政. 連續(xù)流動系統(tǒng)停留時間分布的隨機模型和模擬[J]. 化工學報, 1986, 37(3): 259-268.
RONG S X, FAN L Z. Stochastic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the residence time distribution for continuous flow systems [J]. Journal of Chemical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China), 1986, 37(3): 259-268.
Equivalent reactor network model for CFB riser
DU Yupeng1, ZHAO Hui1, ZHANG Haitong2, YANG Chaohe1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eavy Oil Process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80, Shandong, China;2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 Chemical Planning Institute, Beijing 100013, China)
Non-homogeneous gas-solid flow in a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CFB) riser was numerically simulated w ith CFD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the time-averaged CFD flow fields, a novel non-ideal reactor model named equivalent reactor network (ERN) model was developed for the CFB riser. Six parameters for characterizing the structure of a reactor network and the criteria for equivalence checking of the established reactor network were proposed. Systematic analysis on each model parameter an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m were made elaborately. Values of these parameters were determined subsequently. It was found that the developed ERN model, which was based on the time-averaged CFD flow fields, was capable of describing reasonably non-ideal gas-solid flow behaviors in the CFB riser.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CFD;model;reactor network;equivalence;model parameters
date: 2016-03-31.
Prof. YANG Chaohe, yangch@upc.edu.cn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2012CB215006).
TQ 021.1
A
0438—1157(2016)08—3268—08
10.11949/j.issn.0438-1157.20160402
2016-03-31收到初稿,2016-05-25收到修改稿。
聯(lián)系人:楊朝合。第一作者:杜玉朋(1987—),男,博士研究生。
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fā)展計劃項目(2012CB21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