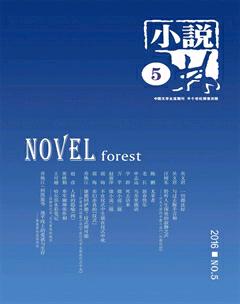微小說二題(二)
桃葉歌
我是桃葉,南朝時秦淮河邊一位賣扇兼賣硯的女子。我家的這方硯,叫“桃花硯”。這香艷的秦淮河邊,常有公子王孫過往。他們一看到我,就眼睛發直,說我長得跟桃花一樣好看。有些為了顯示他們的風雅,還要幫我畫扇或者在我的扇上題詩呢。
這些濁物,我又怎么會把他們放在眼里?我心里有一個人。他是誰?王獻之!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個兒子,字子敬。小時候,我練字,父親就給我講王獻之臨池十八缸的故事。
我愛極了王獻之的書法,嫻熟,潤秀,如丹穴中鳳凰飛舞,如清泉中蛟龍飛躍。字如其人,他本人也英俊瀟灑,風流蘊藉。而且,他是一個多么專情的男人。他和表姐郗道茂情深意篤。用他自己的話說:“雖奉對積年,可以為盡日之歡,常苦不盡觸類之暢。”那是幾年如一日的恩愛啊。可是,新安公主(司馬道福)愛慕他,她的丈夫恒濟篡權事敗,她就與恒濟離婚,硬纏著要改嫁給王獻之。她的弟弟孝武帝同意了,謝安等大臣也在旁操縱。王獻之心意堅定,甚至燒傷了自己的雙腿,以跛足為由拒婚,可這也無濟于事。于是,他無奈地娶了公主。為了家族利益,他被迫休了郗道茂。這事成了他一生的心結。
相思渺渺,王獻之郁郁寡歡,四十三歲就離開了人世。離世前幾年飽受足疾之苦,臨終前,他說此生唯一的憾事就是跟表姐郗道茂離婚。
這樣才貌雙全又重情的男子,哪個女子不動心呢?
我是一個賣扇女,家境貧寒,卻從小喜歡文墨,心比天高。我一遍遍臨摹王獻之的字,不可救藥地愛上了這一個已經作古的人。我想,如果我和他同個朝代出生,我心甘情愿做她的小妾。哪怕,他最鐘愛的是他的表姐。哪怕,家中還有一個霸道的新安公主。我只要他的一點點柔情。曾經,他住在烏衣巷,在河的那一邊。一個又一個春天,桃花盛開的時候,我想象著,我渡河去與他相見。他白衣飄逸,深情款款地在渡口迎接我。他充滿愛憐地對我說:“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我呢,一定送上一方“桃花硯”,為他紅袖添香。如果夏日到了,我會送上一把團扇,上面題著我作的《團扇歌》:“七寶畫團扇,燦爛明月光。與郎卻耽暑,相憶莫相忘。”
我就這樣想象著我和他的愛情,在一把又一把扇子上,題上《桃葉歌》,落款為“王子敬”。
不知為什么,《桃葉歌》竟然傳唱開了。人們疑惑,難道王獻之有個叫桃葉的愛妾?可是,王獻之的年表里沒有桃葉,正史也不見記載呀。多年以后,這樁風流韻事鐵板釘釘,那個渡口,叫作“桃葉渡”。 人們甚至想象出桃葉有個妹妹叫桃根,也做了王獻之的妾。特別是宋朝開始,文人們心儀的就是這個桃葉渡。秦淮河乃六朝金粉所凝的旖旎之地,才子佳人在此依依惜別、殷殷相迎甚是相宜。那個寫《儒林外史》的吳敬梓,故居與渡口相鄰,他當然也沒放過這個吟誦風雅的機會。“花霏白板橋,昔人送歸妾。水照傾城面,柳舒含笑靨。邀笛久沉埋,麾扇空浩劫。世間重美人,古渡存桃葉。”當然,這時我亦是一個古人。
我以這種方式,將自己“嫁”給了王獻之,在他的鐵畫銀鉤中,渲染出一朵桃花。年復一年,青絲成灰,我仍孑然一身。有一次,一種預感,使我毅然渡河。恍惚間,我發現那個白衣飄逸、英俊瀟灑的王子敬正朝我微笑,然后,又飄然而去。“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風映何限,感郎獨采我。”我就要去追他,向他訴說……
冥冥中,我聽到岸上有人傳唱:“桃葉復桃葉,渡江不待櫓。風波了無常,沒命江南渡。”
薛濤箋
她隱居在浣花溪邊,用“玉女津”(井名)的水,制作出一種桃紅色的小箋。小箋纖巧別致,適合寫旖旎的情書和清新小詩。
那箋,就叫“薛濤箋”,那井,后來叫作“薛濤井”。年復一年,錦城的木芙蓉花開得燦如人面。“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一個又一個春天,她在相思中寂寞地老去。
夜闌人靜,斜月西墜,身著道袍的她,在想些什么?如果一直感嘆佳期渺渺,她期待的又是誰?
記憶中,是一張又一張男人的臉,一首又一首云霞般瑰麗的詩歌。
白居易、劉禹錫、武元衡、李德裕、牛僧孺、令狐楚、張籍……跟她交往的名士,可開出一份長長的單子。男詩人們寫出了詩,第一個想給皇帝看,第二個就想給她看。她美貌絕倫,才華蓋世,有林下之風,胸襟氣度不讓須眉。
一生閱人無數,但最后,烙印最深的還是兩個男人。
韋皋,一個恩威并濟,一手捧紅了她又嚴懲她的男人。她在一首詩中,說自己是螢火蟲,怎能跟明月爭輝。那個她比喻為明月的人,確實是一代名臣。他被稱為諸葛再世,武能安邦,文能治國。當年,因為父親亡故,她,一位官宦人家的小姐,淪入樂籍,在宴席上伺酒做詩。是川主韋皋,看到了一顆風塵中光彩熠熠的明珠。他讓她進入他的幕府,處理公文,甚至還想上書奏封她為校書,由于門客反對,最后作罷。可是,“校書”之名不脛而走。多少名士爭相一睹芳容。一些趨炎附勢的小人更是希望接近她了解韋皋大人的喜好。彼時涉世未深,難免恃寵而驕,居然收納賄金。終于,韋皋憤怒了。韋皋的憤怒在于這只美麗的孔雀居然如此不愛惜自己的毛羽,當然,另一面,是因為她的招搖,在男人們的寵愛中她飄飄欲墜。他把她派往偏遠的松州。路途迢迢,寒風刺骨,烽火連天,她一個弱女子怎么能經受住邊地的風霜。她兩次獻詩,最終以哀婉動人的《十離詩》打動了韋皋,被召回。
這次赴邊,成了她一生的轉折點。她看清了自己的地位,想明白了今后的道路。她在詩中說:“但得放兒歸舍去,山水屏風永不看。”果然,回來后,她就脫離了樂籍,隱居在萬里橋邊。從此,她內斂,沉靜,與名流酬答不卑不亢,詩歌也越來越大氣。可是,她和韋皋,有了一道深深的鴻溝。盡管,韋皋調任前,與她兄妹相稱。盡管,他離開蜀地,還到處傳播她的才名。可是,情感上他們無法對等。而在聽到他暴病而亡的消息時,她是如此痛楚。后來,劉辟充任西川節度使,起兵謀反,還想通過她來籠絡人心。她堅持氣節,不肯同流合污。第二次,她又被發配到邊地。但是,這次赴邊,徹底地洗刷了當年的恥辱。后高崇文平叛,她被迎回。
元和四年的春天,她遇到了元稹。元稹小她十歲,年輕英俊,仕途得意,他不僅詩歌寫得卓爾不群,而且是顆多情種子。他們一見如故,風流才子連贊美之詞都與眾不同。“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多停筆,個個公卿欲夢刀。別后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云高。”他舌燦蓮花,令她心花怒放。她也回應:“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下詠花憐暗澹,雨朝題柳為欹垂。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好男兒。”是的,那片細膩風光,深深地迷住了她。后來,元稹喪妻貶官,她寄詩,其中“閨閣不知戎馬事,月高還上望夫樓”,儼然把自己當做了元稹的妻子。可是,元稹本就是個輕薄的人。他能寫“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來懷念亡妻,他也能一邊寄詩給她,一邊又愛上年輕貌美的劉采春,后又納妾安仙嬪,續娶裴淑。“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年復一年,她嘆息著,相思和春天一起老去。
暮年時,她得到年輕詩人杜牧的仰慕。“屏風周昉畫纖腰,歲久丹青色半銷。斜倚玉窗鸞發女,拂塵猶自妒嬌嬈。”在杜牧心中,身披道衣、手執拂塵的她,仍然如此嬌美。而她,此時已身心俱疲,回贈他“唱到白蘋洲畔曲,芙蓉空老蜀江花”。意思是自己已是明日黃花,空辜負了風流詩人的眷顧之心。
桃紅色的“薛濤箋”,適合寫旖旎情書。錦書難托,她還是不斷地制作。“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她默默地祈愿。于是,“薛濤箋”流入民間,盛極一時。
作者簡介:趙淑萍,浙江省作協會員,浙江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寧波市作協評論創委會副主任,海曙區文學家協會副主席。作品散見于《文藝報》《中國校園文學》《小說界》《小說月刊》《南方日報》《羊城晚報》等二十多種報刊雜志。有作品入選《新中國六十年文學大系》《中外經典微型小說大系》《中國兒童文學分級讀本》《微型小說選刊》《小小說選刊》等多種選本、選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