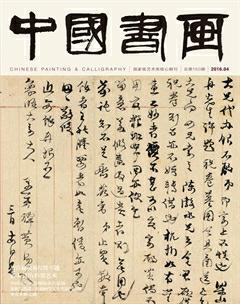宋克未解之謎
林霄


一、宋克在書法史中的歷史地位
宋克(1326-1387)字仲溫,號南宮生,又號東吳生,長洲人,元末明初書法大家。宋克因負詩才,又與楊維楨、倪瓚、高啟、徐賁、張雨、饒介、揚基、王行、施耐庵等交游。在元末的蘇松文化圈,宋克已經有很高的知名度。在書法方面,可以說,明初的頭一百年的書法家幾乎都在宋克的影響之下。明中期楊慎《墨池礫錄》卷三評:“本朝書當以宋克為第一,仲珩(宋璲)次之。”宋克的學生有陳璧,陳璧的學生是沈度、沈粲。而沈度被永樂皇帝稱為“我朝王羲之”,備受推崇,以致明初皆是宋克書風。至于其書后來被僵化為人所詬病的“臺閣體”,則非宋克之過。在元末,宋克書風突破了趙孟頫的書法籠罩,以章草筆法融入楷、行、草書,遒勁高古,卻是一種變革的力量。香港北山堂所藏宋克致高啟一札如此寫道:“子昂寫蘭亭十三跋,字畫精妙,謂能書可矣,謂極神妙,古今之所不許也!”其必以為自己蓋過趙孟俯的,可見自負如此。若將洪武三年(1370)的宋克書《錄趙魏公蘭亭十三跋》與趙孟頫相比,或可謂高下難論。
其青年時期的草書《杜子美壯游詩卷》,波瀾壯闊,筆意險絕。后有正統年間狀元商輅的題跋:“我朝英宗御極時,宸翰之暇,偶見其書,笑曰:‘仲溫何人,而書法若此,真當代王羲之也。其見重若此,嗚呼,自開辟以來,書法之神妙,惟王羲之一人,羲之之后,能繼其高風者,余亦曰仲溫一人而已。”說正統皇帝偶見宋克書法,驚乎其為“我朝王羲之”,試想其祖永樂皇帝若見到宋克書法,還會將宋克的再傳弟子沈度譽為“我朝王羲之”嗎?
二、宋克郡望及早年生平小議
香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近得宋仲溫《賢者帖》墨跡一冊十一開,綾本,被裁成條塊再成冊,為蓑衣裱。說明此冊原來可能是個立軸。雖然殘破,卻字字完好。款云:“至正廿六年,丙午建未月朔,廣平宋克序并書。”往日見其書作多署名“東吳宋克”,而署名“廣平宋克”者,本以為僅此一件,而華東師大教授丁小明先生友情提供另一例:《石渠寶笈》卷二十八《趙孟頫遺墨一冊》(上等)后有宋克題識云“龍集乙巳七月既望,廣平宋克識”,墨跡已不知下落,幸此冊刻于《三希堂法帖》第二十一冊,趙孟頫遺墨冊后,宋克此跋書于饒介題跋之尾,比《賢者帖》早半年時間。饒介、宋克皆稱由好友劉孝章出示索題。劉孝章,元末人,詩人宋存爵、顧瑛、周至堯皆有詩贈劉孝章,稱“劉孝章治中”或“劉孝章經歷”,可見劉孝章為元末江南文化圈內的官員,此處不考。而“廣平”為宋氏郡望之一,今在河北境內。以上兩件皆落款“廣平宋克”,說明宋克雖為長洲人,而其郡望卻是河北廣平郡,這一點從未有人提及,此時則可以確認。
對宋克郡望廣平的確認,正可以釋疑一卷臺灣收藏機構所藏宋克草書《杜子美壯游詩卷》。此卷落款處的題記:“右杜子美壯游詩,東吳宋克仲溫書于廣平之草堂。”此落款之地名確讓人有怪異之處,因為從未有文獻提及宋克曾到過廣平。《徐邦達集》第六卷對于此卷的按語是:“此卷書法和上錄《進學解》極相像,大約在差不多的時候寫的。元廣平路在今河北省境。宋氏不知在何年北游,待考。”徐邦達先生談到的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宋克草書韓愈《進學解》手卷,書于其家鄉蘇州的“南宮里”,時年二十三歲,為所知最早宋克書法。徐邦達的按語是:“此卷書法稍生硬,還不太成熟,但已有勁健氣,是他早期的作品。”從書法成熟程度來講,《杜子美壯游詩卷》雖與《進學解》屬于同一時期,但從書風的成熟度猜測,要稍晚于《進學解》。如果這件草書是真跡,那么不僅說明宋克的郡望為廣平,而且還在廣平寫下《杜甫壯游詩卷》。
宋克到過河北廣平是否還有其他的證據?明清以來,論及宋克生平,皆來自于一篇宋克摯友高啟的《南宮生傳》,如《明史。列傳。文苑》、王鏊《姑蘇志》、《江南通志。人物志。文苑》等。《南宮生傳》提及宋克年輕時的北游之行:“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陣法》。將北走中原,從豪杰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溯大江,游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搜覽瑰怪,渡浙江,泛具區而歸。”高啟記述宋克三十歲之際欲北上中原“從豪杰計事”,卻因路阻而返。而《杜子美壯游詩卷》上卻留下“書于廣平之草堂”之題記,相悖之處,或有蹊蹺。若做這樣的猜測或許可以成立:宋克這次的北游目的地正是其郡望“河北廣平”,以召集族人起兵為目的。時間在三十歲上下,也就是1355年即至正十五年前后。在這一年的前數年,已有下列事件發生:
1347年,河南山東農民起義:
1348年,方國珍在浙東起義;
1351年,安徽潁州劉福通等擁白蓮教
首領韓山童起義號紅巾軍:同年徐壽輝亦以
紅巾軍為號起義,稱帝于湖北薪水;
1352年,安徽定遠郭子興起義,朱元璋投軍郭子興;
1353年,張士誠于江蘇泰州起義;
1354年,劉福通擁戴韓林兒稱帝,朱元璋占據金陵。
在宋克三十歲之際,天下已亂,四方割據。可謂群雄逐鹿,但鹿死誰手尚不可知。這首《杜子美壯游詩卷》,或許表達了宋克北游的心境,卷中有句“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王”“群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正合其救亂濟世之情懷。然事不成,才回到蘇州,遂不生出山之念。甚至后來拒絕了張士誠的延聘。從此“乃刮磨豪習,隱默自將,履藏器之節”(高啟《南宮生傳》)。我們已經無從猜想北游發生了什么樣的事情,讓他發生了如此巨大的改變,以至于壯志全消。但《南宮生傳》所言北走中原未成,而事實上又留下了“書于廣平之草堂”的墨跡,此中矛盾又如何解釋?
高啟文集中有多首寫給宋克的詩作,如《春日懷十友。宋軍咨克》《醉歌贈宋仲溫》《醉贈宋卿》等。而一首《感舊訓宋軍咨見寄》(《高太史大全集》卷三),其中對于宋克生平的描述幾乎從未有人論及。此敘事體長詩敘述了宋克入明以前的大部分經歷,估計是作于高啟初識宋克之際。詩雖然不同于史料,但對于宋克生平來講,其中的一部分事實是可以被確定的。
高啟《感舊訓宋軍咨見寄》開篇:“我酒且緩傾,聽君放歌行。君歌意何苦,慷慨陳平生。”可見此詩依據宋克自述生平。其中“及壯家已破,狂游恥無成。太白犯紫微,三辰晦光精。金鏡偶淪照,干戈起紛爭。中原未失鹿,東海方橫鯨。遂尋鬼谷師,從之學言兵,石室得陰符,龍虎隨權衡”與《南宮生傳》完全可以呼應。但下面的詩句,則是與《南宮生傳》相抵觸的:“業成事燕將,遠戍三關營,巖谷雨雪霏,哀獸常夜鳴。撫劍起流涕,軍中未知名。奇勛竟難圖,回臨石頭城。石頭何壯哉,山盤大江橫。黃旗想王氣,玉樹沉歌聲。晚登臨滄觀,惻愴懷古情。覽時識禍機,不因憶莼羹。飄然別戎府,溧水還東征。裸衣佐刺船,臨危釋猜萌。歸來訪鄉間,亂余掩蓬荊。”此詩明顯說明以下事實:宋克曾有過從軍的經歷,北游之行甚至到達北方的“三關”地帶,只是無法判定是在哪一方面的軍隊呆過。接著寫“回臨石頭城”則是朱元璋占據的金陵,但不知為何又驚險地逃離金陵回到蘇州家鄉,“裸衣佐刺船,臨危釋猜萌”。袒身劃船的形象,可謂驚心動魄,跌宕起伏,這里面有多少故事,卻沒有說出來。有學者考證宋克與高啟相遇在至正二十年(1358)的云間徐伯齡處,說明此時宋克已經回到故鄉,在蘇松一帶盤旋,也與高啟在《春日懷十友。宋軍咨克》詩句“與君相逢在東州”相合,故此詩當作于此際。至于詩中為什么有“石頭何壯哉,山盤大江橫。黃旗想王氣,玉樹沉歌聲”的句子?難道是預見了朱元璋的未來?合理的猜想是,詩篇成集時已到了明初,此處或許動了手腳,不得不拍朱明王朝的馬屁。
而據《高啟年譜》作者考證《南宮生傳》作于洪武五年(1372)之際,也就是宋克出任鳳翔同知前后。不解的是,高啟在明初所寫的宋克,以上驚心動魄的從軍經歷到他的筆下變成了“將北走中原,從豪杰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溯大江,游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搜覽瑰怪,渡浙江,泛具區而歸”。好像連北走中原都沒有去成,便游山玩水而歸。前后所述差別這么大是什么原因?至正二十(1358)年前后高啟尚稱宋克為“軍咨”,而這“軍咨”又是為誰服務的?更是一個迷。不知高啟為好友作《南宮生傳》的用意,及此傳的用途?改朝換代之后,高啟對宋克的生平有所隱瞞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可見,高啟較早的詩作《感舊訓宋軍咨見寄》其敘事部分則比后寫的《南宮生傳》更為可信。
以高啟詩作《感舊訓宋軍咨見寄》所記宋克自述生平對照宋克早年草書《杜甫壯游詩卷》的落款:“書于廣平之草堂”,則可以坐實宋克的以下經歷:宋克早年從過軍,而且到過了北方,曾在廣平駐足,也呆過朱元璋的金陵。后世人們都將《南宮生傳》作為宋克生平的主要依據,是否被高啟有意地誤導了?
但這件書法冊的出現,不僅坐實了宋克郡望為“廣平”,而且對高啟《感舊訓宋軍咨見寄》《南宮生傳》所述宋克早年生平提供了一件物證,證實了宋克郡望是廣平的結論,并對其早年北游之行提供了一個較合理的目的地。《杜子美壯游詩卷》的題記,不僅證實了宋克北游之行真實存在,而且在位于北方的郡望廣平寫下了草書《杜甫壯游詩卷》。
三、宋克《賢者帖》歷史背景考
《賢者帖》六百多年來沒有收藏印記和文字著錄,在拍賣會也是首次曝光,僅有當代藏家鐘天鐸的題跋藏印,以及王季遷先生題首頁。
初見此冊時因各頁順序混亂,不能完讀,后經比對、調整每頁順序,竟然可讀,而且是一篇完整的宋克自作文。全文如下:
賢者游于庠序之間,必習乎俎豆之事。其材既成,則具文武之用矣,及出而施于邦家。論政而圖治。蓋無往不可焉。后世二道既眾武夫則攻騎射而遺詩書,儒者則談禮樂而忘軍旅。或見訾于巽儒,或取責于暴驕,相互詆誚而莫能一,然各視其時之所尚而輕重焉。故戴鷂弁者或負其勞,視縉紳之徒蔑如也。
陸君則不然,少以材勇從征于江淮,累功受閫職。日從儒先君子以講夫為治之道。庶乎必若君者謂文武之用者歟?今年夏。遂授杭州路治中。夫杭,東南之都會,密邇強梗。往年守者弗戒,已有城下之戰矣。今君之杭,登乎山川,視其有可憑,則設為備御之規。行乎田野,見其有可復,則興為墾辟之利。無事則教民忠義,有事則率民將之,使寇不能復來,而民晏然保其家室,以樂生送死,于千里之內,則君之功效并善,豈不偉歟?仆與君有交游之件,拜于君之行,敢以是為贈。
至正廿六手丙午建未月朔,廣平宋克序并書。(鈐印:東吳生、宋克私印、宋仲溫)
這是一篇寫給“賢者陸君”的贈文,這位陸君新任張士誠割據之下的“杭州路治中”。開篇所談:古代最早的學校是文武并學的,而后世文武分道,武者不讀詩書,文者不習弓矢,而又相互輕視。但這位“陸君”則不然,因文武雙習而被當權者重用。擔任“杭州路治中”之后,率領軍民加強防御工事,開荒造田,準備抵御當時環踞在周圍的“強梗”。此篇正是贈給陸君的贊文。
文中這位文武全才的“賢者陸君”為何人?文中之“強梗”又是誰?還要回到元末戰火紛飛的年代里去尋找。
元末天下大亂,各路英豪逐鹿中原。蘇杭一帶為張士誠所據。南宋故都杭州,也在張士誠的治下。至正十七年(1357)的張士誠雖名義上投降了元朝,實為武裝割據。至正二十六年(1366),宋克寫下《賢者帖》之際的杭州,北有朱元璋,南有方國珍,環顧周圍并視其為敵手,也就是文中所說的“密邇強梗”。據《杭州府志》,杭州城于至正十八年(1358)為張士誠從元軍手中奪下。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分別派紹榮、常遇春攻打杭州不下,故文中有“往年守者弗戒,已有城下之戰矣”。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冬十月,朱元璋為了配合徐達攻取蘇州,又派李文忠取杭州,十一月,張士誠部下潘元明率城投降,自此,杭州為朱元璋所得。次年徐達攻克蘇州,朱元璋開始稱帝。
宋克作此文,時值六月,杭州尚未易手,而朱元璋已經消滅了陳友諒勢力,正對江南張士誠的割據勢力構成極大的威脅。這位“陸君”就是張士誠手下的新任的杭州路治中。“路治中”在元代屬從三品文職官員,官職不高。查《杭州府志》官職表,元代部份十分簡略,至正二十四年(1364)以后缺略。時值亂世,又是張士誠據杭期間,在《杭州府志》中竟然沒有陸某的信息。陸君被任命為“杭州路治中”不久,杭州就被朱元璋所取,時間很短,不為史書所載,也屬合理。但功夫不負有心人,終于在揚州乾隆年間修的《興化縣志》中找到了這位“陸君”的信息:
陸謙,字仲益,復(指陸復,時昆山知府)從子,元未為杭州路治中。明兵平浙右。方國珍猶據甌越數郡,詔選通練才辯者喻之,謙往,喻以度德量力,無滋后悔,國珍遣使輸款。又嘗單騎招張鑒于揚州。鑒服其義,不忍害。授戶部主事改知廬陵縣,時有誣縣民反者,將盡誅,謙以家口保之,一邑獲全。轉湖廣都司斷事,征銅鼓蠻撩與有功,祀鄉賢祠。子闿容別有傳。以上舊志。
又查《廬陵縣志》官職表,陸謙于洪武十五年(1382)任廬陵縣知縣。
據揚州《興化縣志》,這位陸謙降明后,以通練的才辯招降尚割據福建的另一只起義勁旅方國珍,還單騎前往揚州招降另一只起義軍張鑒(張明鑒,青衣軍首領,據揚州,后降明),立了大功。在廬陵縣任上時,有人被誣告造反,全族將被誅殺,而仗義的陸謙敢以全家性命擔保,使人一家得以保全。但陸謙的史料實在不多,僅此而已。但寥寥數語,已經勾勒出這位智勇雙全、膽大心細、能言善辯、行俠仗義者的形象,正像文中所言:“陸君則不然,少以材勇從征于江淮,累功受閫職,日從儒先君子以講夫為治之道。庶乎必若君者謂文武之用者歟?”可見宋克沒有看錯人,但是這篇贈文作于張士誠時代,其的政治立場明顯是站在張士誠一方的。
《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的朋友中有位陸謙,由于時代交集,而且他們都是興化人,又都在蘇州生活過,所以這位陸謙很可能是同一人。《水滸傳》中有林沖的朋友陸謙,為高太尉獻計陷害林沖下獄,最終被林沖殺死。施耐庵何以將小說中最令人厭惡的人物安上了朋友陸謙的名字?他們之間有何過節?這方面的史料太少,難以猜測。
再看《明史。文苑傳。王行傳》附錄,對宋克的描述:
(宋克)偉岸干,博涉書傳,少任俠,好學劍走馬,家素饒,結客飲博。迨壯,謝酒徒,學兵法,周流無所遇,益以氣自豪。張士誠欲羅致之。不就。……杜門染翰。日費十紙,遂以善書名天下。
宋克的形象與這位陸謙有些相似,文武雙全。物以類聚,遂成為朋友。而在亂世中的宋克似乎悟到了什么,自從脫離軍旅回到故鄉,“辟一室,庋歷代書法,周彝漢研,唐雷氏琴,日游期間以自娛”(見高啟《南宮生傳》)。
作《賢者帖》時,宋克四十歲,次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蘇州城破,張士誠被殺。徐達兵臨城下時,張士誠的女婿潘元紹,逼家中七姬同日自盡,命張雨撰文,宋克書丹,立成楷書《七姬權厝志》,勒石成碑,為其小楷名作,文獻所知宋克在元代的活動以此為終結。
四、宋克最后十六年去向成謎
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登基,為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對江南大多數文人賢者曾經被張士誠延納,心懷怨恨,除了對江南諸地課以重稅,更在洪武年間,將江南的這些文人、藝術家大多無情絞殺。如饒介、楊基、徐賁、陶凱、王蒙、高啟、趙原、陳汝言、張雨、王行、王彝等皆非正常死亡,他們大多是宋克的好友。宋克入明以后去向,最明確的記載是洪武四年(1371)赴任鳳翔同知,但奇怪的是,從洪武四年到洪武二十年(1387)的十六年間,僅有一件作品見于清中期的《石渠寶笈三編》記載,就是作于洪武二十年的《臨急就章卷》,也是這十六年間唯一存世的一件,而且這件他存世最后一件書作極不可靠。若如是,從洪武四年以后,宋克就如人間蒸發了一樣,沒有一件可靠的作品傳世,也沒有一個同時代的文獻記錄他的活動,這不得不令人生疑。
這件《臨急就章卷》現藏于天津藝術博物館,作于洪武二十年,鈐有“仲溫”一章。筆者以為,這件《臨急就章》,是一件非常可疑的“宋克絕筆”。理由如下:1.無宋克款:2.題記:“洪武丁卯六月十日臨于靜學齋”,現存文獻作品,從未見過宋克有“靜學齋”的齋號;3.書法與已知宋克章草書法極不類,特別是從書法演變的角度看宋克,可以發現,從最23歲的《進學解》到,30歲上下的《杜子美壯游詩》,到39歲的《賢者游于庠序》,再到44歲的《錄趙魏公蘭亭十三跋》《四體書陶詩并竹窩圖》,將已知的宋克書法按照時序排列,可以看出宋克書風由飛揚險絕到趨于含蓄內斂的轉變,如果到了晚年突然變出如此夸張失度的結字和筆法,是不符合一個書家發展規律的,比較44歲書寫的章草到這件所謂62歲的章草,筆法失度,功力不在一個層面,如何可信;4.其鈐印“仲溫”,未見同一方鈐于其他作品。所以很懷疑是一方偽印鈐于一件佚名的章草作品之上。
明初,漢人將蒙古統治者終于趕出了中原,建立了大明政權,這些江南文人曾經對新皇朝心懷憧憬,紛紛出來做官,但結局卻是悲慘的。朱元璋心底里厭惡這些曾經被張士誠禮遇的文人,所以在明初的幾個大案中,紛紛被牽連,下場可悲。高啟《南宮生傳》寫宋克拒絕被張士誠延聘其帳下,但是在后人所輯高啟詩集中卻留下標題為《宋軍咨克》《感舊訓宋軍咨見奇》的詩篇,難免不讓人懷疑“軍咨”一職乃為張士誠所封。至少宋克與其他曾經服務于張士誠的文武官員交游甚密,不被清算也是難以想象的。宋克的摯友高啟,于洪武七年(1674)因《上梁文》案被腰斬,對于宋克來講,一定是個巨大的刺激,他會做出怎樣的反應?他是像其他朋友們那樣死于非命還是隱姓埋名逃出升天?目前各類文獻所謂宋克卒年的依據皆來自于解縉文集記載:“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官鳳翔府同知,卒于其地,時洪武丁卯(1387)。”解縉卒子1415年,距離宋克的卒年僅晚28年,這個記載按理具有權威性的,但可惜的是至今未發現任何其他的交叉證據,從洪武四年(1671)到洪武二十年(1681)這十六年間,成了宋克生平事跡的空白期。宋克究竟是得以善終,還是死于非命?以學術觀點來看,宋克這最后十六年終究還是個謎,這個謎或許還需要等待更多的數據出現才能破解,或許永遠也無法破解。
責任編輯: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