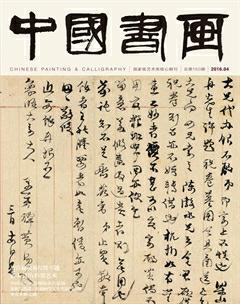論中國書法前藝術階段的日常書寫及相關問題
曹興章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談到:“夫(文字)變之道有二,不獨出于人心之不容己也,亦出人情之競趨簡易焉。繁難者,人所共畏也:簡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導其所喜,握其權便,人之趨之,若決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從之矣。”由此看來,漢字形體總體的演變趨勢是簡化,這種簡化是人們在長時期的書寫過程中不斷趨繁為易的結果。文字由象形符號發展到甲骨文、金文而形成篆書,進而由篆到隸,由隸到真、行、草,書法藝術也隨著文字的演變過程逐漸發展開來,可以說,中國書法是與漢字共生共長的藝術門類。20世紀以來,大量考古新材料(如簡牘、殘紙等)的發現,為我們呈現了傳統視野之外的另一書寫世界,帶來了對書法史進行重新審視的全新視角。簡牘、殘紙等這些新發現大多是日常書寫,因此,“日常書寫”便成為窺探中國書法發展的另一窗口。
漢末魏晉時期,書法脫離實用而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故而筆者認為日常書寫應分為兩個階段:書法藝術獨立之前的日常書寫與書法藝術獨立之后的日常書寫。這兩個階段的日常書寫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前者主要是以實用為主,而后者則與書法創作交織,這時書家們日常書寫的尺牘、便條、草稿等往往會帶有創作的意味。如唐人孫過庭《書譜》記載:
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后答之,甚以為恨。
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
由此說明,書法藝術獨立之后,書信除了交代內容之外,更注重顯示書寫水平,日常書寫成為轉換到書法創作的一個環節,尺牘已經成為書法創作的一種形式。書法獨立之后的日常書寫與書法創作已經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并且這些經典已經成為后世學書的圭臬,因此備受人們的關注,然而卻很少人對書法藝術獨立之前的日常書寫進行研究。
先秦至兩漢時期是書法藝術發展的重要時期,可以說無論是書體的演進與簡化、筆法的豐富以及書法形制、形式的確立都與日常書寫密切相關。當代著名書法理論家侯開嘉先生曾指出:“從先秦到漢代末年,書寫漢字的功能主要是為了實用,其次才是表現漢字的造型和線條的美。因此,我們把這大約三千年的歷史稱之為中國書法的前藝術階段。”本文引用侯先生的觀點,并專門對中國書法前藝術階段的日常書寫及其相關問題展開討論。
現代考古發掘將幾千年前古老的書跡公諸于世,傳說中的“倉頡造字”并非空穴來風。只不過文字的創造絕非一人能為之,與“倉頡造字”類似的“史籀制大篆”、“李斯創小篆”、“程邈造隸”、“史游創章草”、“王次仲創楷”、“劉德升創行書”,這些“創造者”應是文字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整理者,每一次文字整理都是官方對日常書寫的承認、美化與規范。
(一)甲骨文、金文時期的日常書寫
很多學者著書立說,認為我國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青銅器上的金文,那么它們屬于日常書寫應用的文字么?我們知道,甲骨文是用于占卜的,屬于宗教文字:青銅器的制作是國家行為,比如要公布法律、記錄戰爭等大事才會鑄造有文字的青銅器,這些都是莊嚴的大事。那么日常的書信、便條應該是怎樣的?筆者認為,特定的書寫載體有特定的用途,絕非是普通大眾化的日常使用,而真正流行于民間大眾書寫的才是日常書寫的載體。有了文字,就必須有書寫文字的載體,甲骨文與金文時代必定也有一種日常書寫文字的載體,從甲骨文中存在“冊”“典”兩字足以為我們透露出一些信息。周代《尚書》中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漢字之始,起于象形,從“冊”“典”字的形狀來看即是20世紀大量出土的竹木簡牘的象形字。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中這樣闡述:“金石盤盂都是有為而作,真正的古代文化,應靠竹帛來記載。”我們的祖先在文字的日常書寫過程中不斷地尋找適合的載體,我們在古代文獻中常會看到他們在地、墻、樹等上面書寫的記載,但是他們最終找到了竹木簡牘作為日常書寫材料。侯開嘉先生亦認為竹簡應是最早書寫漢字的主要材料,并且給出了合理的理由:“第一,材料要易得、量多、價賤:第二,要易于大量制作:第三,要方便書寫和匯集保存:第四,要有制作材料的工具。竹子這種植物就符合前三個條件。另外,現代考古發現表明,公元前兩千多年的時候,我國中原地區已不像人們常說的還處于石器時代,而那時候的青銅冶煉技術已經普及了。因此,第四個條件,即制作竹簡的刀具應具的條件在那時已經成熟了。”由此可知,文字是社會化的東西,只有在普遍意義的書寫載體上才會產生所負載的意義及應用作用。甲骨文是書寫或契刻在龜甲和牛肩胛骨上的文字,是官方指定貞人專門為記錄求神問卜的特殊文字。金文為青銅器皿上鑄造的文字,銘文內容多與祭祀、征伐、錫命、契約相關。顯然,甲骨文、金文不屬于日常應用書寫的范圍,它是帶有官方、宗教性質的書寫。也就是說,甲骨文、金文并非日常書寫的文字,其材料也非日常書寫、普遍應用的載體。此外,現代考古發現戰國時期的玉石書寫的《侯馬盟書》、《溫縣盟書》、帛書等,其書寫材料亦十分特殊,在大量的書寫中只能占據很小比例,并不能當做日常書寫大量應用的材料。從目前考古發掘來看尚未發現殷商春秋時期的書寫實物,其日常書寫到底是什么樣子就不能證實了,不過我們把殷墟出土的白陶片墨書“祀”字,與春秋晚期出土的《侯馬盟書》玉石手書文字進行對比分析,推斷在甲骨文之前至少經過一次大規模的對日常書寫進行的美化、規范的文字整理。由于簡牘易于腐朽毀壞、難于保存,現在存世最古老的日常書寫實物是近代出土的戰國晚期的秦簡、楚簡。
秦國直接承襲周文化,其官方文字為籀文,即大篆。目前,最早的當時的日常書寫書跡是出土于四川青川縣郝家坪的《青川木牘》(前309年),由它已處于早期隸書的形態來看,可以說在其之前相當漫長的一段時期里,在大量的日常書寫過程中不斷地加速文字的演變。根據春秋戰國時期的出土的實物資料,如《秦公簋》、《商鞅戟》、青川木牘、簡書等來看,小篆在春秋時期為日常書寫應用性文字,而戰國時期則是小篆與古隸并存。
(二)小篆時期的日常書寫
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戰亂頻仍,秦始皇滅六國而統一中國,為了對幅員遼闊的疆土進行有效的管理與統治,秦統治者建立了一系列的強化政策,其中在文化方面實行的一項措施為“書同文字”。許慎《說文解字。序》云:“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徐無聞先生曾經運用大量史實著文作出“小篆是戰國期間秦國通行的文字”的結論。根據侯開嘉先生的《俗書與官書的雙線發展規律》一文可知,在中國文字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俗書與官書兩大體系現象。所謂官書,即是在特定時期內,官方認定的和社會公認的莊嚴鄭重的書體:所謂俗書,即是民間流行的手書體。其中所言“俗書”即是日常書寫的應用性文字。秦始皇推行“書同文”,把秦國通行的小篆作為全國統一的文字。并由李斯、趙高、胡毋敬等人對小篆的結體進行整理成為標準的官方文字。秦書八體只能稱為大篆、小篆、隸書三種書體,其他的都是因用途不同而作為有指向性的書體來運用。而此時小篆、大篆作為特定場合使用的官方書體,實質大篆已經居于次要位置,所以日常書寫應用的是隸書。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夢縣睡虎地的《云夢秦簡》以及1983年3月出土于甘肅天水市放馬灘的《天水放馬灘秦簡》,這才是當時日常書寫的真實面目,它是小篆在日常書寫的簡化作用下,發生了隸變,形成的一種比小篆更加簡化、便于書寫、初具隸書形態的文字。至今在湖北、四川、甘肅等地的秦墓中出土的竹木簡牘,內容多為抄寫日常相關的《秦律》《日書》等,字體為古隸,這說明在戰國末期的秦國至秦朝,在小篆退出日常書寫的舞臺而成為官書的時期,日常書寫的書體就是這種古隸。
(三)漢碑時期的日常書寫
進入兩漢時期,書法藝術的發展呈現出一次重要的飛躍,四百余年間,小篆、隸書、章草、今草、行書、楷書都在這期間的日常書寫過程中交替,尤其到了漢代末年,書寫條件的成熟,尤其紙的改進與廣泛應用使得書法邁向了藝術的獨立階段。漢代日用文字已經完全使用了隸書,從西漢初的尚未完全擺脫篆書成分的古隸,在日常書寫過程中逐漸發展成全用方折筆畫、結體簡約趨扁的成熟隸書,有的是帶有波挑的八分隸書以及章草書,甚至今草、行書、楷書形態已具初型。漢代分為西漢與東漢兩個時期,下面分別述之。
據不完全統計,至今保存下來的西漢時期的金石碑刻十余種之多,這些銘文均為小篆的字體,而這些碑刻均為官方應用的書寫產物。20世紀以來,在我國西北及山東、湖北、湖南等處,出土了從戰國到晉代的大批竹木簡,同時還有少量的殘紙和帛書,這些新資料的發現為我們展現了當時日常書寫的真正面貌。其中西漢時期的簡牘占據很大的比例,時間上從西漢初期到西漢晚期的新莽時代。如西漢初期的《老子乙本》簡中已經出現規整、成熟隸書的雛形,這也許就是“程邈創隸”后整理出來的隸書面貌。我們再看西漢中期的《延壽太初三年簡》等,可以說完全擺脫篆書的成分而完全是成熟隸書了。西漢時紙已經出現,但由于生產力低下而未能大量普遍使用,但到了東漢時期,蔡倫等對制作紙張的技術進行了改進,臻至漢末,書法用紙已經具備很高的質量。到了魏晉時期,紙張得到了廣泛應用,簡牘遂遭廢除。由此看來,兩漢時期主要的書寫載體還是簡牘。
到了東漢時期,立碑之風盛行,漢碑林立。此時篆書官方地位已經居于次要,轉變成碑額使用的裝飾文字,成熟莊重的隸書稱為官方文字。而在此時的日常書寫的書體出現了新的變化,已經出現章草、楷書、行書、今草的字體。從留存及考古發掘的簡牘、陶瓶、磚石上來看,隸書的形態已經十分模糊,如《玉門官隊次行簡》已經是楷書面目了,《毫縣曹氏墓磚》中已經出現獨立成篇的行草書。由此表明,東漢的日常書寫是章草、今草、行書、楷書嬗變交替的。
由上文可知,日常書寫始終主導著字體演進的方向,同時在書寫過程中產生了新的筆法,并在約定俗成中被整理美化而轉化成官方書體,可以說“日常書寫”對中國書法前藝術階段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字體簡化作用
日常書寫的內容上往往是公牘文稿、尺牘抄文,因而其目的旨在方便、實用、快捷。為了適應瞬息萬變的時代發展,因而在書寫的時候勢必要追求陜速、簡單。如古文中的“圍”字本是畫四個足形在一個城邑的四面,表示包圍。書寫在竹簡上就很不方便,為追求陜捷就省去左右兩個足成為“韋”字,等等,可以說此種例子不勝枚舉。像這種為了在書寫載體的限制前提下,達到日常書寫中方便、快捷的效果就不得不對許多繁雜字進行簡化,可以說這種對漢子的取繁為簡、創造新字都是在書寫過程中完成的,最后這種簡化而約定俗成,之后被大家承認而大量應用。
(二)書法形制、形式的確立
如今我們廣泛使用的日常用語中的“文牘”“信札”“編”“卷”等詞匯無不彰顯著古代日常書寫的豐富多彩。可以說書法形制、形式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的日常書寫中被逐漸確立起來的,其中,不能忽視日常書寫材料這一重要因素。在中國書法的前藝術階段,竹木簡牘是日常書寫的主要材料,因而簡牘的形制影響到書法形制、形式的確立。竹木簡牘形狀窄而長,或者先寫后編,或者編后再寫,這種簡冊的形制形成了中國文字由上而下、自右而左的固定書寫款式,同時這種竹簡的窄而長的樣式則對中國漢字產生了影響,比如,原始象形文字是屬于很寫實的,在書寫過程中受到簡牘形制的限制,一些如“象”“馬”等橫形字形變成豎形字:最后在書寫的過程中逐漸地把漢字變成了方塊字,在竹簡上書寫由于受到左右方向的限制而只能在上下方向伸展,但是竹簡形制較小而不允許在上下方向任意伸展,就這樣在日常書寫過程中,文字逐漸變成方塊形狀被固定下,一直延續到今天,漢字還是方塊字。
(三)豐富筆法的作用
由于日常書寫具有隨意性,故而在書寫的過程中會產生一些新的筆法,一旦被約定俗成而總結固定下來,那么另外一種新的字體就誕生了。比如,在簡牘的日常書寫中,大篆書寫中受到簡本身形制的影響,追求簡單、對稱的筆法產生了:之后到了小篆的書寫時,面臨由圓變方向趨勢,大量的書寫中左舒右展、蠶頭燕尾的的筆法出現了:在漢簡隸書的書寫過程中,波折的形態不斷地被弱化,快捷書寫中鉤、挑、捺等形態的楷書筆法出現了,進而在簡化書寫過程中草書出現了,字字相應帶的行書現象出現了。在左右書寫的慣性中提按、使轉、緩急等元素被人總結肯定下來,貼別是書寫材料由簡牘到紙張的過渡過程中,更是促進了它的轉變,書寫幅度變大、自由度放寬、連帶性更強,因而表現筆法方面更加豐富,最終使得書法由實用過渡到藝術階段了。由上述可知,每一次書體演變都是對前一次書寫過程中筆法的肯定與美化,如小篆是對大篆的減省與美化,漢碑是對漢簡的肯定與美化,楷書、行書、草書是在隸書的日常書寫中產生新筆筆法的肯定與發展,最終這些筆法元素被美化后固定下來成為今天紛繁多姿“真草隸篆行”——五體書具備。
綜上所述,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離不開日常書寫,在書法藝術尚未獨立的前藝術階段,無論是書體的演進與簡化、筆法的豐富以及書法形制、形式的確立都與日常書寫密切相關,這一階段的日常書寫為中國書法藝術風格的演變塑造了一個完美的體格,在藝術獨立之后的不同歷史時期的日常書寫過程中不斷產生不同的藝術風貌。
責任編輯:歐陽逸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