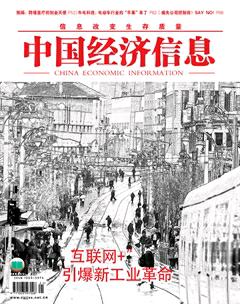智能種植系統
2015-11-12 09:09:53
中國經濟信息 2015年21期
這套名為“Plug&Plant”的智能種植系統最大的優勢就是把原本應該擺在地上的盆栽掛到墻面上,有效節省空間。采用模塊化的種植方式,先將整體框架固定在墻壁上,而后再將裝有培育用智能泡沫和植物種子的生長模塊裝進框架中即可完成。Plug&Plant智能種植系統除了可以掛在墻壁上種植之外,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土壤。在每個種子生長模塊中都使用含有營養成分的智能泡沫替代傳統的土壤。這種智能泡沫可以給植物根部充分的生長空間,確保種植在最頂端的植物根部也可以延伸到最底端的泡沫中。該系統可以將每次澆水后多余的水存儲起來,從而使最長澆水周期達到一個月。endprint
猜你喜歡
小讀者(2021年2期)2021-03-29 05:03:48
華人時刊(2019年13期)2019-11-17 14:59:54
文苑(2018年23期)2018-12-14 01:06:06
文苑(2018年22期)2018-11-19 02:54:14
文苑(2018年19期)2018-11-09 01:30:14
文苑(2018年17期)2018-11-09 01:29:26
文苑(2018年21期)2018-11-09 01:22:32
紅領巾·萌芽(2017年5期)2017-06-23 10:35:59
爆笑show(2016年7期)2017-02-09 09:36:13
紅領巾·萌芽(2016年1期)2016-09-10 07:2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