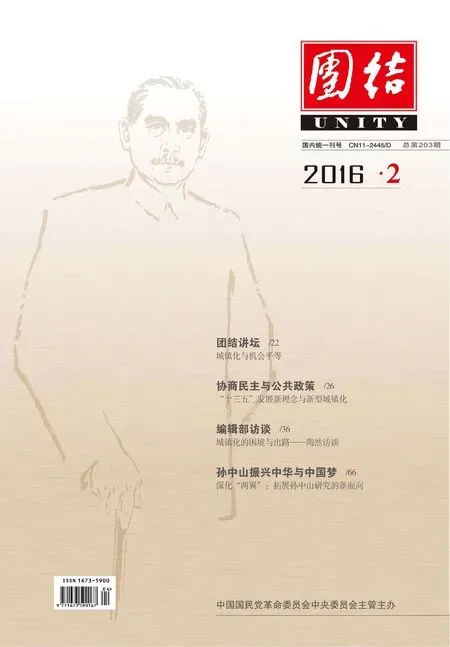經典重讀 《左傳》表達的古代智慧(二)
◎吳先寧
經典重讀《左傳》表達的古代智慧(二)
◎吳先寧
前面說過,智慧是關于“是什么不是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等根本性的問題的判斷能力,所以,與“聰明”常常跟“小”聯系在一起稱作“小聰明”相反,智慧往往跟“大”聯在一起,有“大智慧”一說。然而也往往因為大,人們也常常覺得這些“大智慧”大而無當,婦孺皆知,毫無新意,誰都會說,誰都知道。于是充耳不聞,視而無睹。
比如,《左傳》里的“曹劌論戰”一篇,可謂是人人皆知,因為它一直以來都入選中學語文課本。文章不長,估計許多人讀中學的時候都是熟讀背誦,滾瓜爛熟。我們熟知“一鼓作氣”這個成語出自這一篇;更進一步,也知道這篇里有“肉食者謀之,又何間也”(意即:“那些當官的搞的事情,我們干嘛去摻乎。”)這樣的憤激之語。大多老師在講解的時候,也都是在這些地方津津樂道,大加渲染。然而,有幾個人注意到這篇文章講的一個大道理,就是“司法公平”,是戰爭勝負的一個主要條件。
公元前684年,也即魯莊公十年,齊國來攻打魯國,魯國國君魯莊公當然要率師迎敵,已經調動軍隊,準備打仗。這時候,曹劌來求見魯莊公,問了國君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曹劌的問題是,國君你想憑什么打贏這次戰爭。這個問題富含深意,因為當時齊國是大國、強國,魯國是小國、弱國。假如魯國比齊國大而強,那么靠實力的大而強也就可以了,一目了然,不必問。假如兩國的實力旗鼓相當,堪可匹敵,那么多談一些迎敵的戰略戰術,在這些方面獻計獻策也就可以了,不必問。因此,必須擁有根本性的致勝之道,才可言戰,否則就談和好了。
魯莊公當然知道曹劌的深意,所以他也壓根沒有拿實力說事兒,而是回答:“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也就是說,國君有好吃好穿的,肯定會與他人分享,不會一人獨占。然而曹劌認為,這些小恩小惠,只能施及國君周圍的一小群人,也就是一些小小的利益集團、利益群體,作為戰爭主力的普通老百姓和兵士并沒有享受到,所以此舉并不足以激勵士兵和人民與你同仇敵愾地參戰拼搏,故這不是致勝的根本憑藉。
于是魯莊公又接著說:“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意思就是供給鬼神用的祭品,都是如實統計、如實地向神們報告,不敢虛報、不加水分。然而曹劌又認為,這種對鬼神的誠信只是一種“小信”,神們并不看重,因此也并不會來全力保佑你的國家,所以這也不是致勝的根本憑藉。戰爭致勝依靠的是對國家、人民的大誠大信。

連著兩個魯莊公自己認為的最重要的致勝法寶都被曹劌否了,莊公有點急了,想了想最后說:“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這最后一個,曹劌認同了。曹劌認為,大大小小的案件,即使不是每個案件,案件的每個細節都能明察秋毫,但司法者如果都會準情度理,以最大最深的誠意力求公平地決獄,達致最大程度的司法公平,這才是戰爭致勝的根本因素。因為這體現了統治者對國家的最高忠誠,也使得人民最廣泛、最根本地受惠。只有這一司法公平下最廣泛、最根本的受惠,才使得人民認同你的國家,認同你的統治,與你同心同德,同仇敵愾,并肩與外國入侵者作殊死的搏斗,去爭取戰爭的勝利。因此,曹劌認為,魯莊公力求司法公平,是“忠之屬也”,有了這一條,就可以跟強敵一戰了。
接下去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曹劌跟從魯莊公出戰,在戰術上幫助莊公掌握攻守的節奏,其中就說到了如何“一鼓作氣”,而最后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司法公平是戰爭致勝的法寶,是打仗最根本的憑藉,起碼也是之一,這是《左傳》這部古書揭示給我們的智慧。因為司法公平是最普遍、最廣泛的公平,是所有公平中的底線公平,一人遭遇不公,全家啼哭,全村憤懣。一案公平,全家顏開,人人起信。沒有司法的這一公平,其他所有公平就沒有了基礎,都將面臨崩潰。只有司法公平,才能在底線上守住人民對政權的信心和認同,守住老百姓對國家的忠誠,才能是戰場上三軍將士,皆如挾纊。試想一個司法者貪贓枉法、冤獄遍于國中的地方,讓老百姓遵守日常規則都很困難,怎么能讓他們與國家共患難,赴戰場冒死殊殺,流血犧牲?
《左傳》在對歷史的敘述中揭示的這一政治智慧,也是顯而易見的大道理。但正因為它大而顯,并非枕中秘計,掌上神器,所以中國歷史的千百年中,并非能引起人人關注,特別是沒有能引起歷代統治者的關注,“包公戲”的流行,恰恰說明司法公平的稀缺。不要說沒有引起中學語文老師的特別關注,就是專門研究戰爭的,如中國古代最為著名的研究戰爭規律的《孫子兵法》,被奉為西方近代軍事理論的經典之作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就都沒有提到司法公平在戰爭中的根本作用。
《孫子兵法》第一篇《始計篇》,是戰爭的總論,講的是“廟算”,即出兵前在廟堂上比較敵我的各種條件,估算戰事勝負的可能性,并制訂作戰計劃。是從宏觀上對決定戰爭勝負的政治、軍事等各項基本條件進行比較、分析和研究,并對戰爭的發展進程和最終結局進行預測,尤其強調用兵前的周密謀劃對戰爭勝負的決定作用。其中講了“慎戰”,講了“五事七計”,講了“詭道十二術”,但都沒有講到司法公平對戰爭的根本性影響。《孫子兵法》數千年之后,被譽為影響歷史進程的100本書之一的《戰爭論》,作者克勞塞維茨號稱研究了1566~1815年期間所發生過的130多次戰爭和征戰,本書中他對戰爭的性質做了如下定義“戰爭是政治的工具;戰爭必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戰爭就其主要方面來說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這里以劍代表,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規律進行思考了。”這一論點,據說得到了列寧的極高評價,但遺憾的是,該書也沒有一字提到戰爭與司法公平的關系。是他沒有讀過《左傳》,由此對其中的古代智慧一無所聞?還是因為司法公平對于戰爭的根本性作用太過顯豁,因而不必一提?這其中的原因我們就不知道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