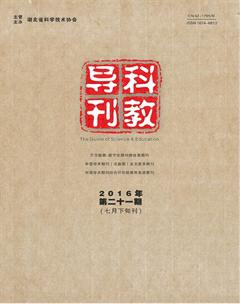論大數據對圖書館員的能力要求
劉瑜
摘要 數據館員是大數據時代對圖書館員的必然要求;從圖書館員到數據館員不僅僅是名稱變化,更是工作方式和服務模式的徹底轉型;因此數據館員必須具備比圖書館員更高要求的技術能力、創新能力和服務能力。
關鍵詞 大數據 圖書館 圖書館員 數據館員 知識服務
中圖分類號:G250.7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j.cnki.kjdkx.2016.07.087
大數據從提出至今,已有三十多年歷史,但是尚未形成統一的定義。由于大數據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因此,研究者對大數據大都只做了定性的論述,而并沒有給定量化指標。但是梳理和分析有關大數據定義的文獻不難發現,大數據是一種數據集,大數據的價值體現在它反映的內容上。它不同于傳統的數據管理及處理技術。大數據時代的圖書館面臨雙重夾擊:一邊是一些IT公司憑借技術優勢推出的“一站式智能搜索引擎”正迅速吞噬著圖書館提供的OPAC服務;另一邊是大數據服務機構推行的量身定制服務正日益吸引著圖書館的傳統用戶。印度圖書館學家阮岡曾經說過,只有貼近社會,重視讀者需求,積極引進新的技術為他們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服務,圖書館方能在社會找準位置并不斷發展。目前,圖書館的技術優勢和服務優勢已經喪失,用戶流失、貢獻邊緣化、價值遭質疑在所難免。圖書館要擺脫當前的生存危機,無疑需要對圖書館員的技術水平和服務質量“兩手抓”。圖情界研究者普遍意識到“數據館員”是大數據時代背景下圖書館員的基本要求,然而他們卻又對數據館員的基本素養、評價標準和任職條件等語焉不詳。鑒于此,本文基于“圖書館員是承擔數據監護任務的理想人選”的立場,根據大數據的內在要求及其它對圖書館產生的實際影響來探討數據館員的能力素養問題。
1大數據對圖書館員技術能力要求
不難看出,解決大數據的主要矛盾的關鍵是提高人類對大數據的掌控能力。大致說來,“大數據掌控能力”包括數據搜索能力、數據獲取能力、數據存儲能力、數據挖掘能力、數據分析能力、數據轉化為知識的能力,數據安全防范能力和數據應用能力八個方面。提高人類大數據掌控能力,除了期待大數據技術手段取得革命性突破外,更要取決于每個個人運用技術的水平不斷提升。對于圖書館員而言,要具備上述大數據掌控能力,不僅需要掌握圖書情報學、檔案學等傳統專業知識,還需要熟練掌握信息管理學、計量學、心理學、語義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學科知識,更要對大數據的基礎理論、技術思想、應用方式有深刻理解。在必備的大數據技術方面,圖書館員目前需要掌握就有OPAC統計、可視化分析、相關性分析、數據挖掘、圖形分析、文本分析、預測分析、語義分析、空間分析等。需要掌握的程序軟件那更是不勝枚舉。有學者指出,如果一個圖書館員真正能夠通曉上述領域的知識和技術,他的知識結構和技能素養也就與IT巨頭眼中數據工作者、數據科學家相差無幾了。
美國圖書館協會明確提出,研究數據管理將成為下一代圖書館員的能力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講,圖書館員要實現向“數據館員”角色轉變,必須努力把自己培養成跨學科的交叉性、復合型人才——目前,這樣的人才在全世界都是稀缺資源,僅美國就有大約200萬的缺口。更為困難的是,由于圖書情報學中的大數據學科體系尚未構建起來,人們對于“怎樣培養大數據服務館員”也毫無頭緒。目前,一些美國高校圖書館做法是,專門設置“數據館員”崗位,并把它作為一項特色性服務活動和前沿性科研課題加以推廣,不斷在實踐中探索總結。我國圖書館界也應積極行動起來,走這種“由做到學、邊做邊學”的大數據人才培養路徑。
2大數據對圖書館員創新能力要求
迄今為止,圖書館服務模式經歷了“文獻服務一信息服務一知識服務”三個發展階段。這充分反映了圖書館服務從“依賴資源”到“依賴技術”,再到“越來越依賴圖書館員的智慧”。知識服務是一種高階的文獻信息服務范式,它要求圖書館員圍繞讀者用戶解決特定問題的需求有針對性地去把那些零散的文獻、信息、數據按照一定邏輯整理成知識,從而為讀者提供一套解決該問題的最優方案。由此不難看出,知識服務的勝任者,已經遠遠超出了“圖書館員”的傳統涵義。
當今時代,數據已成為知識構成的最主要來源之一,但數據本身還不是知識,因為“傳統意義上的數據、信息和知識具有完全不同的概念。數據是信息的載體、信息是有背景的數據,而知識是經過人類的歸納和整理,呈現規律的信息”。0圖書館的最基本職責是提供知識服務,然而數據要轉化為知識卻需要一個人工轉化過程。再從數據類型上講,完全意義的知識是以事務為中心的結構數據,而占85%以上的數據卻是半結構數據和非結構數據。由此可見,把數據轉化知識實質就是把各式各樣的、看似毫無關聯的、碎片式的半結構數據和非結構數據按照一定邏輯關系勾連、轉化或改造為結構數據。這個轉化過程不是簡單的排列組合,而是知識再創造,是數據價值由潛能變為現實從而實現“數據增值”的過程。
圖書館傳統服務模式只是一種形式上的“知識服務”,因為在整個服務過程,知識的傳遞路徑主要體現出“知識——知識”特征。這即是說,圖書館員的傳統業務直接面對的是知識,其工作只是使知識發生了時空轉移,其知識本身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相比之下,以大數據為基礎的知識服務的傳遞路徑則表現出“數據——知識”特征,它一方面強調從數據到知識轉變過程中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另一方面則強調了“新知識”里面蘊涵著圖書館員個人的創造性成果。換句話講,在知識服務范式中,圖書館不再僅僅是知識存儲庫,而還是數據加工廠——原材料是數據,產出是知識。相應地,圖書館員不僅是知識的存儲者和傳遞者,而且還應是知識的創造者。目前,如何把非結構數據轉化為結構數據還是IT界人士面臨的難題之一。在得不到充分技術支撐的情況下,圖書館人必須要發揮創新意識,努力培養自己知識創作能力和智慧分析能力。
3大數據對圖書館員服務能力要求
大數據時代的固有矛盾決定了圖書館不可能存儲所有數據,只能有選擇性地去保存那些“有價值”的數據。由于“價值”是一個具有相對性范疇,那么數據所含價值的“應許之地”就始終無法固定下來,舉例來說,某一數據(A)對用戶(甲)有現實價值,但不一定對用戶(乙)有現實意義,更不能排除它對后者有潛在意義。這表明,數據本身沒有好壞之分,只存在是否有與之相契合的使用者的問題。面對差異性的用戶需求,圖書館在小數據時代可采用“通采通藏”方式去滿足,然而在大數據時代則行不通。
圖書館在大數據時代必然改變傳統的思維邏輯圖式。圖書館理論強調采與訪并重,不可偏廢其一。然而,在小數據時代中,由于“采的對象”和“訪的對象”都具有相對穩定性,出于工作方便的考量,圖書館實際上把“采的對象”當作了思維邏輯運行的“阿基米德點”——這能夠很好解釋圖書館為什么總存在“重采親訪”現象。在大數據時代,圖書館需要存儲和處理的對象數據充滿了不確定性,原有邏輯圖式的基點已不再牢靠,這必然促使圖書館把思維邏輯的立足點“推回”到還相對穩固的“訪的對象”。圖書館思維邏輯圖式變化,自然會改變過去“以文獻資源組織為中心”的工作流程,轉而架構出了“以用戶需求預判為中心”的服務模式——它不僅充分彰顯了“訪”的重要性,而且也使整個業務流程進入到“知識服務”語境之中。圖書館傳統業務即使有所“訪”,采用的也是經驗的調查分析方法,采集到的用戶需求信息總是非連續性的、靜態的、定時的。在大數據時代,隨著數據不斷涌現,不僅數據的新質充滿“熵聚”特性,而且數據始源與數據受眾之間實時互動影響也具有輻射性。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中,讀者需求變化也呈現出動態化、彈性化、非邏輯性等特點。要使“訪”有針對性,圖書館員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去實時“監控”讀者的行為數據和OPAC,然后通過智能分析去把握每個讀者需求與特定數據集合之間的銜接點,還要深度挖掘去相似個體之間的相關性,進而預測分析讀者需求的變化趨勢,揣摩讀者的心理,以便為整合、發現、推送資源提供更好的服務營銷模式。另一方面,圖書館員要主動“嵌入”到讀者的學習、工作和科研過程中去,全方位跟蹤讀者的知識需求動態并提供協作式服務。無論哪一種服務路徑,都要求圖書館員放低姿態,努力掌握與讀者打交道并與之構筑和諧互動關系的技巧和策略,使“一切為了讀者”的圖書館理念真正落到實處。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強化圖書館的激勵機制,因為圖書館作為政府主導下的公益型事業,圖書館員總會在公共服務上面臨內驅力不足的老問題。
4結束語
從圖書館員到數據館員,不僅僅是名稱的變化,更是工作方式和服務模式的全新轉型。數據館員是大數據背景下的圖書館員的理想形象,因此圖書館員應該自覺以此為標桿,不斷鍛煉自己的業務素養,全面提升技術能力、創新能力和服務能力。同時,圖書館也應該積極行動起來,為數據館員培養提供支持、建議和適當的指導,努力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以應對來自大數據信息服務產業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