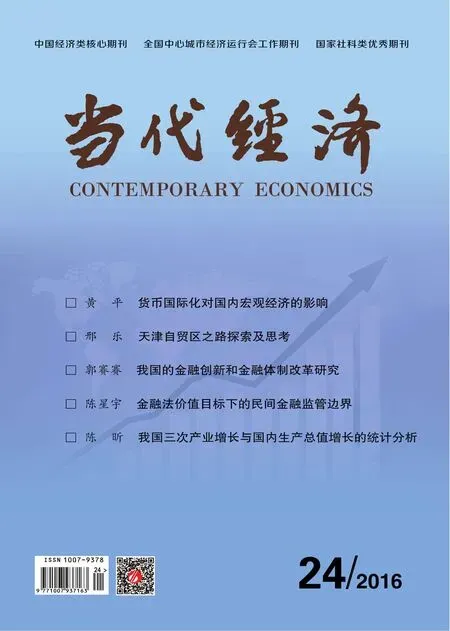財政激勵、政府主導(dǎo)與經(jīng)濟風險
宋子翌
(江西財經(jīng)大學 經(jīng)濟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財政激勵、政府主導(dǎo)與經(jīng)濟風險
宋子翌
(江西財經(jīng)大學 經(jīng)濟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我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不均衡與不可持續(xù)增長模式,主要源自于政府主導(dǎo),其中,財政制度和財政體制為其提供了激勵。由于社會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政府主導(dǎo)的經(jīng)濟風險日益凸顯。為了降低風險存在,應(yīng)當盡快推出政府主導(dǎo)地位,優(yōu)化財政改革,構(gòu)建自主退出激勵結(jié)構(gòu)。
經(jīng)濟風險;政府主導(dǎo);財政激勵
目前,我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極為不均衡,已經(jīng)嚴重影響經(jīng)濟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其中不均衡的一大重要原因便是政府引導(dǎo),特別是近年來不斷僵化的增長動力結(jié)構(gòu)、激化的群體性事件以及地方政府負債等,導(dǎo)致政府主導(dǎo)雙面效應(yīng)愈加深刻。怎樣讓政府退出主導(dǎo)地位,確保經(jīng)濟自主增長,已經(jīng)成為改革開放后的重要研究課題。以過往經(jīng)驗來看,政府主導(dǎo)地位退出絕非易事,且當前制度條件和微觀基礎(chǔ)并不齊備,所以盲目地嘗試反而會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根據(jù)大量研究表明,我國政府經(jīng)濟主導(dǎo)地位,很大程度上由于財政制度和財政體制,所以應(yīng)在政治框架中激勵政府,正確應(yīng)用主導(dǎo)地位改革的路徑選擇和改革原則。
一、不同財政體制和財政格局
自改革開放后,我國的財政制度經(jīng)歷了2個階段,并且表現(xiàn)出顯著的分權(quán)化傾向,導(dǎo)致財政體制模式截然不同,其中,以1994年為分水嶺,之前的可以稱之為分成制,之后的可以稱之為分稅制。以當前的目光審視,分成制存在較為明顯的缺陷,特別是強行依據(jù)條塊分割原則將行政隸屬企業(yè)體制整合,導(dǎo)致存在重復(fù)建設(shè)、地區(qū)分割等問題,但是就當時情況而言,也有著一定的階段合理性和必然性。分成制利用包干方式,對地方政府賦予剩余索取權(quán),盡管在分成制期間,財稅立法權(quán)并沒有形成實質(zhì)性改變,但是由于籌集機制,令地方政府的央地博弈斬獲巨大優(yōu)勢。
分稅制的形成,利用協(xié)同激勵形成了經(jīng)濟增長的體制環(huán)境,強化政府宏觀調(diào)控能力,和分成制相比而言,盡管我國經(jīng)濟經(jīng)歷了數(shù)次危機沖擊,但是依然保持年均GDP 的2個百分點增長,與此同時,分稅制的經(jīng)濟增長穩(wěn)定性也遠遠高于分成制,在分成制期間,經(jīng)濟增長差達到3.88,但是95年后至今,波動標準差僅僅達到1.68,某種程度上來說,政府宏觀調(diào)控能力得到提高。
二、財政格局與經(jīng)濟增長政府主導(dǎo)
我國的集權(quán)政治體制,盡管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政府經(jīng)濟風險的應(yīng)對能力,然而,此種體制下,也能夠?qū)Φ胤秸爡^(qū)經(jīng)濟的發(fā)展起到一定的影響,該影響的釋放方式和釋放程度取決于地方政府的激勵結(jié)構(gòu)和自主決策空間大小。雖然分稅制和分成制的激勵方式有顯著差異,可是分權(quán)策略基本相同,均為賦予地方政府的部分融資裁量權(quán)以及支出決策權(quán)。該分權(quán)策略,能夠在不同財政體制下促進地方政府治理合理性,確保轄區(qū)內(nèi)的經(jīng)濟社會健康發(fā)展,并且成為經(jīng)濟增長的“動力”。
雖然在分成制和分稅制的兩種財政格局下,央地關(guān)系特征呈現(xiàn)較大差異,然而均是在中央政府主導(dǎo)下生成,所以其便是央地財政關(guān)系的主導(dǎo)者。因改革政策的束縛,要求政府在考慮央地財政關(guān)系過程中必須重視地方利益,盡可能地滿足分權(quán)和激勵相容基本標準,因此,縱觀央地財政關(guān)系改革歷史,最為重要的策略便為增量改革,即所謂的增量控制,利用增量對存量予以調(diào)整。某種程度上來說,此改革策略下,地方財政格局變化通常涉及預(yù)算之外,比如分成制期間,地方政府確定方案后,利用預(yù)算外途徑變更,影響各自財政狀況,最終導(dǎo)致普遍亂收費和預(yù)算外資金膨脹等問題發(fā)生。中央一旦改變變革規(guī)則,那么地方便需要不斷的改變關(guān)系,以求滿足自身財政狀況,目前的增值稅擴圍便是最好的例子,但是,也有一直難以根治的弊端,就是跑關(guān)系爭專項,主要由于政府間財政關(guān)系硬化程度不夠,財政關(guān)系法制化匱乏。
雖然我國央地財政關(guān)系歷經(jīng)分成制和分稅制兩種模式,卻表現(xiàn)出極為的不平衡特點,各級政府分稅收、包收入,真正的改革都沒有為政府間事權(quán)分配構(gòu)建約束性,這種惡性不平衡改革,將會滋生惡劣后果,即缺失政府公共治理責任感,分成制過渡于分稅制,共同的特征便是財政支出和央地財政收入變化并未共同進行,且集中財力也沒有和事權(quán)上移支出責任做出合理反應(yīng)。
結(jié)合經(jīng)濟增長理論,若想確保經(jīng)濟長期增長,粗放要素投入或集約全要素生產(chǎn)率進步均有所裨益,其中,前者是我國地方政府均熱衷的增長方式,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與我國政府官員的任期制密不可分,我國官員任職年限一般集中于3年左右,為了盡快地促進所在地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打開局面,新任官員總是會做出一些巨大的政策變動,所謂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便是最好寫照。
三、政府主導(dǎo)的風險機制
某種程度上而言,地方政府大規(guī)模不規(guī)范融資,不僅會造成債務(wù)風險累積,還能夠?qū)κ袌鲋刃蛟斐蓴_亂,影響正常的融資需求,滋生大范圍資源錯配,其次,地方政府若盲目追求地區(qū)收入,還能夠?qū)е潞暧^調(diào)控風險以及嚴重社會風險。地方政府為滿足自身收入要求,經(jīng)常會打著公共利益或錯使行政權(quán)的幌子,和公正爭利,其次,部分地方政府為了削弱宏觀調(diào)控其造成的政府收入和經(jīng)濟的影響,通常會應(yīng)用自身信息優(yōu)勢,對中央宏觀調(diào)控予以無聲的抵抗,使得宏觀調(diào)控的實際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國內(nèi)現(xiàn)行財政格局與財政體制下,政府主導(dǎo)經(jīng)濟風險的傳導(dǎo)機制如圖1所示。

圖1
為了降低社會經(jīng)濟風險,政府深化財政改革可以從如下方面著手:
1、確保市場經(jīng)濟總體目標,對政府責任程度予以敲定,基于效率管理依據(jù),不斷分層次的在政府間予以分工,要求各級政府的責任收益與范圍確定范圍相同,假如受益范圍較大,那么要求其責任履行的層級必須提升,與此同時,在進行分配責任過程中,還要重視公民權(quán)利層次特點。
2、對各級政府財權(quán)和事權(quán)進行敲定,若進行政府間財權(quán)和事權(quán)安排過程中,應(yīng)該分清受托主體和委托主體,假如某級政府責任委托主體為轄區(qū)公眾,且經(jīng)由人代會敲定,則其受托主體能夠擁有財權(quán)和事權(quán)的執(zhí)行責任、如何執(zhí)行責任和如何融資權(quán)利,換句話來說,政府保障維護委托人利益為基礎(chǔ),如何更好的實現(xiàn)決策權(quán)持有,政府對不應(yīng)該做的事情中其決斷權(quán)和自由裁量權(quán)怎樣被限制,安排事權(quán)和財權(quán)的目的便在于確保財政體制的實效性和強制力,法制化財政體制,明確財力保障機制和課稅權(quán)實現(xiàn)方式。
3、財政體制改革盡管堅持責任劃分為前提,但是假如課稅權(quán)設(shè)計缺乏科學性,難以有效執(zhí)行責任,也會有違初衷,因此,約定財政體制改革責任之后,則應(yīng)當對政府間課稅權(quán)配置予以設(shè)計分析,假如委托責任均為轄區(qū)自治,那么和中央政府一樣,轄區(qū)政府也享有同樣課稅權(quán),當然,其課稅權(quán)大小要取決于委托責任大小,為了公眾的公平和效率著想,在實際實踐過程中,應(yīng)當動態(tài)性的對課稅權(quán)配置予以調(diào)整,通常會結(jié)合稅基流動的程度,對課稅權(quán)享有主體予以選擇,如果說流動程度較高,則其課稅權(quán)享的政府層級會更高,某種程度上來說,課稅權(quán)配置能夠制約政府融資措施,同時預(yù)設(shè)政府融資對公眾的責任所在,因為課稅權(quán)一旦確定,將很難再次變動,為此,假如政府課稅權(quán)不能夠達到公眾委托責任的要求,經(jīng)過人大授權(quán)后,轄區(qū)政府可以科學的選擇其余融資方式,比如債券融資等,與此同時,結(jié)合自身收入能力以及責任,實現(xiàn)政府間轉(zhuǎn)移支付機制的合理構(gòu)建。
總的來說,財政改革屬于系統(tǒng)工程,不但需要縱觀整個國際國內(nèi)形勢,更要在細節(jié)的內(nèi)容中不斷設(shè)計、調(diào)整,力求在策略中優(yōu)先選用對改革影響最小辦法,從而減低改革阻力,所以先從增量改革著手,旨在調(diào)整增量,變更存量格局,隨后漸漸瓦解存量格局中的潛在風險。目前,我國財政制度和財政體制難以利用增量改革而完整解決,然而改革會促進政府主導(dǎo)地位退出,實現(xiàn)經(jīng)濟自主增長,那么未來的存量空間也會有所變化,其存量潛在風險也會在不斷的改革中得以消化,與此同時,對政府的不合理行為和機制予以矯正,督促其重視公共利益,奠定良好的公眾輿論基礎(chǔ)和社會氛圍,兩方面相互作用,降低經(jīng)濟風險,確保經(jīng)濟健康可持續(xù)增長。
四、結(jié)束語
綜上所述,政府主導(dǎo)地位的社會經(jīng)濟弊端繁多,對經(jīng)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極為不利,為此,應(yīng)該構(gòu)建財政激勵制度,促進政府主導(dǎo)地位的退出,降低經(jīng)濟風險,實現(xiàn)社會和諧與經(jīng)濟健康發(fā)展。
[1] 梁文鳳.政府主導(dǎo)型發(fā)展模式的財政邏輯及其風險消解[J].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5,36(5):137-140.
[2] 李夏影.中國式分權(quán)與地方政府財政風險形成機理分析——基于財政激勵的視角[J].經(jīng)濟論壇,2010(4):41-44.
[3] 王雪雁.中國經(jīng)濟轉(zhuǎn)型期地方政府投資行為研究[D].吉林大學,2012.
[4] 胡鋒.轉(zhuǎn)軌時期我國財政風險成因及控制研究(下)[J].經(jīng)濟研究參考,2011(72):49-57.
[5] 劉方濤.政府財政行為對金融風險影響的分析及定位[J].改革與戰(zhàn)略,2011,27(11):66-67.
[6] 國勇.調(diào)查顯示:地方債風險成當前經(jīng)濟最大挑戰(zhàn)[J].企業(yè)改革與管理,2013(9):87-87.
(責任編輯:李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