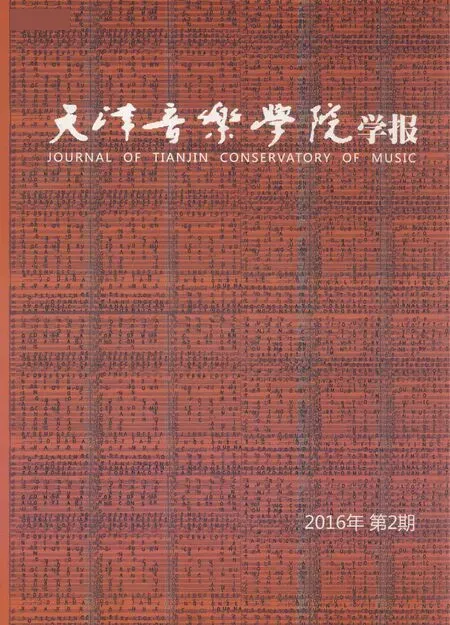后殖民時代科特迪瓦丹族中的表演、認同和堅守①
[美]丹尼爾·B.里德著,魏琳琳譯
?
后殖民時代科特迪瓦丹族中的表演、認同和堅守
①
[美]丹尼爾·B.里德著,魏琳琳譯
對于大多數科特迪瓦的丹族來說,“堅守”是一個既熟悉又重要的概念。在后殖民時代,丹族的堅守行為通過“蓋伊”的表演方式得以體現。蓋伊是一種本土的、宗教的表演,由戴面具的舞者與音樂組成。文中描述兩種爭議:其一,丹族的年輕人把蓋伊表演的復興看作是一種反伊斯蘭意識形態的表達方式,力圖通過自身的表演來復興“祖先的宗教”,他們強調葬禮的重要性,而這些都與伊斯蘭的教義相悖;其二,當地天主教唱詩班對蓋伊表演的核心“蓋坦”進行改編,丹族的年輕人認為這種改編已將蓋伊融入教堂,而唱詩班的成員則認為使用這種音樂可以表達他們的基督教信仰。本文借鑒“權力論斷”這一說法,在丹族內部用不同個體話語討論以上兩種爭議,說明了蓋伊表演是一種匯集多重權力的能動,從而形成帶有相互沖突權力的關系網。作者通過權力分析的論斷來解釋這種堅守行為,進而在多樣化的社群中揭示著相互交織、相互沖突的權力結構。在科特迪瓦不同族群、宗教多樣化和沖突四起的語境下,音樂表演作為一種協調宗教和族群認同感實現的手段,在地方認同與國家影響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②譯者注:摘要中的“蓋伊”原文為Ge,均表示蓋伊的制度和概念。
堅守 表演 宗教 認同權力
我將在本文中解釋堅守的概念,它與科特迪瓦(象牙海岸)千禧年轉折之際的丹族(Dan)的表演和宗教認同有關。我會在文中描述兩種不同的爭議,一些丹族將對霸權體系制度進行堅守的表達方式來解釋本土的表演事件。在我們的談話中,丹族的個體成員表達了另一種激烈的不同的看法,伴隨著2002年引發內戰并最終導致國家被迫分裂的國家認同政策的危機,這種表演的核心對于地方認同協調具有重要意義。
在第一種爭議中,丹族的年輕人把蓋伊(Ge③以下大寫Ge均表示蓋伊的制度和概念。,發音與“gay”類似)宗教表演的復興界定為一種反伊斯蘭意識形態的表演,它是一種本土的、宗教的表演形式,通常由戴面具的舞者與音樂組成。與他們的父母所不同的是(這些父母中的一些人信仰伊斯蘭教中的瓦哈比派,許多人是來自西非草原的穆斯林,他們向南移民到馬恩),這些丹族的年輕人企望以蓋伊(Ge)的表演形式為核心來復興他們稱之為“祖先的宗教”。在談話中,這些年輕人強調葬禮的重要性,爭論他們應該按照丹族的習俗來舉辦葬禮,其中包括被稱為“蓋坦”(Getan)表演中的音樂和舞蹈;但這些都與伊斯蘭的教義相悖,在該教義中,這些表演是被禁止的。因此,這些年輕人明確地將蓋伊(Ge)宗教表演與他們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進行堅守的表達方式聯系在一起,而這些力量又與經濟實力和社會流動性息息相關。
第二種爭議集中討論當地天主教唱詩班對蓋坦的改編所引發的相互矛盾的詮釋。作為蓋伊(Ge)宗教表演的元素,它把精神能量吸收到人世間,蓋坦在蓋伊(Ge)表演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很多丹族認為蓋伊(Ge)是對男孩子們文化教育啟蒙的精神基礎,也是丹族社會中成年人用以表現適當的教育行為方式的精神基礎。所以說,對于丹族宗教的大多數實踐者而言,以蓋坦為核心的蓋伊(Ge)便成為了丹族宗教的核心內容。對于他們來說,在教堂中蓋坦的表演意味著蓋伊(Ge)的精神本身已經融入教堂,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對殖民時代傳教士試圖廢除本土文化和宗教實踐的堅守活動。然而,對于唱詩班的成員們來說,這些用基督教歌詞所改編的音樂,已經不再吸引本土精神,反而吸引圣靈。丹族唱詩班的成員們堅信,在教堂中對這種音樂的使用可以使他們以一種與丹族人民所匹配的身份認同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基督教信仰。在這兩種爭議中,我們可以看到丹族對于身份認同的爭論,會使丹族特定的穆斯林教徒和基督教徒將他們的宗教身份從他們的族群身份中分離出來。與此同時,蓋伊(Ge)實踐者的爭論導致了丹族不僅有著族群的含義,而且還有著更深層的宗教意義。最終,這場爭論集中圍繞宗教表演展開,正如不同的動因驅使是否選用或棄用特定的音樂和舞蹈,并以此作為堅守他們生活中的強權力量的關鍵因素。
這兩種爭議中的行為可以被解釋為表述行為堅守的個案,也是面對霸權時的一種地方性力量的呈現。然而,通過丹族個體話語關于這兩個富有爭議議題的討論,我堅信這遠不只是簡單的個體抗議者與主導霸權主義結構之間的二元對立,而是集合了多重權力的能動,他們的表演形成了一種帶有相互沖突權力的關系網。④Abu-Lughod,Lila.1990.“The Romance of Resistance:Tracing Transformations of Power Through Bedouin Women.”A-merican Ethnologist 17(l):4l-55.我視之為堅守的行為發生在這張復雜的關系網之中。⑤Gilman,Lisa.n.d.“Resisting Resistance:Multiple Agencies,Gender,and Malawi Politics.”MS.在文中,我借鑒“權力論斷”這一說法,⑥Abu-Lughod,Lila.1990.“The Romance of Resistance:Tracing Transformations of Power Through Bedouin Women.”A-merican Ethnologist 17(l):4l-55.將全部權力相互作用中所發生的堅守行為考慮其中。這種方法可以作為一種實用的模式去闡述在多樣化社群中所交叉的權力關系網,特別是那些沖突不斷、卻把堅守這個詞天真地解釋為反霸權空前勝利的現象尤為適用。⑦Abu-Lughod,Lila.1990.“The Romance of Resistance:Tracing Transformations of Power Through Bedouin Women.”A-merican Ethnologist 17(l):4l-55.我的分析同時會強調國家內部的、地域性的沖突,它們對于完整的、現實的基于當地政府和體制結構之間的權力聯系尤為重要。⑧Ortner,Sherry B.1995.“Resistance and the Problem of Ethnographic Refusal.”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7(1):177.這里顯現的場景不僅是二元對立的相互作用,還包括在對話空間中的爭論話語。⑨Kaplan,Martha,and John D.Kelly.1994.“Rethinking Resistance:Dialogics of‘Disaffection’in Colonial Fiji.”American Ethnologist 21(1):123-51.
此外,我要探究這些堅守的表演方式所帶來的非主觀意識的結果。⑩Abu-Lughod,Li la.1990.“TheRomanceofResistance:TracingTransformationsofPowerThroughBedouinWomen.”A-merican Ethnologist 17(l):4l-55.通過堅守天主教霸權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我的丹族顧問已不知不覺地陷入到另一種強權政治之中,既包括作為本土社會控制的蓋伊(Ge)本身,也包括那些在國家政治認同沖突中其對立面所引發的主導話語,它們最終導致內戰和象牙海岸國家的分裂。在當代象牙海岸這個已經將宗教、區域和民族之間差異政治化(特別是對穆斯林和北方人的詆毀)的言論中,這些對宗教認同產生的地方表演的協調都具有民族含義。今天,丹族人民正陷于各種強權勢力和政治危機之中,他們的宗教選擇被賦予了越來越多的重要性和意義。正如在許多后殖民環境一樣,在這種語境下的表演和與之相關的話語正演變成為認同協調的重要舞臺。
認同、堅守和蓋伊(Ge)
對于大多數丹族來說,“堅守”是一個熟悉又重要的概念,他們的故鄉橫跨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亞的邊界。①在歷史上,丹族以農業為主,直到今天也有很多人仍在從事農業。一些人從事農業經濟,他們種植咖啡豆、可可、水稻或其他莊稼用來銷售,另一些則普遍為自給農業。然而,今天很多丹族人民,比如生活在馬恩(Man)或達納尼(Danane)的人,他們都以從事服務型經濟為主,向大城市的市場銷售商品,或者在當地的企業工作。還有一大部分丹族人民生活在科特迪瓦南部,從事種植業或者到阿比讓(Abidjan)尋求創業。近期沒有準確的丹族人口普查數據,距離最近的那次估算350,000人顯然是偏低了。在象牙海岸的這一邊,丹族是被法國人“平定”下來的幾內亞海岸族群中最后的一支。在之后的數十年間,丹族在法國人的鎮壓下生活,他們對殖民法和強迫勞動進行了強烈地反抗。在20世紀之前,丹族已經對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進行過大規模的抵抗運動,盡管今天很多丹族把基督教徒作為標識或者大多數人認為是穆斯林。在科特迪瓦,相比其他任何一個當地的族群,丹族作為反抗外部力量、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而聞名,其中最具象征意義的就是在科特迪瓦西部景觀中無處不在的丹族面具。
對于大多數丹族人而言,這些面具作為被稱為蓋伊(Ge)的多層面概念中的一部分而存在。②蓋伊[Ge,復數形式為蓋努(genu)]是一種最基本的森林精神的類別,它們作為丹族社會理想和信念的化身出現在人類社會中。③(在此文中,我會用大寫G e來表示蓋伊的制度和概念,用小寫g e表示表演中的個體神靈)。④蓋努組成了復雜的介于神與人之間神靈調節的一部分,包括已逝的祖先,還有許多其他種類的精靈。⑤在我采訪的大部分丹族認為蓋努源于荒野,出現在特定的山脈、樹林或者溪流中。在表演中,蓋努的個體可能會采用多種形式,盡管大部分特征是佩戴著面具的舞者和配以特定的音樂聲音。每一個出現在人類社會中的蓋伊(ge)都出于特殊的原因,為了滿足特定的功用。舉些例子:有的蓋努是為了慶祝和娛樂,有的伴隨著直接的動機,有的在干燥的季節祈禱防火,還有的扮演審判官來解決矛盾。但需要重申的是,蓋伊(Ge)是在入教時作為精神基礎而舉行的體驗式教育,這其中包括丹族社會中的社會理念哲學觀和正確的行為舉止。出于這個原因,大多數丹族一直把蓋伊(Ge)稱作他們的“傳統”或“祖先的信仰”而持續實踐,他們堅信蓋伊(Ge)是丹族民族認同的根基。
對于這些我所研究的丹族宗教實踐者而言,蓋伊(Ge)不是一種象征,而是涵蓋了人類所能證明的所有方面——面具、服裝、舞蹈、賜福儀式、歌曲、節奏、演唱和擊鼓的風格——這些都是從森林深處蓋努那里沿襲而來的。①盡管蓋伊(Ge)表演(或被丹族西部和南部寫做“G l e”)通常被學者們翻譯成“面具”,但我的一些受訪者認為這并不準確,也不全面。因為蓋伊(Ge)是一個多面且復雜的現象,其中包括在表演中身體表現的因素。很多(盡管不是全部)蓋伊(Ge)表演都包括一位戴著面具的舞者,他們戴著格威德侯伊Gewoedhoe(字面譯為“蓋伊(Ge)的臉”,或“面具”)表演。這其中蓋坦音樂尤為重要,它是蓋伊(Ge)表演中的精神主導。音樂可以淡化精靈與人類之間的界限,②Friedson,Steven.1996.DancingProphets:MusicalExperienceinTumbukaHealing.ChicagoandLondon: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當表演者使用蓋坦來吸引稱為“伊南”這種精靈的時候,對于人類而言有必要證明蓋伊(g e)的存在。③很多丹族認為人與神(Z l a n)之間存在著不同種類的精靈。伊南(Y i n a n)和蓋伊(g e)是這些精靈中的兩種。關于更多丹族宗教系統中的精靈,以及人類是如何與這些精靈聯系的,請參考里德[Reed]專著第72頁(2003)。
在20世紀90年代,蓋伊(Ge)表演發生在不斷增長的種族與宗教間分歧和緊張關系的后殖民時代語境下。在那個時期,科特迪瓦是一處集宗教、族群、區域間差異而綜合的場所,它不斷出現的政治化趨勢部分歸因于被誤導的政治政策,它惡化了象牙海岸“本地人”與移民、北部與南部、穆斯林與基督教徒之間歷史的緊張關系。恰恰是這些緊張形勢導致了2002年的內戰,以及國家先后被分裂成三個部分,然后又合并成兩個部分,甚至到本文2005年夏天寫作的時候,一些不穩定局勢依然存在。自1960年科特迪瓦宣布獨立后,天主教執掌政權。近些年,政治領導們制定了法律,基于極端排外的稱之為“Ivoirite”的政策(譯者注:純種科特迪瓦人Ivorianness),剝奪了大部分北方人和穆斯林的合法權益。很多人堅信這項法案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排除北方阿拉薩內·德拉馬納·瓦塔拉(Allasane Outtara)穆斯林當選總統的可能性。在1993年,自從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et-Boigny)總統去世后,一位前總理贏得北方人和南部移民的支持,瓦塔拉對此后的總統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

圖1 科特迪瓦迪歐拉(Deoule)一場慶祝紅薯的蓋努表演。作者拍攝于1997年3月。
1999年12月,在科特迪瓦歷史上發起了首次政變,結束了將近40年的政治穩定格局。隨后的幾次政變崛起,2002年9月爆發了一次內戰,反對派占領了科特迪瓦近半個北部,沿著歷史上的穆斯林北部和基督教南部分界線有效地將國家割裂。在此期間,尤其是叛亂剛開始的時候,穆斯林和北部移民不斷被騷擾,他們的房屋被燒毀,只能離家躲進清真寺,或向科特迪瓦北部逃離或者到周邊諸如馬里、布基納法索等那些原本是他們故鄉的國家。從今天的宗教關系上不難看出,當代國家危機中的對立雙方仍在持續威脅著整個象牙海岸國家的統一和持續發展。④如需了解象牙海岸政治危機中出現的民族、宗教以及區域沖突準確的數據,請參考詹姆斯·考普(J ame s Co p n a l l)2 0 0 4.
本文的民族志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在當今政治軍事危機之前,很多都發生在馬恩(Man),那是丹族地區最大的城市(人口約100,000至125,000),也是科特迪瓦西部半山區的首都(Région semi-montagneuse de l'Ouest)。在那個時期,馬恩可以被形容成一座邊界小鎮,界于森林與草原之間(一個地理上的、文化上的分界線),①科特迪瓦森林區域是講克魯語(K r u)和阿坎語(A k a n)人的故鄉,北方的草原區域則大部分講森諾夫語(Se n o u f o)或者尤拉語(Jula),北部的曼丁哥語(Mande)與官方語言馬里語(Mali[Bambara]班巴拉族或寫做[Bamanankan]),還有圭亞那東北部的語言(馬林可語[Malinké]或寫做Maninkakan)。盡管很多北方人也生活在南方,但南北方之間還是會存在實質性的文化差異。也是界于歷史上的南部基督教和北部穆斯林之間。今天,馬恩已成為一座不同類型的邊界小鎮,它恰好連接了北部與西部邊界線,分割了“新興力量”的領地。這種“新興力量”由不同的反對派和政黨組成,它們反對選舉政府。同時,這些領地仍掌握在科特迪瓦選舉政府手中。伊斯蘭教在當地已有很長的歷史,但在上個世紀開始迅猛發展,部分歸因于現在把馬恩當作家鄉的北方草原穆斯林的大量涌入。②很多北方人沿著法國殖民者借“和平政策”侵略所開辟出來的貿易之路在現在的科特迪瓦森林地區開放了定居點和貿易點(皮爾森[Person]1982),這些定居點之一就在馬恩。在20世紀,它見證了北方移民者的穩定增長,移民者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穆斯林。與類似加納海岸地區附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里的基督教已存在了五百多年,在20世紀30年代,馬恩就已經開始出現傳教活動。③Zinsou,Jean-Vincent.1976.“L'Expansion des missions Catholiques en Coted'Ivoire coloniale:Desoriginesaumilieudu XXe siècle.”Godo Goyo(2):47-78.到了2 0世紀9 0年代,馬恩從宗教意義上講已成為一座與眾不同的城市,伴隨著穆斯林、基督教和當地宗教交替并存、協同合作,當他們遷徙并進入日常生活中,他們之間也會發生沖突。在這種情況下,在世界各地沖突的諸多種形勢之中,音樂表演變成了一種認同協調的重要場域。
“我們的長輩正在‘扮演穆斯林’”
早在1997年,那一天炎熱、干燥又塵土飛揚,我的研究助理比耶米·格帕·雅克(Biemi Gba Jacques)、我的夫人妮可·科薩里歐(Nicole Kousaleos)和我走在佩蒂特·帕魯(Petit Gbapleu)的街區,這是一個被逐步擴大的馬恩所包圍的古老的丹族村莊。很多人曾經告訴過我們,佩蒂特·帕魯這個地方在蓋伊(Ge)宗教表演中格外熱鬧,雅克也有親戚在這里,因此我們對在這樣的社群進行調查的可能性充滿著好奇。在與幾個陌生人交談之后,我們找到了雅克的一些遠房親戚,雖然那些人他也多年未見。在一陣熱情的寒暄與簡短地介紹此行目的之后,一群年輕人便開始自豪地引領我們在附近游覽。行程的第一站是墓地酒吧(Tomb Bar)——這是一處圍著格帕優達(Gba Youda)村莊建立者的墓地所建造的酒館。接下來他們帶我們來到了昆(Kun),這里有一條神圣的小溪。他們向上指著一座被稱為“馬恩之牙”(Dent de Man)的山脈,這是該村莊另一處神圣的地方。在這兩處神圣景點交界的地方,我們逐漸聊起了這個社群。之后,我們走在一處泥土路段的時候停下來,他們說:“這就是邊界”。我們問:“這是什么意思?”,“這是我們村莊的邊界。尤拉(J u l a)人(在科特迪瓦,一種對北方草原遷徙移民的統稱④“尤拉”這個詞的界定比較復雜。“尤拉”在北方曼丁哥語中是“商人”的意思,像尤拉、班巴拉(Bamb a r a)以及馬林克(Malinké)。通常來講,所有來自北方草原和荒漠草原的移民,大部分都是商人,都被其他人稱為“尤拉”,他們定居在科特迪瓦的中部和南部。這些人中的小部分來自科特迪瓦北方中部的尤拉族或來自南方的布基納法索,但大部分來自其它民族。然而,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們的服裝(布布[bubus]一種類似伊斯蘭教的長袍),所以他們通常自然地與伊斯蘭教和北部地區聯系在一起,被稱為“尤拉”。更為復雜的是,一些來自森林地區的人們即使轉變為信仰伊斯蘭教,他們有時界定自己或被他人認定為“尤拉”。在馬恩的丹穆斯林當中這也是事實。關于科特迪瓦“尤拉”更為詳盡的研究請參考洛奈1982和1992。簡單地總結一句,一談到成百上千不同類型的北方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國籍和民族,并且生活在科特迪瓦南部,北方人=尤拉=穆斯林。)可以在邊界的另一邊生活、擁有自己的房屋,但是不能在我們這邊。”說完他們繼續帶我們在附近觀光,在幾處關鍵的地方,他們都刻意強調那條隱形的邊界對他們所處社區的特殊含義。“尤拉在對面,”他們說,“丹在這邊。”(這使我想起科特迪瓦現有的劃分地圖)我們很想知道這句話的深層含義,為什么在我們圍繞村莊的整個旅途中,這條邊界線被一再強調?最終我們了解到,這條邊界線不論從字面上還是引申的含義講都代表著一種抵抗的方式,它就是我們所研究的核心——蓋伊(Ge)表演。
丹族與北方移民之間長久以來的矛盾關系存在多種原因,主要原因是經濟競爭。①Ford,Martin J.1990.“Ethnic Rela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adership among the Dan of Nimba,Liberia(ca.1900 -1940).”Ph.D.dissert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事實上,正如羅伯特·洛奈(Robert Launay)所說,在科特迪瓦伊斯蘭教與主導經濟力量聯系在一起。基于他們與貿易商(指尤拉)長久以來的傳統,許多北部移民已經成為非常成功的企業家、商人和經營者。洛奈認為,一個人如果轉信伊斯蘭教,實際上他可以更容易獲取暴利的商業機遇。②Launay,Roberts.1992.Beyond the Stream:Islam and Society in a West African Tow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一些我調查的貧苦丹族人民對北部馬恩人存在嫉妒與偏見,他們認為是那些人搶走了丹族人民的工作和其他經濟機遇。
盡管歷經幾代人,許多丹族人民已經將北方商人帶來的伊斯蘭教傳統與丹族人宗教的思維方式與實踐融合在一起。然而近年來,這種融合的宗教實踐遭遇到兩種實踐者的堅守,即來自于瓦哈比派伊斯蘭教主張的“純粹”伊斯蘭教風格,主張應該脫離帶有地方宗教色彩的實踐者;另一個則來自于當地的年輕人,他們拒絕伊斯蘭教并聲稱他們所崇拜的是來自“我們祖先的宗教”,它以蓋伊(Ge)宗教表演為核心。這些年輕人批評他們的長輩,認為長輩們不該屈服于那些北方移民,不該沿襲他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不該遵從他們的宗教。這些人還譴責長輩們受北方移民的影響而拋棄了蓋伊(Ge),蓋伊(Ge)才應該是丹族人民認同的核心所在。
這種表演與信仰混合的復興運動被當地人界定為“傳統的”,它的框架是作為一種對伊斯蘭教的拒絕。在西非森林區域中,作為一項對應的研究提供了伊斯蘭教的發展和本土宗教與音樂活動減弱的記載。例如,在20世紀70、80年代,萊斯特·蒙特(Lester Monts)就曾仔細研究過伊斯蘭教的發展和瓦伊(Vai)面具表演與秘密社團數量逐漸減少的關系。蒙特指出,秘密社團參與者的減少直接導致與社團相關的音樂體裁表演幾乎瀕臨消失。③Monts,Lester P.1980.“Music in Vai Society:An Ethnomusicological Study of a Liberian Ethnic Group.”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Monts,Lester P.1984.“Conflict,Accommodation,and Transformation:The Effect of Islam on Music of the Vai Secret Societies.”Cahiers d'Etudes Africaines 24(3):321-42;Monts,Lester P.1998.“Islam in Liberia.”In The Garland Encyclopedia of World Music.Volume 1:Africa,edited by Ruth M.Stone,327-49.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Inc.與其相反的是,這些佩蒂特·帕魯(Petit Gbapleu)年輕人堅守伊斯蘭教,復興他們的蓋伊(Ge)“傳統”,包括與蓋伊(Ge)相關的表演形式。我的研究支持彼得·馬克(Peter Mark)提出的假說,即從伊斯蘭教脫離的運動可能比西非的民族志文獻所描述的更為普遍。④Mark,Peter.1992.The Wild Bull and the Sacred Forest:Form,Meaning,and Change in Sen egambian Initiation Mask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51.顯然,宗教的選擇對于很多西非人來說是一種基本的認同因素,并且在當代西非這個宗教多元化的環境中,這些選擇可能導致沿襲宗教、世代、區域以及族群的路線而引發激烈的沖突。
1997年,佩蒂特·帕魯成為那些身份沖突尤其突出的一個社群。丹族信奉的宗教實踐依然是附近丹族居民生活經歷的一部分。男孩女孩們要在很小的年紀實行割禮和入教儀式。個體崇拜那里的圣山和圣泉,還有很多佩蒂特·帕魯居民崇拜蓋努。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20世紀90年代,佩蒂特·帕魯作為蓋伊(Ge)宗教表演的核心,在馬恩一直享有盛名;盡管事實上那些聞名于世的蓋努已經銷聲匿跡多年了。
此外,佩蒂特·帕魯的大多數居民都是穆斯林。村里的首領和所有掌權的男性,還有年長的、地位很高的婦女,事實上,幾乎所有四十歲左右及以上的人都是穆斯林。佩蒂特·帕魯位于馬恩穆斯林掌權的特有的伊斯蘭區域。與佩蒂特·帕魯接壤的是密集而龐大的尤拉布古(Julabugu),它是當地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在20世紀90年代是多數馬恩北方移民的故鄉。尤拉布古布滿各種清真寺,從很小的、單間的,到家庭式的,無數街邊店面式的清真寺,再到雄偉的“白色大清真寺”,它一直主宰著這座城市地平線的景致。每天五次,這些清真寺的喚禮聲響徹佩蒂特·帕魯,一些聲音來自尤拉布古,其它的則來自佩蒂特·帕魯。年長的甘納森·馬馬杜·謝里夫(Gnassene Mamadou Cherif),曾經是一名醫者/占卜師,也是一位隱士,1997年他曾計劃開展一項穆斯林運動,吸引該地區信奉丹宗教的人們轉信更“純潔”的伊斯蘭教——瓦哈比派。他始終努力,并把它當作一生的使命,說服那些信奉祖先宗教的人和那些總把伊斯蘭教與丹族宗教混淆的人們,讓他們成為“真正的”、“純粹的”瓦哈比派穆斯林信徒(p.c.)。①本文中所有引用的訪談材料皆為錄音制品,原版本存于印第安納大學傳統音樂檔案館。
甘納森最想說服的鄰居之一是格帕·格瑪(Gba Gama)。格帕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年輕人,他拒絕像家人和其他佩蒂特·帕魯的長者那樣把自己塑造成為穆斯林,而依然信奉蓋努。作為對“更純粹”風格且廣受歡迎的伊斯蘭教的回應,格帕和其他人拒絕任何形式的伊斯蘭教義。格帕·格瑪把自己看作是佩蒂特·帕魯地區非正式的、反穆斯林運動的領導。格帕與佩蒂特·帕魯的建立者格帕·尤達(Gba Youda)有著直系的血緣關系。因此,格帕·格瑪把格帕·尤達的墓地作為公共的圣地并在周圍建造經營著墓地酒吧。盡管格帕·格瑪家族中的許多人,包括他曾經作為首領的、已逝的父親都是穆斯林,但他們也都曾經與蓋伊(Ge)活動有著密切的聯系。隨著格帕·格瑪的父親及同輩人在20世紀80年代初相繼去世,蓋伊(Ge)和丹族宗教曾經經歷了一段空白時期。從那時起,很多本應該接管丹族宗教領導權的長者在甘納森的領導下,開始轉向瓦哈比亞,并漸漸拋棄了蓋伊(Ge)實踐者們所聲稱的“傳統教義”。
很多像格帕·格瑪這樣的年輕人都拒絕伊斯蘭教,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認為起源于祖父輩和父輩的沖突緣于他們把伊斯蘭教和丹族宗教混為一談的結果。實際上,1997年一位扎西(zudhe)的女性宗教領導者的葬禮激化了佩蒂特·帕魯的激烈沖突。扎西是女性蓋伊(Ge)貢派(Kong)分支的年長領袖,貢派從事著女子入教、割禮、生產和精神溝通。扎西是丹族社會中最有權力的女人,也是掌管丹宗教事宜的領導者。其實扎西就像其他佩蒂特·帕魯貢派的成員一樣,也是一名穆斯林。她對宗教融合的嘗試并沒有引起太多爭議,直到她去世的那天。之后,關于她的安葬和葬禮到底應該按照伊斯蘭教還是丹族的傳統引發了一場沖突。按照伊斯蘭教瓦哈比派的傳統規定,葬禮應該相對簡單,包括誦讀古蘭經,但沒有任何歌曲或舞蹈,之后幾乎立即對尸體進行安葬。與此相反,丹族的喪葬傳統要持續很多天,以圍著逝者身體歌唱和舞蹈表演為主,還要對其守靈。讓很多村民傷心的是,在丹族宗教追隨者們反對之前村里有權力的穆斯林長者們將扎西的遺體按照伊斯蘭教的方式安葬了。很多扎西的年輕女追隨者們對此感到悲痛欲絕。例如,利恩·薩提·伊芙(Lien Sati Yvonne)告訴我,扎西作為丹族的宗教領袖,應該按照丹族的方式舉行葬禮。人們從各個地方趕來,熬了一整夜就是為了看她的遺體,但卻未能如愿。伊芙還說,那些由扎西實行割禮的女孩子們都應該有機會走到她遺體前為她祈禱。“那個時候甚至連舞蹈都沒有,都被穆斯林替代了!”(p.c.)。
后來我才知道在佩蒂特·帕魯所有的年輕女性都是扎西和貢派虔誠的信徒,并且沒有人認為自己是穆斯林。一天,我把她們召集起來做采訪時,她們告訴我,“這里沒有人做禮拜。我們是追隨祖(Zu)的女人。”為了得到澄清,我提到扎西已經是一名穆斯林了(所以她的繼承者也應該是)。她們激動地回答,她們認為扎西成為穆斯林是個壞主意。她們那么敬重扎西,認為簡單地寄托于貢派更好,不要試圖通過其他媒介接近神靈。那樣,當人去世的時候也不會出現任何問題。她們說,宗教上的模棱兩可不好。迪耶莫可·克里斯汀(Tiemoko Christine)總結她的想法后簡單地說,“貢派是一種宗教,在清真寺做禮拜是一種宗教。遵從單一的一種宗教比較好。”我問她們是否會堅守她們母親甚至是祖母那一代的宗教而選擇祖先的宗教。她們回答說,比起那些長輩,正是佩蒂特·帕魯這些年輕女性在“守護祖先的習俗”。
考慮到葬禮在非洲語境中的重要性,圍繞一場葬禮引發的宗教沖突在佩蒂特·帕魯這里發生也就不足為奇了。扎西這件事并不是唯一的。一天,年輕的鼓手高郵·提耶·讓-克勞德(Goueu Tia Jean-Claude)給我講述了幾個其他的例子,包括他的好朋友格帕·馬修(Gba Matthieu)父親的葬禮,就像扎西一樣,既是穆斯林,也崇拜蓋努:
馬修的父親——他熱愛蓋努!無論何時只要周圍有宗教活動,他都會邀請蓋德羅(Gedro)[跳舞的蓋伊(ge)]!但是,當他去世的時候…因為他是長輩,愛我們所有人,我們想請蓋伊(ge)去參加他的葬禮。但年長的甘納森拒絕了!他說,“這是穆斯林的事情!不是蓋伊(Ge)的事情,是穆斯林的事情!如果你們要帶著蓋伊(ge)來,就等葬禮結束。”所以,葬禮上沒有蓋努的表演,就好像那根本不是他的葬禮。(p.c.)
在這樣宗教沖突的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末,佩蒂特·帕魯的年輕人們開始復興蓋伊(Ge)表演。格帕·格瑪在20世紀80年代召集年輕人追隨“傳統”。格帕成為核心人物,并自稱是社群里留下的蓋努“組織者”。他開始在每周六邀請年輕人去他的酒吧練習敲鼓,為他們付酒水錢,鼓勵他們。格帕告訴我:
我們這些剩下來的年輕人,開始教我們的兄弟們敲鼓,并且從事蓋伊(Ge)的活動以免全都忘光了…現在,年輕人們盡力保證傳統的觀點還在延續…我是組織者…我們有人負責敲鼓,其他人跳舞,有的歌唱。所以說這是(一種)分享的(努力)…我希望從現在直到我去世,這些習俗仍然能持續下去。所以…我不會信奉其他宗教,例如穆斯林宗教,他們說:“如果你加入穆斯林,你就再也不能插手蓋伊(Ge)的事情了。”(p.c.)
1987年,當格帕·格瑪投身于復興丹族宗教實踐的時候,一位隱匿多年的蓋伊(ge)表演者重新出現了。佩蒂特·帕魯的居民賽木倫·艾米(Semlen Aime)已逝的祖母出現在他的夢中。這位祖先的靈魂指引艾米,他們家中應該有人讓蓋伊(ge)重新復活,那將變得非常流行。所以佩蒂特·帕魯這位年輕人重新復興了蓋德羅(Gedro),一種舞蹈或娛樂的蓋伊(ge),并且將那個預言變成現實:從1987年到20世紀90年代末,蓋德羅成為馬恩地區最流行的蓋努表演之一。人們不需要信仰蓋努也可以參加蓋德羅表演。甚至甘納森·馬馬杜·謝里夫也出席了蓋德羅的演出。他甚至向蓋伊(ge)贈送禮物(這種實踐通常將“供奉品”或“祭品”聯系起來),但是他解釋說,“這不是崇拜”,“[崇拜]是一種罪惡”(p.c.)。對于甘納森來說,這種方式的贈與行為與其他任何西非音樂中非宗教演出的贈與沒有區別,在那里觀眾們認為演出到高潮的時候贈與表演者禮金都是理所當然的。很多人都把蓋伊(ge)的舞蹈表演看作是一種純粹的、非宗教的娛樂活動。一些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感覺他們可以參加蓋德羅演出而不需要向他們的宗教價值觀妥協。但是對于那些年輕的表演者而言,這是一種明確的宗教復興,也同樣是一種明確地堅守瓦哈比派的實踐方式。
一位在蓋德羅演出的專業鼓手高郵·提耶·讓-克勞德(Goueu Tia Jean-Claude)非常明確地表達了這種情感。關于瓦哈比派,高郵嘲笑地宣稱:
正是我們的父輩來到了這座城市,扮演著穆斯林。這是我們的父輩所不理解的。是他們變成了,你管那個詞叫什么?瓦哈比派——扮演穆斯林…佩蒂特·帕魯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例子。非常危險。我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在佩蒂特·帕魯我們的父輩追隨了那些生活在這里的外人,并且他們現在想要拋棄他們自己的習俗。(p.c.)
高郵強烈的措辭——指責他的長輩僅僅是在扮演穆斯林——強調了1997年在佩蒂特·帕魯世代間宗教分裂的緊張形勢。佐伊·斯特羅瑟(Zoe Strother)寫到:彭德(Pende)面具表演(譯者注:剛果的一種民族面具)“建構鞏固了族群關系”。①Strother,Zoe S.1998.Inventing Masks:Agency and History in the Art of the Central Pende.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6.顯然,佩蒂特·帕魯的居民在他們的宗教實踐中,既建立了族群關系,也有沖突;那些實踐包括蓋伊(Ge)演出,一些人認為這是一種堅守瓦哈比派的形式。認同總是通過與他人的關系而形成;認同是被協商的。②Bauman,Richard.1971.“Differential Identity and the Social Base of Folklore.”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84:31-41.高郵以直接的反對態度表達了他的價值觀和認同感——在堅守中——堅守他者族群中其他人的行為,蓋伊(Ge)是這場辯論的焦點。
在多重宗教定位的語境下,人們傾向于虔誠地將自己與他者加以區別,很少依賴教義,而更多基于行動。從這點來說,我的研究支持羅伯特·洛奈對科特迪瓦北部的研究。洛奈稱:“反對者們的觀念簡直是無知甚至有點愚蠢;另一方面,他們的行為如果不能直接用‘邪惡’這個詞來形容,那也是令人厭惡的。”③Launay,Roberts.1992.Beyond the Stream:Islam and Society in a West African Tow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05.同樣,我的采訪者正是以這種行為方式,例如在葬禮中是否需要音樂和舞蹈表演,而不是以他者的觀念,當作區分丹族宗教與其他宗教認同的因素。這些因素使得蓋伊(Ge)的公眾表演——宗教抵抗的實施——在20世紀90年代馬恩這種多重社會環境的認同協調中,變得如此重要。
“教堂中的蓋伊(Ge)”
在我開始討論第二種觀點時,先介紹兩個人:比耶米·格帕·雅克(Biemi Gba Jacques)和古尤·格比·阿方斯(Gueu Gbe Alphonse)。比耶米·格帕·雅克,1997年時他23歲,他基本是在阿比讓的大城市長大的,盡管他也曾在馬恩附近的村莊生活了很多年,在那里進行過蓋伊(Ge)的入教儀式。和許多西非年輕人一樣,比耶米認為自己既是國際化的,同時又與傳統深深地聯系在一起。比耶米首先界定自己是個天主教徒,盡管他內心里很虔誠地相信蓋伊(Ge),也承認蓋伊(Ge)對于丹族族群認同的重要性;作為我此次的研究助手,比耶米提出辯論,使他能夠加深與蓋伊(Ge)的關系,以及他的身份是作為一名丹族人。古尤·格比·阿方斯先生是位年長者,已經從國家旅游局退休。與比耶米一樣,古尤·格比對蓋伊(Ge)在丹族宗教和族群認同中的重要性持強烈意見。鑒于他在文化方面的博學才智在當地享有盛名,古尤·格比是我此次研究的重點采訪對象之一。
一天,比耶米和我與古尤·格比坐在一起,討論不同宗教間的競爭形成了20世紀90年代馬恩的特色。古尤·格比的年紀足以回顧那個地方基督教的初期情況,他回憶說早期的傳教士要求改信基督教的人要宣布斷絕任何與丹族宗教和文化相關的東西。古尤·格比繼續講,隨著時間的延續,教堂組織者們意識到有必要允許一些地方文化——例如語言、服飾、舞蹈、音樂——在教堂的服務中存在。這種趨勢在非洲很普遍,也像這塊大陸的許多地方一樣,非洲人通過創辦他們自己獨立的教堂匯集各種音樂,甚至在很多情況下將特定的教義將當地的文化融合到他們的周日活動中,從而使基督教“非洲化”。①Omoyajowo,J.Akinyele.1982.Cherubim and Seraphim:The History of an 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New York:Nok Publishers International;Peel,J.D.Y.1968.Aladura:A Religious Movement among the Yorub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這里有許多歐洲人和美國人開辦的教堂,在他們的圣會中參與人數日漸減少,逐漸開始允許地方文化元素融入到他們教堂的服務之中,以便贏得更多的追隨者。
在馬恩,這種趨勢導致了天主教堂里本土唱詩班的形成。在馬恩附近,丹族和“威”[(Wè)丹族南部的少數民族鄰邦]的唱詩班演唱著本地的音樂,使用本地的樂器,配以基督教為導向的歌詞。古尤·格比解釋說,天主教這樣做是很明智的選擇,因為這讓丹族人民在保留他們自己的文化認同感的同時變成了基督教徒。他論證說,“如果我們在教堂中沒有使用鼓,人們就會離開教堂,回到他們的村莊,回到他們的面具那里”(p.c.)。我發現這些都很有意思,如果不是尋常的話。但是當古尤·格比繼續講的時候,我的耳朵豎起來了:“他們把我們的面具歌曲送到教堂,他們管那些歌曲叫做‘唱詩班’…他們把‘耶穌’、‘圣父’、[或者]‘救世主’加進去,但是副歌、旋律、鼓——完全都是一回事!”他斷言這些都顯示了蓋伊(Ge)的權力。基督教如果沒有從蓋伊(Ge)轉移權力的話,在丹族國家它將無法生存下去。事實上,無論節奏、歌唱與擊鼓的方式,在某種情況下甚至特定歌曲本身,它們都以蓋努的方式傳授,并且被認為是一種蓋伊(Ge)的表現形式,即意味著教堂中的蓋伊(Ge)。
下面介紹第三個人:丹族唱詩班的領唱和贊美詩作者盧瓦·菲利普(Loua Philippe)。盧瓦是一個中年鄉下人,他年輕的時候一直在研究丹族宗教,1997年把自己稱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并且表達出對丹族不再有任何興趣。贊美詩作者盧瓦對于在教堂中使用蓋坦有著不同的詮釋。盧瓦向我解釋了他的創新過程。他選取了傳統的丹族歌曲,將歌詞參考他的基督教信仰進行改編,之后把這些教給他的唱詩班,伴隨著丹族鼓一起合唱。盧瓦告訴我,尤其有效的是那些與宗教有關的歌曲——蓋坦或者蓋伊(Ge)歌曲——那些原本為蓋伊(Ge)表演者而做的歌曲,在聲效方面代表著蓋伊(Ge)。下面是一首我在一次洗禮中所聽到他的唱詩班演唱的歌曲文本,后面我聽到了這首歌的原來的版本:
原來的版本:
Gewon ye dhoe 蓋伊(Ge)這件事是存在的
mengban waa wondo Gewon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ye dhoe 蓋伊(Ge)這件事是存在的
天主教唱詩班版本:
Zlan ye dhoe 上帝是存在的
mengban waa wondo Zlan ye dhoe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上帝是存在的
在這個典型的例子中,盧瓦只是簡單地把“Gewon”換成了“Zlan”或“上帝”,字面上翻譯成了“蓋伊(Ge)這件事情”,但是指的是蓋伊(Ge)整個的系統、概念和制度。按照盧瓦·菲利普所說,他對蓋坦原始版本素材的使用并不意味著他把蓋伊(Ge)請進了教堂。他說,改變歌詞就改變了意義。②盧瓦的斷言說明了他改變了這首歌曲的含義,這使我想起近些年民族音樂學文獻中提出的理論,即音樂到底能帶著那些超出音樂之外的元素探索到何種程度。彼得·曼努爾(Peter Manuel)曾經在《卡帶文化》中用了完整的一章來描述印度旋律的循環(曼努爾[Manuel]1993:131-52)。杰弗瑞·薩米特(Jeffrey Summit),在《陌生土地上的神曲》[The Lord's Song in a Strange Land]中討論了在教堂唱詩班中是否應該引用非基督教旋律(薩米特[Summit]2000)。馬丁·道奇(Martin Daughtry)(2003:59),在他關于身份認同的研究中提到在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立法過程中把俄羅斯國歌換成蘇維埃時期的國歌,鮑里斯·阿薩耶夫(Boris Asaf'ev)認為盡管一種旋律中使用了新的“腔調”從而引起意義上的稍微改變,但原意通常是不變的。很明顯,任何重新使用、重新編詞和音樂的挪用都會引起意識形態上的辯論,它們通常說明了音樂在認同協調中的中心性。那些歌曲再也不會吸引伊南(yinan)精靈。相反,在教堂里,當他的唱詩班成員歌唱時,他們好像被圣靈帶動得異常活躍(p.c.)。對于盧瓦來說,歌唱與擊鼓的方式,還有旋律,都不再是蓋伊(Ge)表演的一部分。對于他而言,它們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對于蓋伊(Ge)的實踐者來說,蓋伊(Ge)表演加深鞏固了民族與宗教的認同感;盧瓦在這些復雜的認同感中將宗教從民族認知中脫離出來。
比耶米·格帕·雅克是盧瓦·菲利普觀點的反對者。對于比耶米而言,蓋伊(Ge)是一種精神,這種精神的所有層面都顯示在地球上,一種教育,一種個人的行為方式——以及當蓋坦在教堂里表演的時候,蓋伊(Ge)就在教堂里。蓋伊(Ge)是一種比依附于其他宗教更深的事物;它是一些人所謂“傳統”的理論和行動,是一種不能分裂的基于宗教和民族認同的概念準則。和其他任何人一樣,比耶米強調,一些丹族人感受他們的音樂、他們的文化和他們的身份認同及其一切來源之間的聯系,蓋伊(Ge),這里比耶米稱其為“面具”。①盡管我訪談的很多人都認為,在文章中使用“蓋伊”(Ge)比用“面具”更好,當使用法語來采訪這些人的時候,他們用“面具(Masque)”來代表“蓋伊”(Ge)。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比耶米敘述的這段話中出現的“面具”這個詞,雖然它并不能準確地翻譯出“蓋伊”(Ge)的多層含義。談到蓋伊(Ge)音樂的使用,或者蓋坦在教堂中的運用,比耶米說:
如果說節奏是從面具表演[蓋伊](Ge)中學來的,在這樣的語境下,假設歌曲也是這樣學來的——因為是相同的副歌——如果是這些歌曲,如果鼓的運用是為了表達面具表演的成功,為了表達面具表演的榮耀,為了在歌曲里贊頌面具表演,如果這一切都可以在教堂里找到,我認為面具[蓋伊](Ge)就是在教堂里…如果說服裝,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為了配合面具表演而穿的演出服,也都可以在教堂里找到,我要說面具表演就是在教堂里。這是那些人不想要的!也是他們不知道的…我們[指雅克和作者]可以去教堂看一看,聽一聽…你就會發現那就是一回事!區別就是這邊唱的是“面具”,那里唱的是“上帝”…那將成為面具在教堂里明顯的證據!…所有這些因素都出自“面具”學校。即使面具沒有在教堂中舞蹈。但是他們[蓋努]是被教授的,我們都在教堂里找到了。而且那就是面具表演!他們[基督教徒]認為面具表演不過是一個人臉上戴了一張面具而已。但是,不!那是他們永遠不能理解的!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的!他們不知道面具——其實是一種教育。面具是一種行為舉止,面具是服飾。面具是一種說話的、歌唱的方式。簡言之,面具就是生活,就是他們[長輩們和蓋努]教會別人的生活方式,他們教導著別人。這是傳教士們起初所不了解的…面具所具有的形而上學的表現已經進入到人們的精神世界,融入到人們的思維方式之中,融入到人們的行為方式之中!簡而言之,即融入人們所有的社會文化行為之中。(p.c.)
很明顯,蓋坦的旋律、節奏和樂器——都是蓋伊(Ge)的表現——那些在教堂崇拜活動中所使用的,對于比耶米來說都象征著蓋伊(Ge)的勝利,丹族文化的勝利,它們戰勝了法國殖民者試圖廢除本土文化的實踐和信仰。盡管他本人沒有用這個詞,比耶米的評價代表了一個富有堅守行為的典型個案,代表了當地媒介所面對強權時所表達的情緒。
結論:權力的論斷
哪里有權力,哪里就有堅守(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性經驗史》作者)哪里有堅守,哪里就有權力(萊拉·阿布-盧格霍德[Lila Abu-Lughod])
引用一種權力分析的論斷到本文富有爭議的兩種觀點,使得其中所表現的堅守表達方式更加復雜化了。這種路徑不僅使那些公然反抗專權的反對機構突顯出來,而且使這些反對者在與專權勢力抗衡時得到可以使用的手段,盡管在不經意間又陷入了其他專權的陷阱之中。如此,一場關于權力的論斷使那些躲在堅守運動后的權力關系突顯出來,類似20世紀90年代科特迪瓦這樣一種復雜、多樣化的環境。
首先我以權力分析的論斷討論第二種爭議。雖然對于比耶米來說,也延伸到丹族,蓋伊(Ge)很明顯地堅守傳教士試圖消滅本土文化實踐的嘗試,但其它的權力勢力在做什么呢?在堅守教堂專權的過程中,比耶米和其他追隨蓋伊(Ge)的實踐者又會不自覺地陷入到其它什么樣的專權了呢?在文章的前言中,我強調了蓋伊(Ge)在身份建構形成方面的重要。但是蓋伊(Ge)表演不僅僅是堅守殖民主義以及后殖民主義強權而獲得身份協調與自我界定的唯一手段。它遠不止于此。蓋伊(Ge)還有一個歷史性的角色即作為一種地方社會控制的手段。例如,蓋伊(Ge)在表演中界定并加強了丹族的父權制,它為男性的控制權、對女性的支配權,以及比如女性的割禮等習俗,都提供了深入的精神論據。①雖然對女性實行割禮可以說是丹族社會中對父權制的強調,但實際上還有更復雜的含義在其中。因為在非洲很多地方,丹族社會中的年長婦女是那些維護女性割禮最熾熱的守護者。很多丹族認為女性(和男性)的割禮是丹族身份認同中一種關鍵的身體標記方式。蓋伊(Ge)同樣也為地方政權提供了宗教基礎。在許多丹族社群里,首領僅依靠幕后最有權力的蓋伊(Ge)的支持對此進行管理,即這個既崇敬又帶些懼怕情緒的家庭職權在地方事務上起到很大的控制作用。一些丹族人拒絕蓋伊(Ge)這樣做,因為他們感覺受到限制并且被“傳統”的陷阱所困。那些反對者有可能會被蓋伊(Ge)的實踐者糾纏和攻擊;事實上像盧瓦·菲利普這樣杰出的基督教唱詩班領導時常會遭到這種攻擊。那么對于盧瓦來說,如果在教堂里演唱蓋坦是一種堅守行為的話,那并不是對基督教和殖民主義、后殖民主義權力聯合的堅守;相反,盧瓦唱出了他對蓋伊(Ge)偏狹的社會秩序的反抗。但是,像羅恩·伊莫夫(Ron Emoff)那樣,我也要強調,對盧瓦而言,歌唱他的作品根本上并不是對任何制度的反抗;盧瓦告訴我說,他在教堂里演唱純粹是為了“崇拜上帝”。同樣地,伊莫夫為韋伊特·爾曼(Veit Erlmann)的《夜之歌》[Night song](1996)注解時提到,雷村黑斧合唱團(Ladysmith Black Mambazo)里的約瑟夫·沙巴拉拉(Joseph Shabalala)談到“一種上升到所有人之上的權力”。②Emoff,Ron.2002.Recollecting from the Past:Musical Practice and Spirit Possession on the East Coast of Madagascar. Middletown,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51.將這種對信仰的表達僅僅詮釋作為與人類權力斗爭相關的堅守行為實在是簡化了,它會對那些借助超越人類的權力對自我解釋的人造成傷害。③參見Gilman,Lisa.n.d.“Resisting Resistance:Multiple Agencies,Gender,and Malawi Politics.”MS.吉爾曼為那些學者們的堅守傾向提出了批判性的修正方案。如她所注,我們必須要將那些人從抵抗中剝離出來。那樣,面對霸權主義會有多種可能的反應——不只是反抗——還說明了能動性。吉爾曼指出,如果一個人已經意識到了權力的不均衡性,但仍然選擇置身事外,那么他與那些參與堅守的人沒什么區別(吉爾曼n.d.)。
如果我有可能感覺到我是在強迫唱詩班領導盧瓦接受一種對堅守詮釋的話,至于比耶米·格帕·雅克,堅守很明顯的是他對蓋坦在教堂表演的詮釋。然而,為了繼續說明權力分析的論斷,當雅克為蓋坦能在教堂中表演這件事慶祝的時候,他從言語中對這種堅守的表達幾乎不會對教堂的權威造成挑戰或者顛覆;④參見Gilman,Lisa.n.d.“Resisting Resistance:Multiple Agencies,Gender,and Malawi Politics.”MS;Abu-Lughod,Lila.1990.“The Romance of Resistance:Tracing Transformations of Power Through Bedouin Women.”American Ethnologist 17(l):4l;Kaplan,Martha,and John D.Kelly.1994.“Rethinking Resistance:Dialogics of'Disaffection'in Colonial Fiji.”American Ethnologist 21(1):126;Scott,James C.1986.“Introduction.”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3(2):6.教堂通過對蓋坦進行音樂的/文化的挪用,強大地吸引并且獲得了很多丹族的追隨者。如果在教堂里演唱蓋坦可以被解釋為是一種個人權力,或地方權力,或面對霸權能動性的例證,那它不過是教堂為了贏得更多追隨者而做的選擇。因為這是一種堅守行為,至少從一些丹族人的視角來看,這里沒有人“勝出”。同時,教堂的權力因為參與者們——有趣的是,也包括比耶米·格帕·雅克——轉信天主教而變得更加強大,盡管他們全部都在演唱丹族的音樂。
這種族群、宗教認同感的分離對于丹族人來說是相對嶄新的,并且對盧瓦·菲利普這樣的基督教徒來說也是特別顯著的,他們希望通過以帶有他們族群認同感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基督教的信仰。與此同時,對于比耶米·格帕·雅克和古尤·格比·阿方斯這些蓋伊(Ge)的實踐者來說,丹族人的認同感保持著固有的族群的和宗教的定位,它作為對外部力量驕傲的堅守者從而形成對丹族國家聲譽的比喻。比耶米在這個問題上的定位既有趣又復雜,因為他既是一位蓋伊(Ge)的實踐者又是一名天主教徒。像盧瓦一樣,比耶米宣稱自己既有強烈的丹族認同感,同時又有作為一名天主教徒的身份認同感。同時,在他生命的這個轉折點,當他將特定的精力投入到蓋伊(Ge)并加深作為一種丹族人的自我感知時,比耶米也選擇對這種抵抗的強烈表達歸結到歷史性的嘗試之中,并以此作為認同表達的一部分來壓制蓋伊(Ge)。在世紀更迭的語境下,這些不同的觀點對于丹族而言,意味著多元化、沖突四起的科特迪瓦通過音樂的選擇和表演的話語從而進行協調。
像唱詩班的領導盧瓦一樣,在佩蒂特·帕魯的丹族瓦哈比派同樣表達了將宗教從民族中分離的多重認同感,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們對丹族宗教實踐的反對,包括蓋伊(Ge)表演。而那些帶頭復興蓋伊(Ge)的年輕人們則激進地拒絕這種定位,宣稱作為丹族人其意義就是要以蓋伊(Ge)為核心。但是,通過堅守他們所認為是一種專權的瓦哈比派,佩蒂特·帕魯這些年輕人們會不會在不經意間對作為一種地方社會控制的手段來支持蓋伊(Ge)專權呢?考慮到本文提到的年輕女性,一方面,在當地的貢派確實可以提供一些限制進入的權力,尤其是對扎西這種在任何丹族社群中最有權力的女人,當年長的男性領導者對整個社群造成很大影響而做出一些重大決策時,通常也會咨詢她的意見。而且貢派的確會在女性事件上實施一些最初的權力,包括入教、出生和割禮。然而,貢派社會內部及其本身就是一股明顯的霸權力量。年輕的丹族女性必須要接受割禮和入教儀式,這樣才能被傳統的丹族社群看作是為社會所接受,才可以結婚。很多生活在阿比讓的丹族女性拒絕這些丹族身份認同感的儀式標志,實際上有一些人參加號召國家法律執行的堅守運動,在科特迪瓦的一些書中將女性割禮定為非法。對于年長的瓦哈比派領袖甘納森來說,他認為蓋伊(Ge)只不過是男性長者炫耀、鞏固他們權力的一種手段。當這些長者要求為祖先或者蓋伊(ge)做祭祀活動時,女人必須遵從,她們要準備豐盛的筵席,這些食物和飲料實際上都被那些長者所消費了。之后,甘納森堅守當地蓋伊(Ge)的權威并且將自己與遙遠的正統伊斯蘭教徒(尤其是那些來自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派的領袖們)結盟,他們偶爾會到佩蒂特·帕魯拜訪,住在甘納森的清真寺里(p.c.)。然而,盡管甘納森將他成為瓦哈比派的決定與對蓋伊(Ge)的強勢看法聯系起來,把他的宗教定位僅當作是一種堅守來解釋,就可以把那些與信仰和其他因素有關的復雜定位簡單化了。
那些年輕的復興主義表演者們自認為蓋伊(Ge)在絕對的積極地位方面有很多原因,包括信奉蓋伊(Ge)表演確實讓一些人(例如專業鼓手高郵·提耶·讓-克勞德)賺到了他們急需的錢。按照洛奈教授(1992)所說,如果改信伊斯蘭教可以開拓商機,因此就會被看作是一種提升的手段,那么高郵則證明蓋伊(Ge)也可以做到。如果說高郵因為反對伊斯蘭教而失去了與穆斯林控制的商機,而敲鼓演出則為他提供了其他賺錢的渠道。因此,經濟振興是第二種爭議的一個額外因素,蓋伊(Ge)演出對于一些人來說是一種對經濟系統的堅守,那些經濟體制使馬恩這座小城市中的丹族窮困年輕人處于顯著的弱勢地位。
但是佩蒂特·帕魯年輕的表演者們信仰蓋伊(Ge)的主要動機還是以身份認同感為核心:即他們對祖先宗教的復興,以及對長輩、北方移民和瓦哈比派伊斯蘭教的反對。當這些年輕人通過蓋伊(Ge)表演實現地方認同政治時,反穆斯林、反北方的情感就演變成為國家層面所引發的政治問題。在當前科特迪瓦的政治危機中,把宗教、區域和種族的差異政治化,導致了公民政治選舉權被剝奪,引發暴力事件以及最終爆發的國家內戰。在北部和南部,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當街打架。聯合國記錄在案的至少有一件事,選舉政權總統勞倫·格帕格博(Laurent Gbagbo)在大選期間支持鎮壓和迫害穆斯林及北方移民,他們試圖在主要的城市阿比讓采取和平示威。①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2004.“U.N.Probes Abuses in Ivory Coast.”BBC News U.K.Edition,16 July. http://news.bbc.co.uk/l/hi/world/africa/3899483.stm.對于比耶米來說,他并不清楚佩蒂特·帕魯的年輕人以他們的表演來堅守推翻長輩們和北方人的權威這件事是否成功。但是他們反對伊斯蘭思想的表達難道真的為他們贏來了更多的話語權嗎?
這種情形的黑暗面必然會受到科特迪瓦當今國家政治認同危機下宗教選擇的影響。由于國家的不穩定性,我無法返回像馬恩這樣的邊境城市繼續研究這個課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聯合起來,不僅為了宗教和族群,也包括戰爭中的反對派。于是我帶著猜測和不解離開了那里。當改變宗教信仰成為一個復雜的話題,伴隨著對個體選擇有益的各種因素——信仰絕不是唯一的因素——選擇一種基督教認同感同時又夾雜著與南方的關系、與選舉政府的關系,還有更傾向于西方國家的文化、經濟以及政治選擇。伊斯蘭教意味著對西方權力的堅守,對于今天來說,更是對南方選舉政府的堅守,因為大多數反對派的新興力量控制了北方半個國家,他們都是穆斯林。
很明顯,這些通過蓋伊(Ge)表演的方式而引發的地方沖突存在著一種國家語境。面對日益緊張的介于北方與南方、穆斯林與非穆斯林間國家層面的局勢,年輕的蓋伊(Ge)表演者們如何回應呢?通過將蓋伊(Ge)表演與反穆斯林文化的復興聯系在一起,佩蒂特·帕魯的年輕人們是否將自己與國家的排外霸權結為聯盟?像盧瓦這樣生活在反對派控制地區的基督教徒們一樣,是否感覺到他們與南方政府控制區的關系比自己地方社群的關系更加親近呢?在宗教、區域和族群差異政治化的語境下,今天丹族人的生活很復雜,因為他們大多選擇尊崇非本土的權威。年輕的丹族人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通過反對長輩和蓋伊(Ge)的權威來遵從梵蒂岡教條?還是通過堅守瓦哈比派而追隨蓋伊(Ge)?蓋伊(Ge)不僅是歷史的,也包括將來的一段時間里,它們都會成為堅守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一種手段,這些都關聯著復雜的含義。然而,蓋伊(Ge)本身不僅是丹族認同感的核心,也是社會控制的一種形式。今天的丹族人民被困在與霸權斗爭的網中,一些人通過他們關于音樂和舞蹈的話語將自己與霸權主義聯系起來。正如阿布-盧格霍德(1990)提到的,“哪里有堅守,哪里就有權力”。通過對權力的論斷來分析堅守是一種有用的模式,它在多樣化的社群中揭示著相互交織、相互沖突的權力結構,這是一種很好的模式。在象牙海岸不斷增加的族群、宗教多樣化和沖突四起的語境下,音樂表演作為一種協調宗教和族群認同感實現的手段,在地方認同與國家影響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① 譯者注:考慮到題目的簡潔,翻譯時做了適當調整。
2016-03-09
J608
A
1008-2530(2016)02-0030-14
著者:丹尼爾·B.里德(Daniel B.Reed),男,美國民族音樂學家,印第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民俗與民族音樂學系副教授,主要從事西非音樂研究;譯者:魏琳琳(1980-),女,博士,博士后,內蒙古藝術學院講師。本文的翻譯與發表已獲作者丹尼爾·B.里德和文章初次發表刊物《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的授權,原文刊載于《民族音樂學》2005年第三期,第347-367頁。
本譯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青年項目“蒙漢雜居區的音樂與文化認同”(15CD136)、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58批面上資助項目“傳統音樂與文化認同——以蒙漢雜居區音樂實踐活動為例”(2015 M58128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