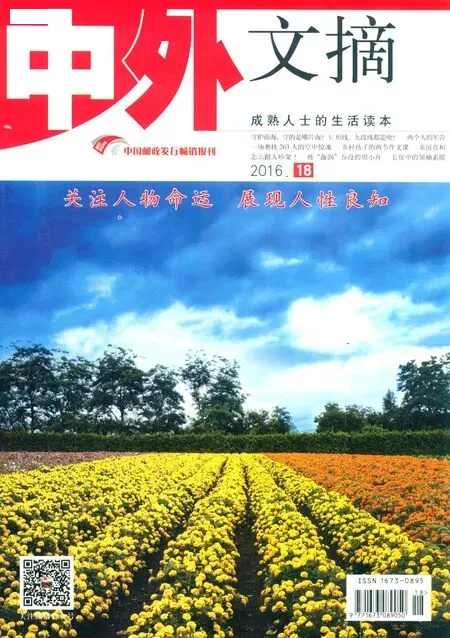文人的骨頭
□
祝 勇
文人的骨頭
□
祝 勇

對于明朝的滅亡,很多年后依舊在舊士人心里隱隱作痛。曾寫出《長物志》的文震亨,書畫詩文四絕,崇禎帝授予他武英殿中書舍人。崇禎制兩千張頌琴,全部要文震亨來命名,可見他對文震亨的賞識。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清兵攻破蘇州城,文震亨避亂陽澄湖畔,聞剃發令,投河自盡未遂,又絕食六日,終于漚血而亡,遺書中寫:“保一發,以覲祖宗。”意思是,絕不剃發入清,這樣才能去見地下的祖宗。
以“粲花主人”自居的明朝舊臣吳炳,在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按照吳炳的紀年,是明永歷二年——被清兵所俘,押解途中,就在湖南衡陽湘山寺絕食而死。
“粲花主人”餓死的時候,距離乾隆出生還有63年,所以乾隆無須為他的死負責。但來自舊朝士人的無聲抵抗,卻是困擾清初政治的一道痼疾。他們無力在戰場上反抗清軍,所以選擇了集體沉默。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康熙下詔開“博學鴻詞”科,要求朝廷官員薦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供他“親試錄用”,張開了“招賢納士”的大網。被后世稱為“海內大儒”的李颙,就有幸受到陜西巡撫的薦舉,但他堅決不從,讓巡撫大人的好意成了驢肝肺。地方官索性把他強行綁架,送到省城,他竟然仿效伯夷、叔齊的樣子,絕食六日,甚至還想拔刀自刎。官員們的臉立刻嚇得煞白,連忙把他送回來,不再強迫他。他從此不見世人,連弟子也不例外,所著之書,也秘不示人,唯有顧炎武來訪,才會給個面子開門。
顧炎武之所以受到李颙的特殊待遇,是因為他們情意相通。當顧炎武成為朝廷官員薦舉的目標,入選“博學鴻詞”科時,他也以死抗爭過,讓門生告訴官員,“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才被官府放過。同樣的經歷,還發生在傅山、黃宗羲的身上。
康熙畢竟是康熙,他有的是耐心。以刀俎相逼既然沒有效果,就干脆還他們自由,讓地方官府厚待他們,總有一天,鐵樹會開花。康熙深知,士大夫的骨頭再硬,也經不住時間的磨損。后來的一切都證實了康熙的先見之明。康熙多次請黃宗羲出山都遭到回絕,于是命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里抄寫黃宗羲的著作,自己在深宮里,時常潛心閱讀這部“手抄本”。這一舉動,不能不讓黃宗羲心生知遇之感,終于讓自己的兒子出山,加入“明史館”,參加《明史》的編修,還親自送弟子到北京,參加《明史》修撰。顧炎武的兩個外甥也進了“明史館”,他還同他們書信往來。至于李颙,雖已一身瘦骨、滿鬢清霜,卻被西巡路上的康熙下旨召見,他雖沒有親去,卻派兒子李慎言去了,還把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二曲集》贈送給康熙,以表示歉疚。連朱彝尊這位明朝王室的后裔,也最終沒能抵御來自清王朝的誘惑,于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舉博學鴻詞科,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入值南書房……
躲進剡溪山村的張岱也沒能頑抗到底,在浙江學政谷應泰的薦舉下,終于出山,參與編修《明史紀事本末》。
畢竟,新的政治秩序已經確立,新的王朝正蒸蒸日上,“復辟倒退”已斷無可能。顧炎武、黃宗羲早就看清了這個大勢,所以,他們雖然有心殺賊,卻無力回天。他們自己選擇了頑抗到底,終生不仕,卻不肯眼睜睜斷送了子孫的前程。連抗清英雄史可法都說:“我為我國而亡,子為我家成。”
新生的王朝歷經康熙、雍正兩代帝王,平穩過渡到乾隆手中,已過100多年的光陰,潛伏在漢族士大夫心底的仇恨已是強弩之末。就在這個當口,乾隆祭出了他的殺手锏——開“四庫館”,編修《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安徽學政朱筠上奏,要求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認為過去朝代的書籍,有的瀕危,有的絕版,有的變異,有的訛誤。比如明代朱棣下令編纂的《永樂大典》,總共一萬多冊,但在修成之后,藏在書庫里,秘不示人,成為一部“人間未見”之書,在明末戰亂中,藏在南京的原本和皇史宬的副本幾乎全部被毀,至清朝手里,已所剩無幾,張岱個人收藏的《永樂大典》,在當時就已基本上毀于兵亂(流傳到今天的《永樂大典》殘本,也只有約400冊,不到百分之四,散落在8個國家和地區的30個機構中)。因此,搜集古本,進行整理、辨誤、編輯、抄寫(甚至重新刊刻),時不我待,用他的話說:“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體,而窺天地之純”。乾隆覺得這事重要,批準了這個合理化建議,這一年,成立了“四庫全書館”。
對于當時的士人來說,這無疑是一項紀念碑式的國家工程,因為這一浩大的工程,既空前,又很可能絕后。所有參與其中的人,無疑在一座歷史的豐碑上刻寫下自己的名字。這座紀念碑,對于以“為往圣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為己任的士人們,構成了難以抵御的誘惑。
(摘自《故宮的隱秘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