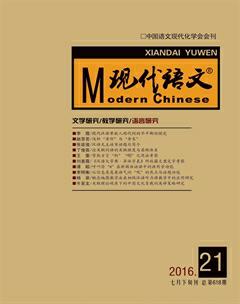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小說中的空間類型與身份狀態
○楊曉青
?
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小說中的空間類型與身份狀態
○楊曉青
摘 要:帕特里克·莫迪亞諾的小說描寫的是占領時期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作品中的人物多為身份缺失的人,對身份問題的關注凸顯莫迪亞諾對現代社會人類生存困境的反思。空間是莫迪亞諾小說中一個獨特的內質,筆者嘗試將莫迪亞諾作品中的身份與空間兩大要素結合,分析不同類型的空間中人物身份的存在狀態。
關鍵詞:身份 空間 存在
空間是與時間緊密相連的一個要素,包括性別空間、語言空間、地理空間等。本文所關注的空間多為地理空間,是指人物活動的場所、地點,這種實體空間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人物的內心體驗。莫迪亞諾筆下的故事多發生在城市空間中,城市中的街道、建筑物等在文中頻繁出現,城市是記憶的載體,對于城市空間的探析有助于我們把握莫迪亞諾小說中身份在城市空間中的呈現狀態、城市空間的變遷與記憶的關聯,以及它們如何對身份產生影響。
身份是什么?“身份是由一系列的自我觀點組成,這些自我觀點是在特定的群體或角色中,通過自我歸類或認同基礎上形成的。”[1]身份中囊括自我意識,身份是自我的外在標簽,而自我是身份的內在核心。身份的要素包括籍貫、姓名、職業等,是個體身份的外在標簽。身份標簽——身份——自我,形成了逐層遞進的內在關聯。探究個體的身份標識可以明晰個人的身份,而對個人身份的厘清則有助于理解深層的自我。莫迪亞諾對身份問題的關注其實是對個體自我存在的關注。本文對不同空間類型劃分主要是依據人物活動的場所,即文本中呈現出的不同地理環境來分類,小說中的城市空間分為以下幾個類型:隱私空間——家;公共空間——咖啡館;都市空間——巴黎。
一、隱秘空間與身份困惑
家是每個人的心靈歸宿,然而在莫迪亞諾筆下,家卻成為故事人物想要不斷逃離的場所,家庭關愛的缺失、家庭成員的不完整使人物對自我的身份產生最初的懷疑,“我”究竟是誰?這種對于自我身份的最初疑惑動搖了個體身份的穩定性狀態。《青春咖啡館》中露姬出生在索洛涅的一個村子里,但母親年輕時就帶著她來到巴黎,此后母女二人再也沒有回到索洛涅,露姬的母親說“我們已經沒有屋架了……”[2]索洛涅不僅是母女二人最初的生存場所,同時也代表著兩個人的最初身份,離開索洛涅隱喻著與她們最初身份的割裂。她們在巴黎租房子住,始終沒有一個固定的身份標識。露姬對于自我身份的懷疑是與她父愛的缺失不可分割的,露姬從小就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這種生理父親的缺位不僅造成了情感紐帶的斷裂,同時也產生了對自我身份的困惑。此外,露姬的母親為了謀生而在紅磨坊當酒吧招待,對于母親這樣的身份,露姬心理上是難以接受的。文中露姬向其他人介紹自己的母親為會計師,自己為學習東方語言的大學生。露姬的自尊心促使她撒謊,但這層謊言的背后暗示了她對自我及母親身份的美好設想,這種重構的新身份是建立在拋棄舊身份的基礎上。露姬產生了對自我身份的疑惑,而母親每天忙于工作,根本不與露姬交流情感,這種冷漠的母女關系更讓露姬產生如同孤兒般的無助感,家對于露姬而言缺少情感的歸屬感,更加劇了她對自我身份的厭惡。這些注定了露姬的逃離是必然的行為,她在一次次的探尋中尋找身份的多種可能性。
露姬的再一次逃離是在婚姻中尋找身份和生存的意義。露姬和她的丈夫有一個家,但是家中冷清且裝置簡單。家中的環境暗示了露姬的丈夫是一個機械冷漠的人,他選擇和露姬結婚只是由于露姬長得秀麗,婚后也缺乏對妻子的關愛,露姬認為真正的生活不是這樣的,她沒能在和丈夫共同的家中找到自我賴以依托的歸宿。“雅克林娜·舒羅”這一舒羅的妻子的身份并不能滿足露姬想要尋找的真實身份,她在離開丈夫后毅然拋棄了這一姓名,用回了自己的原名“雅克林娜 德朗克”。真正的生活應該是實現個人的多種可能性,因此露姬要尋找真正的自己,在家、咖啡館、酒吧等一個個空間中探尋真正的自我。
露姬是莫迪亞諾作品中許多人物的縮影,無論是《地平線》中逃離父母的博斯曼斯,還是《陌路人》中遠離家庭的女孩,亦或是《夜半撞車》中父子關系冷漠的青年,他們或多或少都有著在經歷父親或母親等家庭成員的缺失后帶來的身份困惑,都在心理上不同程度體驗著缺少父母關懷的孤兒感,難以將家庭當作心靈的歸宿更難以借家庭空間構建自我身份。遠離家庭的他們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游蕩,流連于一個個咖啡館、酒吧、飯館,在不同的旅館住宿,但是他們的靈魂卻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安放。
二、公共空間與身份虛構
莫迪亞諾作品中的公共空間多為咖啡館、酒吧,正是由于公共空間的存在才讓無數的偶遇和相逢成為可能。《青春咖啡館》中故事大多發生在孔岱咖啡館,每個人來到這里的理由不同:避難、逃離、揮霍青春。孔岱咖啡館已經成為諾亞方舟,之所以能夠吸引這些青年男女,就在于人們能在此獲得某種心靈慰藉。在咖啡館中每個人都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極力忘記自己的過去,大學生、露姬、偵探、羅蘭都用化名的假身份與他人交往,被命名為“露姬”后的雅克林娜仿佛脫胎換骨,而她的真名早已不為人所知,與之一同被埋葬的是不堪回首的過去。這種虛構的假身份帶給人物某種程度上的心理安全感——不必擔心被他人摸清自己的底細。
在這些公共空間中個人的真實身份難以辨識,同時也因為人與人彼此之間的小心翼翼界限,有限度地了解而又不觸及對方的隱私,彼此對于對方的不真實身份心知肚明而從不戳穿,從而讓使用虛假身份成為可能。露姬在離開丈夫后經常來孔岱咖啡館,這片具有磁力的小空間吸引了露姬,她總是混在人群中默默不語,極力抹消自己的存在。新的身份帶來了新的生活體驗,但建立在假身份基礎上的生活如同流沙般充滿不穩定性。公共空間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短暫且脆弱,消失是常態。“那些人在某一天消失了,人們才發現對他們一無所知,連他們的真實身份都不知道。”[3]他們曾經存在過,但沒有任何東西能夠證明他們的存在,就連唯一殘存在人們腦海中的名字也是假的,謎一般的身份下被遮掩的真實個體,而我們永遠不知道他們是誰,個體的存在如同影子般悄然而逝不留任何痕跡。
三、都市空間與身份迷失
莫迪亞諾筆下的空間多為巴黎等大城市,巴黎不僅承載了最美好的人生回憶,還見證著種種難堪的過往。而今它已逐漸衰老,那些曾經鮮亮的回憶早已漸漸消失在時光中。莫迪亞諾用手中的筆力圖還原一個曾經的巴黎。但是他筆下的巴黎更像是充滿立體感的三維空間,不同的街區、路口、大廈、門牌號在文中若隱若現,充滿縱深感的空間極易讓人在其中迷失方向。高樓林立的大廈和縱橫交錯的街道營造出的空間想象感和文中不斷出現的“地圖”意象帶來的視覺平面感互相交錯成為一個立體形象的三維空間巴黎。巴黎具有它自身獨特的元素,如環狀的街區劃分、燈火輝煌的酒吧、浪漫憂傷的爵士樂。巴黎的獨特更在于生活在巴黎的人們與其難以割裂的情感紐帶,1968年五月風暴中學生關于爭取權利的街道游行示威不僅是一次精神上的“尋父”,同時也作為獨特的歷史記憶融化在巴黎空間中。對自我身份的質疑與追問,對個體存在狀態的反思在莫迪亞諾小說中呈現出立體縱深的空間與渺小卑微的個體之間的鮮明反差。“他們還沒有單獨的生活,而是同樓房的門臉兒和人行道融為一體。”[4]《一度青春》里的路易和奧迪兒在這個偌大的城市空間中被高樓、街道吞沒消融,喪失了自我的主體性,他們就像瞬間消失的氣泡,凸顯出人物存在的悲愴性和凄涼感。
戶口本中有一欄即為家庭住址,然而小說中的大部分人是沒有家庭的,沒有固定的住址,他們如同浮萍般在城市間飄蕩并常常變換住址,個人的身份處于不穩定狀態,總是處于行走之中。這也是莫迪亞諾小說中的人物如同影子般難以確定的原因之一。人物行走在白天也游蕩在黑夜,游走于都市中心也逃遁于郊區。行走在路上,行走于尋覓,行走于未知。這些沒有根基的到處游蕩的幽靈,唯一能把他們存在的片刻痕跡記錄下來的是曾經生活過的、待過的場所。但是偌大的城市空間中個人是如此渺小卑微,人物在城市空間中行走但極易迷失于其中。巴黎的環狀分布街區如同彼此隔絕的區域。《地平線》中的博斯曼斯產生心理上的錯覺,即一個街區就是一個獨立的王國,忘卻過去的最有效辦法就是到另一個街區以一個新的姓名新的身份開啟新的生活,于是人物總是處于行走之中,不停地在街區之間游蕩。然而呈同心圓狀的環形街區分布,寓意人物即使不斷逃離,最后的結果很有可能是回到了最初逃離的地方。身份的探尋亦是如此,迷失在對自我身份的困惑中,不斷改變更名換姓以求探尋多重身份的可能,最終結果是永遠喪失了自己的身份。《暗店街》中居依對自我身份的尋找如果用一個個地點來貫穿大致為餐館——酒吧——事務所——中學——山區別墅——島嶼,自我身份迷失在支離破碎的空間中。居依想借對空間的探尋去尋找自我身份的種種細節,但散落的細節只能拼湊出一個模糊不清的人物影子,真實的居依早已遺失在空間的碎片中。文章結尾居依要去羅馬暗店街2號尋找自己的身份,顯而易見是徒勞的。
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相似的街道樓房使城市中的空間難以辨認,人物通過記憶門牌號碼來標明自己的存在印記,“他決不會忘記那些大樓所在的街名和門牌號碼。這是他跟大城市的冷漠和千篇一律斗爭的方法,可能也是跟游移不定的生活斗爭的方法。”[5]這也是跟不確定的身份抗爭的手段,然而大樓不斷重建、門牌號碼也在不斷修改,沒有永恒固定的存在。憑借門牌號碼標明存在的努力是失敗的,無論是家、旅館還是咖啡館、酒吧抑或是樓房街道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磨損或消失,沒有永恒的固定空間存在。即使是幸存的個別建筑,亦難尋舊日的痕跡。與歲月流逝相伴消失的還包括歲月難再的凄涼心境。《往事如煙》中讓的自問“難道景物依然如故嗎?譬如有一天晚上,我同羅克洛瓦一起徒步穿過的這個轉盤,是否就是原先的那一個?”[6]這種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的人生哲學,更體現出對時光流逝的感傷無奈,即使這些建筑物依然存在,但已無法回到過去。空間的不穩定使記憶沒有一個可靠恒久的載體,從而使身份的認知缺乏穩定的依托,身份的尋找也必然陷入僵局。
四、身份迷失與個體逃離
中立區指不偏向任何一方,保持獨立的地區。莫迪亞諾的小說中多次出現中立區,《夜巡》中的中立區是指無戰爭硝煙的中立國瑞士,隨后中立區的含義在文中不斷具體化,《八月的星期天》中的公園,《青春咖啡館》中的遠離市中心的街區。從中立國——公園——旅館,空間的縮小象征著人物內部心理空間的縮小,他們在一次次探尋不同種類的空間后最終只能縮回到自己的內部世界。人物對中立區有種偏愛情結,也許因為中立區與他們的身份一樣具有模糊性。中立區沒有明確的定義,它是人們內心對某些遙遠且從未涉足的地區的感知。羅蘭對中立區的描述是“在巴黎是有些中間地區、一些無人地帶的,那里處在一切的邊緣,處于中轉過境甚或懸而未決狀態。在那里能享受到一定的豁免權。”[7]這種無人監管的中間地帶顯然是不存在的,但是它從未被羅蘭涉足,心理上的遙遠和視覺上的陌生造成這些地點是新奇的、充滿人生任何可能性的錯覺。因而露姬和羅蘭常常漫步在午夜巴黎的這些中間地帶,享受著逃離的快感和游蕩的沉醉。中立區這些實體的空間已經逐漸轉為個體心理空間,伴隨著理智的漸漸清醒,他們意識到真正的中立區其實是不存在的,褪去了新鮮感之后產生了清醒的絕望,于是他們只能迅速尋找下一個中立區。在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歸屬感的露姬注定無法長久游蕩在中立區,無數次的逃離是對生活信心的喪失,因而她選擇跳樓自殺,讓年輕絢爛的生命戛然而止。
五、身份確認與固定點
家、咖啡館、街道,人物在不同的城市空間中來回游走,卻從未在任何一個空間真正安放自己的內心,抓住他們存在的痕跡。《青春咖啡館》中保齡為了能留住自身存在的痕跡,創立了固定點理論,包括人物、時間、地點三個要素。固定點把一個人存在的片刻瞬間以文字的形式記錄下來,是個體曾經存在過的證明。然而一個人的一生中存在許許多多的固定點,十四點鐘的露姬我們能確認她在哪里,下個瞬間能確認她的存在嗎?以時間為基本要素的固定點有千千萬萬個,有許多固定點散落在時間長河之中被人遺忘,某幾個固定點難以勾勒出個體完整的人生主線。試圖以時間來確認不斷變動的個體,這種途徑本身就是徒勞的。逃離的個體、數不清的日期、不斷變動的地點,這使得個體身份的確認困難重重,呈現出人類喪失存在感的生存狀態。
露姬的人生如同莫迪亞諾在《暗店街》中對“海灘人”的描述,每個人的存在如同沙灘上的腳印瞬間被沖洗掉,生存即虛無。莫迪亞諾對個體主體性喪失的揭示是人們精神世界危機的體現,也與法國動蕩不安的局勢以及莫迪亞諾自身的身份困惑有關。莫迪亞諾筆下的身份與個體存在緊密關聯,個體存在需要借助身份這一外在標簽來證明,在某種程度上凸顯了生存的荒誕性。我存在,但我無法證明自己的存在。我存在,但其實我并不存在。
六、結語
莫迪亞諾自述“我一想到什么人,就必須把他放在一個地方,一條街,一棟房子里,地名能讓人想起許多事情。”這也是莫迪亞諾小說中充滿不同類型空間的原因。人物在家庭、咖啡館、街區空間的游走經歷了身份的困惑——身份的虛構——身份的迷失的漸變過程,此外,空間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發生改變,身份的尋找難以真正實現。而借虛構中立區空間來逃避身份缺失的恐慌感是人物在無力抵擋被吞噬下的行為,即使是選擇固定存在痕跡的方位標也只能確認個體的短暫存在,在時間的洪流下,我們每個人都只是瞬間消失的氣泡。這不僅是莫迪亞諾對人類生存境遇的悲哀感受,也是每個個體生存現狀的真實寫照。
注釋:
[1]吳小勇,黃希庭,畢重增,茍娜:《身份及其相關研究進展》,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第9頁。
[2]金龍格譯,[法]帕特里克·莫迪亞諾:《青春咖啡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頁,33頁。
[3]金龍格譯,[法]帕特里克·莫迪亞諾:《青春咖啡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頁。
[4]李玉民譯,[法]帕特里克·莫迪亞諾:《一度青春》,桂林: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128頁。
[5]徐和瑾譯,[法]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地平線》,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頁。
[6]陳筱卿譯,[法]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往事如煙》,桂林: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頁。
[7]金龍格譯,[法]帕特里克·莫迪亞諾:《青春咖啡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頁。
參考文獻:
[1]柳鳴九.二十世紀文學中的荒誕[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2]曾艷兵.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3]周婷.莫迪亞諾的新寓言小說《夜巡》:現實與臆想的結合[J].法國研究,2010,(11).
[4]楊冬.莫迪亞諾小說中的“身份遺失”[J].福建省外國語文學會2012年會論文集,2012,(12).
(楊曉青 寧夏銀川 寧夏大學人文學院 750021)
基金項目:(本文為寧夏大學2015年研究生創新項目“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小說創作論”,項目編號[GIP 2015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