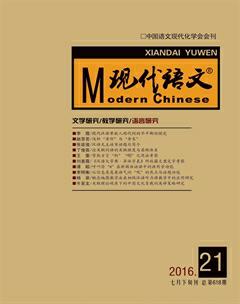“以杖荷蓧”之“蓧”眾說平議
摘 要:“以杖荷蓧”出自《論語·微子》,其中“蓧”字歷來爭議頗多,筆者綜合各家觀點,認為“蓧”應該釋為“一種盛器 ”。
關鍵詞:以杖荷蓧 蓧 盛器
一、“蓧”之爭
《論語·微子》:“子路從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對句中的疑難詞“蓧”歷來爭議頗多,筆者所見,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1.古代鋤草的工具。大多數學者都持這種觀點,如:楊伯峻《論語譯注》將“蓧”釋作“古代除田中草所用的工具”,金池主編的《論語新譯》釋為“古代鋤草的工具”,李澤厚《論語今讀》譯為“鋤草的農具”,王力《古代漢語》解為“古代除草工具”,安作璋主編的《論語辭典》同樣譯作“竹制除草農具”。另外,《辭源》《漢語大詞典》《辭海》等工具書都將“蓧”釋為“古代耘田所用的竹器”。①這種觀點在學術界較為通行。
2.古代耕田的農具。朱東潤《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將“蓧”注為“耕田器”,《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注為“耕田用的農具”,錢遜《論語淺解》中釋為“古代耕田用的竹器”。
3.江西南昌用于水田除草的農具,即腳歰。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是清代學者劉寶楠,腳歰“形如提梁,旁加索,納于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踏草入泥中”。
4.古代的一種盛器。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主要有于智榮和李立(2007)。
二、眾說平議
1.“古代除草的農具”一說有明顯缺陷。主張此觀點的各家都并未對“蓧”的形制做出清楚的解釋。根據常識可知,除草的工具一般為長柄,元代王禎的《農書》農器部分附有圖形,其中收錄的除草工具“耰”“耨”“钁”“臿”無一不是長柄,但這種長柄的工具很難再“以杖荷”,荊貴生也曾經質疑:“用拐杖挑著除草工具,又怎么個挑法呢?老人直接把除草工具扛在肩上不是更好些嗎?”②這是疑問之一。另外,如果“蓧(莜)”是古代除草工具,那么古書對它一定有所記載,但《爾雅·釋器》的除草工具條目中收錄了“劬斸”“斫”等,并未收錄“蓧”字。古代的農事專書——元代王禎的《農書》和明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都在耕耘器具部分對“耰”“耨”“錢”“銚”“钁”“鉏”等古代除草工具的形制功用等作了詳盡說明,并附有圖形,但也沒收錄“蓧”字。③這也可以說明除草的農具“蓧”在古代是不存在的。因此,我們認為將“蓧”釋為“古代除草的農具”不僅不符合實際,缺乏根據,而且也造成了文意上的不通暢。
2.“古代耕田的農具”一說也存在明顯缺陷。“蓧”,從字形上來看從“艸”,其材質應該是“艸”,而耕地的農具一般比較堅硬,多為鐵制。通過查閱元代王禎的《農書》和明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發現二書所載耕耘器具部分并未收錄“蓧”,而且書中收錄的用于耕地的工具多為鐵制或木制,字形上多從“金”或“耒”,并未發現從“艸”的耕具,從字形方面證明了“蓧”不可能為“古代耕田的農具”。另一方面,學者之所以將“蓧”釋為“耕田的農具”大概是受下文“植杖而蕓”中“蕓”的影響,王力《古代漢語》注釋“蕓”通“耘”,學者大概誤將“耘”釋為“耕耘”,從而將“蓧”釋為“耕田用的農具”。《說文解字》“艸”部下收錄“蕓”字,釋為“艸也,似目宿,從艸云聲。”其“耒”部下收錄了“耘”字,釋為“除苗間穢也,從耒,員聲耘,耘,或從蕓”,可見“耘”義為“除草”,并無“耕地”之義。因此,將“蓧”釋為“耕田的農具”不符上下文文意,也是不正確的。
3.“江西南昌用于水田除草的農具,即腳歰”的觀點難圓說。清人劉寶楠認為:“蓧”就是南昌人除草用的工具——“腳歰”。它的形制和除草方法是:“形如提梁,旁加索,納于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踏草入泥中”。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子路行,遇荷蓧丈人”的地點是孔子“去葉,反于蔡”的途中。《孔子年譜》云:“前490年(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六十二歲。孔子自蔡到葉,有與葉公問答。由葉返蔡,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隱者途中相遇。”《古代地名》注云:“葉:古邑名,一稱‘葉縣,春秋地名。在今河南葉縣境”;“蔡:古國名,建都上蔡(今屬河南)”。《河南通志》卷六十六《隱逸》也把“荷蓧丈人”列為葉人。“葉”在今河南葉縣,“蔡”也在今河南境內,這說明孔子遇荷蓧丈人是在河南境內。劉寶楠認為“腳歰”是江西南昌用于水田除草的工具,這與孔子遇荷蓧丈人的地點有較大出入。另外,春秋時期的“葉”和“蔡”都在現今河南省境內,處于秦嶺—淮河以北,該地區普遍種植粟、黍類旱地作物。下文提到“(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此外未言水生之稻,可以推知黍為丈人家的主要食糧。雖說農家待客之物非必自產,但以自給之黍來饗客顯然更能彰顯農家本色,就荷蓧丈人而言亦能暗示其作為“隱者”的自足自得。而且丈人“五谷不分”之語,按明代宋應星的說法,上古時期的“五谷”專指麻、菽、麥、稷、黍等五類旱地作物,并不包括“稻”。此外,在碰上荷蓧丈人之前,孔子師徒于同一地區見過長沮、桀溺等類似荷蓧丈人的耕隱者。《論語·微子篇》記載了孔子使子路問津的遭遇,其中桀溺言有“耰而不輟”句,《漢石經·論語》中作“櫌不輟”,《說文解字》引其例訓“櫌”為“摩田器”④。另據《群經補義》考證:“耰,摩田也,又曰覆種。……問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后,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⑤可知,“耰”是一種用碎土覆種的農具,將其動詞化為“耰而不輟”,表明這是一種典型的旱地勞作方式。由此旁推,荷蓧丈人也應該身處旱地耕作區域之中。因此,“腳歰”的觀點也不成立。
我們贊同第四種觀點,即“蓧”是古代的一種盛器。
查閱《說文解字》發現,《說文解字·艸部》未收“蓧”,但收錄了“莜”。“莜,草田器,從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蓧”。徐鉉補注:“今作蓧,徒弔切”。陸德明《經典釋文》:“蓧,又作‘莜,并字異而義同。”由此可知“蓧”與“莜”為異體字。《玉篇·艸部》:“莜,草器名”。何晏《論語集解》引包咸曰:“蓧,竹器”。邢昺疏:“丈人以杖擔荷竹器”。朱熹《論語集注》:“蓧,竹器名”。《史記·孔子世家》:“遇荷蓧丈人”。裴骃《集解》:“蓧,竹器名也”。《廣韻·嘯韻》《集韻·蕭韻》均將“蓧”釋作“艸田器”,到《康熙字典》中仍然解作“草田器”。“草田器”“草器”“竹器”的“草”和“竹”為表質料的定語,表示“蓧”是用草和竹子編成的。湯可敬《說文解字今釋》也主張“莜”為“草編田間用器”。endprint
其次,從字形上來看,“莜”“蓧”應該是盛器。“蓧”義符為“艸”,應該是草木編織成的器具。清吳凌云《吳氏遺著》認為“古作‘莜本字,今作‘蓧俗字,而匚部又有,訓田器蓋‘莜之別出字。”⑥“”從“皿”,“皿”一般都用來作盛器。清崔應榴《吾亦廬稿》:“王氏《農桑圖》曰:‘蓧字從草從條,取其象也,即今盛谷種器,與蕢同類。”⑦今人錢穆亦主張“‘蓧為竹器名,籮簏之屬”。⑧
據于智榮和李立(2007)考證,古代辭書和古訓家對“蓧”“莜”二字的解釋與對古代盛器的詮釋一致。《說文》中訓作“草田器”“草器”的只有“莜”“蕢”二字,《說文·竹部》中釋作“竹器”的主要有“簏”“篿”“?”“籫”等字,《漢語大字典》中分別釋為:
①簏,竹篾編的盛物器,形制不一。
②篿,圓形竹器。
③?,一種竹箱。
④籫,盛筷、勺的竹籠。
綜上可知,《說文解字》中以“竹器”來解釋的名物都是盛器。《說文》前后體例一致,“蓧”(莜)的釋語與這些字一致,也可以從側面說明它們同為盛器。
另外,元代王禎的《農書》和明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在盛器、簸揚之器部分收錄一“篠”字(可能是“蓧”的異體字),釋為北方盛粟種的簍,還附有圖形。而且直至今天,“子路遇荷蓧丈人”的河南地區仍在使用類似于“蓧”的盛器,今名“竹籃”,圓形,中間有橫梁。莊稼需要除草的時節,農民下地勞作時都會帶一個竹籃,一方面方便把除掉的雜草運出田地,防止其復生,另一方面可以將一些野菜帶回家喂養牲畜。正是由于“蓧”是一種中間有橫梁的盛器,所以可以用杖來荷。
綜上所述,“蓧”應為以草木或竹編織而成、帶有橫梁的盛器,大致相當于目前北方農村常用的“竹籃”。以此作解則文從字順。
注釋:
①關于“蓧”字各家的這些解釋,可參見于智榮、李立《〈論語〉“蓧”字解詁》,載《孔子研究》2007年第6期。
②荊貴生.荊貴生語言文字論文集[C].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169.
③于智榮,李立.<論語>“蓧”字解詁[J].孔子研究,2007,(6):117.
④程樹德.論語集釋(下)[M].中華書局,2013:1453.
⑤程樹德.論語集釋(下)[M].中華書局,2013:1454.
⑥程樹德.論語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0:1272.
⑦程樹德.論語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0:1272.
⑧錢穆.論語新解(修訂版)[M].北京:三聯書店,2005:473.
參考文獻:
[1]于智榮,李立.《論語》“蓧”字解詁[J].孔子研究,2007,(6).
[2]荊貴生.荊貴生語言文字論文集[C].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
[3]程樹德.論語集釋(下)[M].北京:中華書局,2013.
[4]錢穆.論語新解(修訂版)[M].北京:三聯書店,2005.
(周曉彥 遼寧沈陽 遼寧大學文學院 11003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