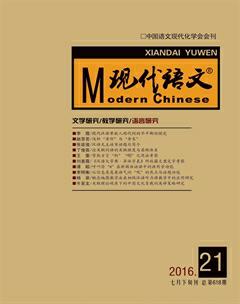謙敬副詞“伏”“竊”的語法化過程及對比
摘 要:謙敬副詞“伏”“竊”都由動詞語法化而來。本文從詞匯意義與結構形式兩個角度分別探討二者的語法化過程,并指出它們在這一過程中的相同與相異之處。二者都由動詞演化而來,且在具體語境中頻繁作狀語共同促成語法化的進程;具體來源不同,二者隱含的副詞詞義特點以及表達自謙的角度各不相同。
關鍵詞:“伏” “竊” 語法化
一、前言
謙敬副詞是漢語副詞中一個封閉的詞類,它數量有限,在現代漢語中大多已不再使用。本文以“伏”“竊”這兩個常用的謙敬副詞為研究對象,考察它們的語法化過程,分析謙敬副詞形成的動因。表謙類的“伏”“竊”由動詞演變為謙敬副詞經歷了語法化的過程,語法化是一個涉及語言演變的術語,包含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其涉及的因素較多,主要包括詞匯意義、結構形式等,謙敬副詞“伏”“竊”的形成過程相應地發生了詞匯意義和結構形式兩方面的改變。這兩者是同一個問題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在語法化的過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促進。詞匯意義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實詞詞義的虛化,結構形式的變化則表現在句法位置與結構功能兩個方面。下面分別從詞義虛化與結構形式演變兩個角度探討謙敬副詞“伏”“竊”的語法化過程以及二者在這一過程中表現出的相同與相異之處。
二、謙敬副詞“伏”的語法化過程
(一)“伏”語法化過程中的語義變化
“伏”從人從犬,屬會意字,人像犬一樣匍匐著,本義為“俯伏、趴下”,這是其早期常見的動詞義,作動詞用的“伏”由本義引申出許多其他動詞義,主要有“隱匿、埋伏”“降服”“受到(應得的懲罰)”等。如:
(1)王在靈囿,麀鹿攸伏。(《詩經》)
(2)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老子》)
(3)后壹奸罪發露伏誅。(《三國志·吳書·吳主傳》
例(1)取“伏”的本義,例(2)、例(3)則是“伏”的引申義,分別為“隱匿”“受到懲罰”。
表示謙敬的“伏”與其他動詞義沒有很大關系,它由本義演變而來。從語料來看,“伏”在漢代開始出現,并且用例逐漸增多。謙敬副詞“伏”雖表示尊敬,在語句中可不譯出,但我們仍能感受到它在詞匯意義中的殘留。如:
(4)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漢書》)
(5)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漢書》)
以上兩例“伏計”“伏惟”中,“伏”雖已完全語法化為副詞,但其殘留的詞匯意義與動作性的“俯伏”有很大關系。根據《周禮·春官·大祝》,臣子對君父的拜禮為稽首,行稽首拜時,取跪姿,先拱手下至于地,然后引頭至地,在地上停留一段較長的時間再舉起,這與“伏”本義所表示的動作大體上是一致的。而謙敬副詞“伏”多用在奏章書信中,書面難以再現稽首禮,要體現敬意必然從現實取材,“伏”進而由普通的動作行為發展為表現敬意的禮節性動作,意義也同時虛化。由此,“伏”由動詞義的“俯伏、趴下”虛化為表謙敬的副詞義。
(二)“伏”語法化過程中的結構形式變化
除詞義虛化,“伏”在句法位置和組合功能上也相應發生變化,最終促成謙敬副詞“伏”的產生。作動詞用的“伏”與一般動詞無異,在句中作謂語,是句子的主要成分。組合功能上后可帶賓語,前可受狀語修飾,與其他動詞可構成連謂結構。例如:
(6)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詩經》)
(7)有鳥焉,其狀如烏,人面,名曰囗冒噡,宵飛而晝伏,食已曷。(《山海經》)
(8)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國語》)
(9)鼎乃淪伏而不見。(《史記》)
例(6)中,“伏”為動詞,后接賓語“其辜”;例(7)中,動詞“伏”前有時間名詞作狀語修飾;例(8)中,“伏”作為動詞與同是動詞的“竄”構成連謂結構;例(9)與例(8)性質一樣,不同之處在于“伏”與并列的動詞“不見”由連詞“而”連接,這些是普通動詞的一般用法。動詞“伏”向副詞演變始于其在句中與其他動詞構成的連動結構。如:
(10)吏民益凋敝,輕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漢書》)
(11)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兵法》)
(12)夫蛟龍伏寢于淵,而卵割于陵。(《淮南子》)
以上例句中“伏匿”“伏藏”“伏寢”可作連動結構解釋,也可作狀中結構解釋。受漢語“V1V2”式連動結構焦點在后的語法規律影響,動詞“伏”逐漸由句中核心成分向次要動詞變化,其動詞性也慢慢減弱,后逐漸虛化為類似方式副詞的成分。說“類似”是因為相對于副詞而言,其動詞性還是比較突出的,而且這種用法也并不是普遍到可以歸為新的一類詞性。連動結構中“伏”逐漸歸為狀語成分為謙敬副詞的產生奠定句法基礎,即“伏”可置于動詞之前作修飾成分,再加上特定的臣屬對皇帝等語境條件,使其最終語法化成為謙敬副詞。
已經語法化為謙敬副詞的“伏”早期用于表達臣對君的敬意,往往與心理動詞及行為動詞搭配。如:
(13)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親廟。(《漢書》)
(14)桓彥范奏曰:“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參聞政事。”(《大唐新語》)
例(13)中,謙敬副詞“伏”修飾心理動詞“念”,此外還有“伏愿”“伏計”“伏憂”“伏思”“伏惟”等常見“伏+心理動詞”的搭配。例(14)中,“伏”修飾行為動詞“見”,古漢語典籍中頻繁出現的還有“伏聽”“伏觀”“伏聞”“伏望”等。
漢代古漢語典籍中,謙敬副詞“伏”多用來傳達臣對君的敬意,隋唐五代時期,“伏”已不限于君臣之間,其他“下”對“上”的“尊敬”之義都可用它表達。如:
(15)伏望將軍希垂照察。(《敦煌變文》)
(16)今朝欣逢,伏望大圣慈悲,與我小談法味。(《敦煌變文》)
以上兩例出自《敦煌變文》,已屬近代漢語的范疇,文中出現的謙敬副詞“伏”的尊敬對象不再限于君,還可為將軍、大圣、和尚、上人等等。
三、謙敬副詞“竊”的語法化過程
(一)“竊”語法化過程中的語義變化
“竊”本義為“偷竊”,《說文解字》:“盜自穴中出曰竊。”早期古漢語典籍中多作動詞用,取其本義,后由動詞義“偷竊”引申發展出副詞義“私下地、偷偷地”,為方便討論,此副詞我們用“副1”表示。古代漢語典籍中動詞義與副1義比較常見。如:
(17)無敢寇攘,逾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尚書》)
(18)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山海經》)
(19)臣竊笑之!(《韓非子》)
(20)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晏子春秋》)
例(17)與例(18)中取“竊”的動詞義“偷竊”,例(19)與例(20)中“竊”為副詞,修飾其后動詞“笑”與“議”,義為“偷偷地”。劉淇在《助詞辨略》中把謙敬副詞“竊”解釋為“謙詞,不敢徑直以為如何,故云竊也。”意指其暗含“私下”之義,這與副1“竊”在意義上有很強的關聯性。由此,謙敬副詞“竊”由副1“竊”進一步虛化而來。在具體的語境中,它往往被發表意見的一方用以表示所發議論或見解是個人不成熟之私見,以此來表自謙。謙敬副詞“竊”在戰國末期的《韓非子》《呂氏春秋》等著作中已經出現。如:
(21)臣竊愿陛下之幸熟圖之!(《韓非子》)
(22)臣竊以慮諸候之不服者,其惟莒乎!(《呂氏春秋》)
(23)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長安君。(《戰國策·趙策四》)
以上三例中“竊”皆用在臣下對君王的對話中,臣下發表自己的看法或建議,“竊”為謙敬副詞作修飾之用,表現個人不成熟之私見,這是副1“竊”在特定的語境條件下語義上的進一步虛化。
(二)“竊”語法化過程中的結構形式變化
以上是從語義虛化角度看謙敬副詞“竊”詞義的演變來源,此外,與其相輔相成的還有“竊”的句法位置和組合功能的變化。作為動詞,“竊”作謂語,為句中的主要成分,與其他動詞無異,組合功能上多為后接賓語。如:
(24)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墨子》)
例(24)中,“竊”為動詞,以“桃李”為賓語,這是動詞的一般用法。動詞“竊”在詞義上發生引申,使相應的結構關系和句法功能也發生變化,動詞“竊”虛化為副1“竊”后,其從句中核心成分變為作修飾用的附屬成分。已經演變為副1的“竊”置于動詞之前,頻繁在句中作狀語,在詞義虛化的基礎上使副1“竊”的詞義和語法功能更加穩固。如:
(25)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史記》)
(26)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左傳》)
謙敬副詞“竊”是副詞內部的進一步虛化,但句法位置及組合功能與副1“竊”沒有很大區別,同是置于動詞之前作狀語,為修飾成分。如:
(27)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呂氏春秋》)
(28)今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韓非子》)
以上兩例中,謙敬副詞“竊”位于動詞“意”“聞”之前,在句中作兩者的修飾成分,在“下”對“上”的對話中表示個人看法只是一己私見。
謙敬副詞“竊”既可以修飾行為動詞,也可以修飾心理動詞,這一點與副1“竊”的用法是一致的。如:
(29)竊聞眾口鑠金,浮石沉木。(《三國志·魏書》)
(30)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辨過君。(《戰國策·趙策一》)
例(29)與例(30)中“竊”都作副詞,“聞”與“觀”都為行為動詞,兩個副詞“竊”都用以修飾行為動詞,但兩者卻并非同一類副詞。例(29)是臣下對君王的上疏,“竊”在此為謙敬副詞,詞義并不重要,刪去也不影響句義,只是表達尊敬,可不譯。例(30)出自門客對主人說的話,雖也屬“下”對“上”的語境,但此“竊”表“私下地、偷偷地”,這句話應翻譯為“我暗自觀察您和蘇秦談話,他的辯才比您強”,副詞“竊”的詞義對句義的完整性來說不可或缺。由此,我們在判斷是否是謙敬副詞時,首先從語境出發,看是否處于“下”對“上”的交流語境,再看副詞“竊”對句義的構成是否必不可少。若處于該語境,且詞義不參與句義構成,則可判斷為謙敬副詞。
四、結語
“伏”由本義“俯伏、趴下”義虛化出多用于卑者對尊者的信件或奏折中表示尊敬的謙敬義;結構形式上也由作句子的主要成分,即后帶賓語、受狀語修飾或與其他動詞組成連謂結構邊緣化為修飾成分。“竊”先由本義“偷竊”引申發展出副詞義“私下地、偷偷地”,進而發展出表示己方所發議論或見解是個人不成熟之私見的謙敬義;在結構形式上謙敬副詞“竊”是“私下地、偷偷地”副詞義的進一步虛化,二者同置于動詞之前作狀語,為修飾成分。
縱觀謙敬副詞“伏”“竊”的語法化過程,二者既相異又相同。
第一,“伏”和“竊”各自來源不同,所以隱含的副詞詞義特點以及表達自謙的角度各不相同。實詞虛化為語法成分以后,多少還保留原來實詞的一些特點,虛詞的來源往往是以這些殘留的特點為線索考究出來的。如“伏”本義為“俯伏、趴下”,它語法化為謙敬副詞以后,殘留的實詞詞義與動詞義相關的“拜伏”這種禮節性動作有很大關系,是從“拜伏”這一角度表達自謙。又如“竊”本義為“偷竊”,偷竊不能光明正大,進而引申為“私下地、偷偷地”,之后又虛化為謙敬副詞,隱含“不敢徑直以為如何”義,是從“私下、不敢徑直做某事”角度表達自謙。
第二,“伏”和“竊”都由動詞演變而來,詞義上是各自動詞義的虛化,結構形式上是各自動詞由句中核心謂語成分逐漸演變為作修飾之用的附屬成分,最后語法化為詞義虛化又具有副詞的語法功能的謙敬副詞。在語法化的過程中,“伏”的演變從與其他動詞構成連動結構開始,受漢語“V1V2”式連動結構焦點在后的語法規律影響,逐漸由句中核心成分向次要動詞變化,動詞性也慢慢減弱,最后整個結構重新分析為狀中結構完成“伏”的語法化過程。“竊”的演變也與作狀語有很大關系,由于頻繁在句中作狀語,其詞義進一步虛化,也使之作為副詞的句法位置與組合功能得到進一步的鞏固。由此可知,二者語法化為副詞的過程都與在句中作狀語密切相關。
參考文獻:
[1][漢]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
[2][清]劉淇.助字辨略[M].北京:中華書局,1954.
[3]王力.古漢語常用字字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4]馬貝加.漢語動詞語法化[M].北京:中華書局,2014.
[5]王寧.古代漢語[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6]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7]解惠全.語言研究叢論第四輯[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
[8]沈家煊.語法化研究綜觀[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4,(4).
[9]劉堅,曹廣順,吳福祥.論誘發漢語詞匯語法化的若干因素[J].中國語文,1995,(3).
[10]張誼生.論與漢語副詞語法化相關的虛化機制——兼論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分類與范圍[J].中國語文,2000,(1).
(李娟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