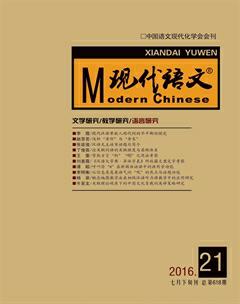從“唐話課本五編”管窺唐通事的漢語教育
摘 要:日本江戶時代的唐通事為中日貿易和商務交流服務,他們學習漢語使用的教科書多以寫本形式存在。本文以“唐話課本五編”的寫本文獻為研究對象,考察唐通事漢語教材的編寫特點和漢語教育的具體實態。
關鍵詞:唐通事 漢語教育 唐話課本
一、引言
日本江戶時代實行鎖國政策,只允許長崎一地與中國及荷蘭進行貿易。因而在長崎,為中日貿易和商務交流而服務的唐通事應運而生,從1604年馮六被任命為唐通事開始①,直到1867年唐通事制度被廢止,這一制度共存在了263年。唐通事主要從事翻譯和日常管理工作,他們的出現直接推動了當地商務漢語教學的發展。
在江戶和明治時期,不僅是唐通事要學習漢語,其他人也有學習漢語的需求,因此出現了大量專門的漢語教科書和工具書。這些教科書既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漢語教學和漢語的風貌,也給今天的漢語教學提供一定的啟示和借鑒。近年來,國內外對這一時期漢語教科書的整理和研究比較多。教科書整理方面,在日本有六角恒廣的《中國語教本類集成》(不二出版,1991年);在中國,張美蘭主編的《日本明治時期漢語教科書匯刊》(廣西師大出版社,2011年)收錄50多種漢語教科書;李無未主編的《日本漢語教科書匯刊》(江戶明治編,中華書局,2015年)收錄江戶至明治末期漢語教科書及工具書文獻134種。研究方面,六角恒廣的《近代日本の中國語教育》(1984)、《中國語教育史の研究》(1988)、《中國語教育史論考》(1989)、《中國語教學書誌》(1994)等是較早的專門研究。
在這些教科書中,江戶時代長崎出身的漢語教育家岡島冠山編的漢語教材“唐話五種”(《唐話纂要》《唐譯便覽》《唐語便用》《唐音雅俗語類》《經學字海便覽》)向來為人們所重視,這不僅因為岡島冠山名氣大,更重要的是這套教科書的內容體系性強,包羅萬象,注重口語和實用,確實在早期的漢語教育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國內關于這套教材的相關研究已有不少,如魯寶元、吳麗君編《日本漢語教育史研究——江戶時代唐話五種》(外研社,2009年)一書收錄了多篇論文,對這套教材進行了細致分析;聞廣益《商務漢語教育的早期實踐——談日本江戶時代唐通事教育的一大特點》(《人文叢刊》第七輯,2012年)對“唐話五種”的商務漢語教育特點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張美蘭《從明清海外商務漢語教材的編纂看商務漢語教材的歷史》(《海外華文教育》,2011年第2期)也有相關內容涉及到這套教材。
“唐話五種”作為漢語教材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不過這套教材并非專門為唐通事而編寫,關于這一點也早有定論。岡島冠山做過譯士,也曾在各地教授漢語,卻因為嫌棄唐通事職位不高,沒有專門從事過唐通事②。在《唐話纂要》編纂出版期間,岡島冠山是荻生徂徠組織的譯社的講師,“因此可以說岡島冠山這套教本,并不是專門為唐通事編寫的,而是為江戶時代初期,各界漢語學習者編寫的,當然其中也包括唐通事。從教本的內容和難度看,不是零起點的漢語學習者,而是具有基本漢語水平的人。”③除《唐話纂要》之外的其他四種漢語教材也是如此。
唐通事漢語教育所使用的漢語教材和漢語教學實態究竟是怎樣的呢?關于這一點,學者們通常引用武藤長平著《西南文運史論》中的一段話:
唐通事最初為學習發音用唐音讀《三字經》《大學》《論語》《孟子》《詩經》等,之后開始語言的初步學習,即學習“恭喜、多謝、請坐”等短的二字句,熟悉了“好得緊、不曉得、吃茶去”等三字話之后,進一步學習四字以上的長短話,其教科書是《譯詞長短話》五冊,然后是《譯家必備》四冊、《養兒子》一冊、《三折肱》一冊、《醫家摘要》一冊、《二才子》二冊、《瓊浦佳話》四冊等唐通事編輯的寫本。畢業后以唐本《今古奇觀》《三國志》《水滸傳》《西廂記》等為師進一步學習,自學《福惠全書》《資治新書》《紅樓夢》《金瓶梅》等,有困難之處詢問老師,這就是普通的順序。④
這段話讓我們了解了唐通事漢語學習的基本順序和使用的教材。這段話里說到學習發音之后所使用的教材都是唐通事編輯的寫本,而這些寫本究竟是什么樣子的?如何使用呢?關西大學圖書館長澤文庫藏有一個唐話教材的寫本,這個寫本將《小孩兒》《長短話》《請客人》《小學生》《鬧里鬧》五編綴為一冊,現已由奧村佳代子將其整理出版,并附了影印本。原寫本并沒有題目,奧村佳代子將其命名為“唐話課本五編”,這套寫本也沒有標點句讀或任何拼讀符號。在這五編中,《小孩兒》《鬧里鬧》作為單篇漢語教材曾在別處出現過(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就藏有這兩篇教材),不過將五編綴為一冊的情況卻是前所少有。因此這個寫本不但有珍貴的史料價值,而且讓我們得以窺見唐通事漢語教育的實況。
二、關于教學對象和教育目的
上述武藤長平關于唐通事漢語學習的一段話中,沒有提到“唐話課本五編”中的任何一種。不過同一本書中,關于薩摩藩(鹿兒島)唐通事的唐話學習,卻有這樣的描述:
作為教科書是習讀《二字話》《三字話》《長短話》《小學生》《請客人》《要緊話》《苦惱子》《譯家必備》《瓊浦通》《三才子》《三折肱》《養兒子》《鬧里鬧》等,以《小說精言》《小說奇言》《三國志》《今古奇觀》《唐話試考》等畢業,這是常例。其中《二字話》《三字話》《長短話》《請客人》《苦惱子》等據說是在鹿兒島藩刊行的。⑤
這段話里面提到了《長短話》《小學生》《請客人》《鬧里鬧》等課本,也說到《長短話》《請客人》是在鹿兒島藩刊行。這是否能說明“唐話課本五編”只是在鹿兒島刊行使用呢?好像還不能這么說。因為從課文內容來看,四編中有三編都提到了長崎,如:“再若是風一轉,還下雨,滿長崎都掃光了,家伙都搬到山上去了。”(《長短話》,第32頁)⑥“尊寓在何處?尚未曾奉拜,小寓暫借在肥前(肥前主要指今天的長崎和佐賀)會館中,怎敢勞動臺駕?”(《長短話》,第32頁)“十年受盡燈前苦,一舉成名聲滿崎。”(《小學生》,第44頁)“說話的,為何只管講賊人的話。因為要講的崎野人們放火的這一段話文,先說這話做個入港。當初長崎繁華的時節,人家守著本分。”(《鬧里鬧》,第45頁)因此,恐怕這些教材主要還是為長崎的唐通事編寫的。
那么,這些教材的具體教學對象都是些什么人呢?讓我們來一一進行分析。《小孩兒》一篇主要是講學堂的規矩,用的全是先生訓誡學生的口吻,里面列舉了小孩子種種不學好、胡鬧的情景,苦口婆心地說明為什么要好好學習,并提出了明確的紀律要求,而且列了獎罰標準。從內容看應該是開學第一課,它的開篇這樣說道:
我和你說,你們大大小小到我這里來讀書,先不先有了三件不是的事情,等我分說一番。把你知道。你們須要牢牢地記在肚里,不要忘記。原來人家幼年間到學堂讀書,不是學個不正經,要是學好的意思了。難道做爹娘的叫你特特送來學個不長俊不成?我這里就是學堂,一個禮貌之地了,不是花哄的所在了。你既然曉得我這里是學堂,因該正經些,不該亂七八造,只管放肆。”(《小孩兒》第20頁)
從“大大小小”“我這里就是學堂”來看,這個地方應該是專門教授漢語的學堂,而且學生人數應該不只一個,年齡也不一樣,從后面列舉的學生們種種淘氣、調皮搗蛋的情形來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另外,文里也提到:“還有大漢子把曲本《西廂》這等的閑書帶過來,放在身邊假做讀書,低低兒唱曲子,把一個學堂當作戲臺。”(《小孩兒》,第22頁)“我聽你們的說話竟不分貴賤,蠻七蠻八,粗糙得緊。大的對小的講也不是了,小的對大的講也不是了。”(《小孩兒》,第23頁)這里的“大漢子”“大的對小的”“小的對大的”都說明學生年齡有大有小,而且可能有的年齡差距還不小。
老師教授漢語是從零起點開始還是教已經有漢語基礎的學生?從《小孩兒》中老師的訓誡來看,應該是從零起點教起的:
你既做了我的學生,要曉得我的恩。我說的恩在那里呢?一個蒙蒙朧朧一字不識的小孩兒,千辛萬苦指點你,方才字也識得出,書也念得下,后來肚里大通,做了職事,一年收多少俸祿,又不少吃,又不少穿,快快活活過日子。究起這個根本來,虧我好幾年用心教導你……(《小孩兒》第27頁)
上面這段話表明先生可能是從發蒙就開始教起,而且一教“好幾年”。當然,老師說上面這段話固然是希望學生知道自己的恩情。不過,對老師來說,更希望學生長進、有出息,他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報恩。
只有一件事情,依我的說話。那個就在我身上算得大大報恩了。一來守規矩,做人要正經;二來發狠肯讀,當心學話。你若做人忠厚,不學不長俊,肚里太通,唐話也會講,明日出頭的時節,不但你一個人體面,連我的名聲也惹得大起來,這個就是報我的恩了。(《小孩兒》第28頁)
“唐話課本五編”的第二部分是《長短話》。岡島冠山《唐話纂要》中有“長短話”,《唐語便用》中有“長短話”,《唐音雅俗語類》中也有“長短雅語”部分,但這些內容都與“唐話課本五編”中的“長短話”不同,可見“長短話”只是一種體例。在岡島冠山的時代,為區別于“二字話”“三字話”“四字話”等整齊的編排,將長短不齊的對話命名為“長短話”,以后就沿用此種體例。
《長短話》的教學對象都是誰呢?課文里有這樣的對話:“老兄到唐館里去值日么?”“不敢,年紀還幼少,不曾去值日。”(《長短話》,第31頁)又有“我們讀書要緊,這些戲文、閑花,都不在心頭。”(《長短話》第33頁)從這些內容推斷,《長短話》的教學對象也許是15歲以下的唐通事子弟。因為大約從15歲開始,這些子弟們就要去唐館中做見習通事,又說“不曾去值日”,所以大約是小于15歲的學生。
在長崎進行貿易的中國人一般都集中居住在稱為“唐人屋敷”的地方,因此,去拜訪當地居住的中國人、進行日常的應酬交際也是唐通事的職責之一。《請客人》的內容就是主人與客人之間勸酒的情形以及就飲酒與喝茶的話題發表一些對世事的看法和議論。從開頭的寒暄來看,似乎是成年人之間的對話:
“尊翁大人多多納福。”
“多謝。家嚴都平安。”
“老翁先生健得很。尊夫人一向都好么?”
“多謝。賤門都好。”
“令郎讀書用工,聰明得很。”
“小兒笨得很,只要懶惰,不能進學。”
“令愛及笄了?”
“小女年長了。”
“好好,兩位都伶俐。”(《請客人》第36頁)
《小學生》與《小孩兒》性質有些類似,也是勸學的內容,甚至許多句子都比較類似,如“原來人家年紀小小的時候,到學堂里去,讀書寫字都要學好的意思。難道做父母的特特送來學個不長俊不成?若是學會了的時候,父母的體面不消說,連我先生的也多少光輝了。都說,某人是某先生的學生,先生教導的好,所以他也學得好,肚里大通,唐話也會。人家稱贊他,便說先生的好。”(《小學生》,第41頁)另外,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小孩兒》有“麻雀是含環報恩,烏鴉是反哺報恩”這樣的話,而關西大學圖書館的《小孩兒》中沒有這句話,但這句話卻出現在關西大學圖書館的《小學生》里,由此是否可以推測《小孩兒》和《小學生》的作者是同一個人呢?《小學生》是先生與學生的對話體,而且從內容和說話語氣、口吻來看,里面的學生比《小孩兒》成熟許多,所以《小學生》是比《小孩兒》更高階段的教材。
《鬧里鬧》由三個話本故事組成,這也是較高階段的教材。
關于教育的目的,對于使用這些課本的人來說,他們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成為唐通事。從歷史上看,由于唐通事的職務一般是世襲的,所以通事家的子弟成為唐通事的可能性最大。潁川君平的《譯司統譜》(1897)、宮田安的《唐通事家系考》(1979)考證了唐通事的家族情況,基本上都是家族傳承。教材的內容也反映了教學目的,如:“晚生們生在通事家,不學書本,不講唐話,那里做得職事,衣飯從那里來?怎能夠養父母?”(《小學生》第42頁)“通事家的兒子,講話、讀書、寫字、學做詩文,第一本等,不得不學。你學成了,做了職事,唐話也會講,肚里也明白,意識運氣轉頭,做了大通事。那時候,吃著好,穿著好,豐衣足食,養著父母。”(《小學生》第42頁)
三、關于漢語教學情況
關于教學的組織者和實施者,也就是老師究竟是什么樣的人,課文里也透露出一些信息。
“我不是生在唐山的。”(《小孩兒》第26頁)
“我說的唐話,雖不如唐人口氣,不過杜謾撰而已,但是不是講假話一樣不三不四的,算作一個唐話,可以做得準了。”(《小孩兒》第25頁)
“我老自又沒有才德,滿口放屁,此身之外,沒有什么想頭。可惜我鄭先生的唐話,一世埋沒了,沒人提起。目今做先生教授學生的唐話,都是鄭先生的偷來教導他,所以口氣教法天差地遠。”(《小學生》第43頁)
“我的唐話雖不如唐人的口氣,鄭先生的教法,學得飽在肚里,你若依我的教法學得好了,就是鄭先生的門生了。”(《小學生》第43頁)
從上面的內容可以基本斷定,進行漢語教學的是生長在日本的中國人,有可能就是唐通事的后代。
關于學習方法,從課文透露的信息來看,仍然以老師教授、學生背誦為主。
我辛辛苦苦教導你十來遍,看見你略覺記得,又換個別人來讀,叫你依舊到自己的坐頭上去讀。(《小孩兒》第21頁)
這個可能是在練習發音的階段,一遍遍糾音,然后再自己練習。
今日學過的書本,回到家里讀了幾十遍。背在肚里,明日在我面前背得出來。這樣的時節,學了唐話才可以用得著。(《小學生》第41頁)
這說明學過的內容不但要回去復習,還要背誦。
四、對漢語語言特點及規律的認識
你若依我的教法,平上去入的四聲、開口呼、撮口呼、唇音、舌音、齒音、喉音、清音、濁音、半清、半濁,這等的字音分得明白后,期間打起唐話來,憑你對什么人講也通得的。蘇州、寧波、杭州、揚州、云南、浙江、湖州,這等的外江人不消說,連那福建人、漳州人,講也是相通的。他們都曉得外江話,況且我教導你的是官話了。官話是通天下中華十三省都通的。(《小孩兒》第25、26頁)
從這段話可以知道,當時教授的是南京官話,唐通事對漢語音韻學術語是非常了解的。
唐通事將商業倫理和道德品質的教育也融入教學中。《請客人》里有關于飲酒、喝茶的情景對話。可是在這些對話中,都對其中的奢侈享受持一種貶斥的態度。
關于《鬧里鬧》,六角恒廣《日本中國語教學書志》中有較為詳細的介紹,認為《鬧里鬧》由三話構成:第一話勸誡節約用錢,如果亂花錢,會貧窮、借錢,甚至會為了錢去殺人放火,導致玷污祖先的名聲;第二話講述社會上各種各樣的盜賊,有個潮州人到蘇州游覽,在浴池洗澡,結果被搓背的一番甜言蜜語哄騙,把柜子的鑰匙調換了,結果衣服錢物都被偷走了;第三話說的是長崎半夜發生的一場火災,人們四處逃竄,街上一片混亂,而一個寡婦卻背著生病的婆婆、帶著三個孩子逃過了火災,為此得到官府對此孝行的獎賞。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的版本正是按照上面的順序編排,而“唐話課本五編”中,《鬧里鬧》的先后順序是:火災故事在前面,其次是節約用錢,最后是盜賊騙子的故事。從內容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版本的順序是對的。編輯這幾個故事的目的,課本說得很清楚:一是學習俗語,二是學習道德,學會孝順父母自然有好報。
今日在下做這一本俗語,因為要說孝婦這一段話文,先說火燒的事情做個入港,但凡這里來學話,不但留心學得這一本俗語,還要把這個孝婦做個樣子,孝順父母。一則話也學會了,二則天地保佑自然出頭了。(《鬧里鬧》第58頁)
五、關于商務漢語教學以及語言的交際功能
語言是用來交際的,唐通事由于職業的特殊性,對口語的交際功能更是十分重視。“唐話課本五編”雖是比較簡單的漢語教材,但是在言語的交際功能方面仍體現了循序漸進的特點。例如《長短話》是各種情景會話的集合;《請客人》主要是宴請場合的對話,但其中包含了成段表達;《鬧里鬧》由三篇短文或者三個小故事構成;《小學生》是以學生與先生的對話呈現。在唐通事學習漢語的階段,這也是日常交際中重要的一環。這從側面提醒我們:編寫教材時,從實用的角度出發,要注意交際對象的身份。課文中有下面一段對話:
“令尊、令堂都好么?”
“多謝問候。家父、家母都是康健。”
“令兄、令弟、令子、令妹,有幾位?”
“家兄、家弟、家姊、家妹,有幾個人。”
“你今年多少歲?”
“賤庚十五歲。先生貴庚幾歲?”
“癡長六十歲。”(《小學生》第41頁)
在上面這段對話中,對話雙方因各自身份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敬稱或謙稱,語體的特點體現得很明顯,體現了言語的交際功能和特性。此外,不同的交際場合應使用的語言也都在教材的編排中展現出來,如見面寒暄、問人年齡、請客吃飯、相互邀約、托人辦事等。除了敬稱、謙稱之外,還有婉語、套語、正式用語等。注重交際禮儀大概是唐通事漢語教學的一大特點。不過,在這本教材中,許多更復雜的交際對話似乎沒有出現在課文中,如商務洽談、求人借貸等。
“唐話五種”中的“二字話”“三字話”“四字話”以及“長短話”包含了很多商務交流的內容。那么“唐話課本五編”作為培養唐通事的教材,是否也注重商務內容和交際功能呢?“唐話課本五編”中的《長短話》都是兩個人的對話,從日常見面的寒暄語談到喝茶、喝酒、賞花等話題。當然這里面包含了涉及唐船貿易的商務內容,從中可以窺見教學的針對性。例如下面這樣的對話:
“如今館內有幾個船么?”
“今年的船只有十八個船。”
“今年為什么船來得少呢?”
“只因舊年多擔閣(耽擱——引注)了幾個月,回唐太遲了,算帳不得明白,捱到今年方才了結,后來打點多少本錢,買東買西。如今正在那里打帳發船,只怕年里頭拾(十——引注)來個船是有得到。”
“原來唐船在東洋所買的回唐貨是不知什么東西呢?”
“正是這個有定規。譬如紅銅包頭、鋼器、漆器、流金、墨、狐貍皮、錨金、薰金、羊皮、金、獐腦、瓷器、真珠不過這幾件東西。”(《長短話》第31頁)
這段對話不但交代了一年中進出港的船只數量以及變化的原因,而且羅列了從日本回中國的船只帶回的貨物種類。
還有下面的對話:
“寶舟是哪里開來?”
“晚生寧波開來。”
“老兄來過幾回?”
“晚生這遭第三回。”
“唐山有什么新聞?請教請教。”
“沒有什么新聞,各處都太平。”
“寶舟幾月里放洋?”
“晚生三月初一放洋,一到初七,看到五島山,初九日進港。”
“尊姓呢?”
“豈敢。姓陳,就是耳東陳。”
“大號呢?”
“豈敢。賤號永昌。”
“貴府是哪里?”
“豈敢。晚生在蘇州。”
“貴庚幾歲?”
“豈敢。賤庚三十一歲。”
“有幾位令郎?”
“豈敢。有兩個小兒。”
“今年唐山年成怎么樣?好不好?”
“好阿,今年算得豐年。米價也比往年賤些。”
“一擔米多少價錢?”
“每擔米不過九錢銀子光景。”(《長短話》第35頁)
由于唐通事還擔負著收集情報的職責,因此上面這一長段情景對話,不僅有寒暄,還順便詢問了中國發生的新聞和物價情況。
六、結語
奧村佳代子認為,“本資料所收的唐話課本5種,是在唐話最初級課本《二字話》《三字話》等結束之后的階段使用的,通過唐話可以說反映了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唐通事的想法和生活。”⑦“不是作為起步的唐話教科書……不是初級水平,我認為是針對一名成為唐通事之前仍有學習必要的年輕人。”⑧這些推論當然有一定的道理。并且我們可以進一步斷定,“唐話課本五編”應該是唐通事的家學課本,課本編寫以口語、實用為主,遵循由易到難、由簡入繁的原則,而且將商業倫理教育融入其中;但唐通事的漢語教育并不是家庭性質的教育⑨,而帶有學校教育的性質。作為唐通事來說,由于其本身的社會地位和受教育的局限性,他們不可能對漢語教育有更多的自覺意識和深入研究,像岡島冠山那樣的漢語教育大家在唐通事中是很少見的。
注釋:
①據《長崎志》(正編):“長慶九年(1604),叫馮六之唐人習記日本詞,故始委任唐通事職,其后增叫馬田昌人者,成為二人。林長右衛門繼承馮六的家業。”六角恒廣:《日本中國語教育史研究》(王順洪譯),第126頁,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年。
②據《唐話纂要》“序”:“然弗補通事之職,而游乎江湖者,無乃憎嫌此職之不貴耶?”那么岡島冠山不曾做過唐通事。魯寶元、吳麗君編《日本漢語教育史研究——江戶時代唐話五種》第194頁,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年。
③魯寶元、吳麗君編:《日本漢語教育史研究——江戶時代唐話五種》第50頁,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年。
④轉引自關西大學圖書館長澤文庫所藏、奧村佳代子編著:《唐話課本五編》“前言”第6頁,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年。
⑤轉引自關西大學圖書館長澤文庫所藏、奧村佳代子編著:《唐話課本五編》“前言”第7頁,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年。
⑥“唐話課本五編”正文內容均出自關西大學圖書館長澤文庫所藏、奧村佳代子編著:《唐話課本五編》(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年),以下引用均只在文后標注篇目和頁碼,不再一一注出。
⑦關西大學圖書館長澤文庫所藏、奧村佳代子編著:《唐話課本五編》“解題”第18頁,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年。
⑧關西大學圖書館長澤文庫所藏、奧村佳代子編著《唐話課本五編》“前言”第7頁,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年。
⑨朱勇《唐通事與漢語言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認為唐通事教育“帶有一種家庭教育的性質”,魯寶元、吳麗君編:《日本漢語教育史研究——江戶時代唐話五種》第50頁,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年。
(蔣春紅 北京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