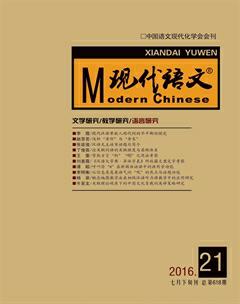多元文化背景的漢語中級班口語教學策略
摘 要: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漢語中級班留學生存在發音頑疾未徹底糾正、語言偏誤高度個性化、內部文化沖突較為明顯等問題。本研究以江蘇大學漢語中級班口語教學為樣本,提出采用“群體集中”與“群體分離”相結合的教學原則,并介紹了五項行之有效的具體策略,以期為有相似組班情況的其他高校提供借鑒,為漢語口語教學模式的建立提供部分基礎性材料。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漢語初級班、高級班口語教學亦可施用相關有效策略。
關鍵詞:多元文化背景 中級班 漢語 口語教學
一
漢語中級班的口語教學往往是一個瓶頸期,初級班的學生處在漢語語言文化知識的吸收期,進步非常明顯;高級班學生在語言技能方面精益求精,漢語日益流暢和地道。而中級班學生在語言方面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詞匯量,但遣詞造句往往支離破碎,固有的發音頑疾仍未徹底糾正,新出現的語言偏誤五花八門;在文化方面,非單一國別成員的中級班在班級融合初期可能出現各種文化的碰撞,容易產生文化相近的小團體抱團現象,導致文化沖突明顯,群體融合度不高。這些都需要教師思考并采用有效的策略組織教學。已有的漢語口語教學策略研究主要關注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背景的留學生群體,如針對泰國、韓國、印度尼西亞等國學生的口語教學策略(蘇香瑞,2013;蘇彩霞,2009;葉玲玲,2011);或對特定的兩大群體進行比較研究,如針對韓國學生與歐美學生的漢語口語教學策略對比研究(那劍,2007)。本研究主要關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留學生漢語中級班在口語教學過程中面臨的一些特殊現象,對應提出有效的教學策略。筆者希望此研究能給對外漢語口語教學提供一定的啟示,同時為漢語口語教學模式的建立提供一定的基礎性材料,并促使有效策略培訓的產生。相應地,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漢語初級班、高級班亦可采用相關有效策略。
江蘇大學的對外漢語教學起步較晚,生源遠不如北京、上海的高校充足,目前尚不可能開設所謂的日韓班、非洲班、歐美班,只能組成多元文化背景的班級。一方面,這樣的情況是國內許多對外漢語教學起步晚的高校所共同面臨的情況;另一方面,多元文化背景班級的組建并非沒有好處,由于學生的英語水平并不整齊,有時為了交流的順利,反而有可能增加使用漢語的機會。如果教師能揚長避短,尋求文化的平衡點,完全可以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
本研究選取江蘇大學海外教育學院2013級留學生漢語中級班為樣本。該中級班留學生共19人,分別來自四大洲的12個國家,其中德國學生1名、波蘭學生2名、西班牙學生1名、加拿大學生1名、日本學生1名、韓國學生6名、印度尼西亞學生1名、泰國學生1名、喀麥隆學生1名、吉布提學生2名、剛果(金)學生1名、斐濟學生1名,每個人均在自己的國家學習過半年到一年漢語。2013年9月起,在江蘇大學漢語中級班學習了一年,所使用的教材是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漢語口語速成·基礎篇》和《漢語口語速成·提高篇》,本研究主要采用課堂觀察、課后資料收集、學生訪談的方法,鑒于第二語言教學的共通性,同時邀請了江蘇大學4名外籍語言教師參與課堂并進行集中學術研討,其中愛爾蘭籍外教1名、美國籍外教1名、澳大利亞籍外教1名、奧地利籍外教1名。
二
筆者認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漢語中級口語教學宜堅持“群體集中”與“群體分離”相結合的原則。具體而言,教師可采用以下五種策略:
(一)研究學生的朗讀錄音,組織產生相似偏誤的群體開展語音復練
美國語言學家塞克林于1969年提出“中介語”這一概念。中介語是在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學習者通過一定的學習策略,在目的語輸入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既不同于其第一語言也不同于目的語、隨著學習的進展向目的語逐漸過渡的動態語言系統。中介語的偏誤具有反復性、頑固性,特別表現在語音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母語的負遷移,即學習者用第一語言的語音規律替代目的語的語音規律;另一方面是由于學習者可能意識到有些偏誤并不影響交際,尤其是課后在與同一國學習者交流的過程中,彼此對共同存在的偏誤意識不到,導致這些偏誤僵化,成為頑疾。該中級班的學生經過此前在各自國家的漢語學習,對漢語已有相當程度的掌握,但某些發音頑疾未得到糾正。雖然每個學生的發音偏誤各有特點,但顯然存在一定的群體特征,例如:歐美留學生的第二聲和第四聲發音存在困難,“留學生”“太極拳”“宿舍”等詞句的聲調時常出現偏誤;非洲留學生的ü發音與u相混淆,x與sh相混淆,zh、ch、sh有濁化傾向;韓國學生的f發音用p代替,r發音用l代替等等。正音貫穿于對外漢語教學的全過程,針對群體性問題,筆者認為宜采用“群體集中”的原則開展語音分組復練:首先,教師在課后布置統一的朗讀作業,學生將朗讀錄音發送給教師,教師通過聽錄音,記錄個體發音問題,同時歸納群體發音問題,將有相似偏誤的學生分成小組①。第二,開展分組復練。教師分小組進行指導,將每個小組的共同問題分別列出,引起各組學生的高度重視,促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語音偏誤。第三,教師通過范讀講解發音要領,讓學生觀察發音方法,重點讓學生認識到正確發音與錯誤發音之間的區別,使學生首先在聽力上能夠辨音;教師通過領讀引導學生模仿正確的發音,從而不斷接近正確的發音;學生逐個發音,小組其他學生聽辨,互相指出問題,教師逐一點評。該策略既能增強學生的辨音能力,也能使學生進一步關注自己的發音偏誤,有針對性地去改善,在此過程中,教師亦可以就學生的個別問題稍加提點。經過半年的訓練,該中級班學生發音問題有了明顯改善。
(二)布置“個人口頭報告”,提高學生個體語言技能
漢語中級班學生已掌握了相當一部分詞匯,熟悉了漢語的基本語法。此時,該中級班留學生口語表達的欲望增強,也樂于運用新詞造句,但普遍存在用詞不當、造句支離破碎的問題,在語音、詞匯、語法方面呈現出的個體差異也愈發明顯:泰國留學生的j、q、x發音偏誤經常出現;斐濟留學生的第一聲和第四聲混淆;韓國留學生常常使用“我想見面他”“這個問題我有關心”等錯誤的表達;剛果(金)留學生的“ang”和“ong”發音混淆嚴重;波蘭留學生對“不”和“沒”的區分時有失誤;德國留學生在成段表達時仍然會犯“我接觸到了更多的漢語知識在中國”這樣的錯誤。隨著詞匯量的擴大,每個學生在進行表達時呈現出的問題愈發五花八門。
針對這種情況教師應采用“群體分離”原則,布置學生準備“個人口頭報告”,即給定一個主題,例如“我的祖國”“漢語難不難”“我的中國夢”等,每節口語課的前五分鐘安排學生輪流演講②。我們可以借用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理論來闡釋該教學策略的必要性:在學習第二語言時,學生受第一語言的影響,會套用第一語言的規則造成偏誤,接觸到更多的第二語言之后,學生會逐漸對第一語言的參數值進行調整或者重建。準備“個人口頭報告”的過程實際上是學生全面調動漢語語言文化知識的階段,除了使用駕輕就熟的已有知識,必然也要采用新學習的、尚未自如運用的詞句,甚至為了完善和豐富口頭報告的內容而自學新的知識,此時,偏誤會個性化地、最大程度地顯現出來。教師聽取“個人口頭報告”時,如能做好相關的記錄,就能及時地、有針對性地促使演講學生發現自己的問題,演講學生改進的過程正是進一步對第一語言的參數值進行調整或者重建的過程,從而不斷改善自己的“中介語”并向目的語靠近。其他學生在聽取演講的時候,教師應鼓勵他們廣泛參與,這樣不僅能提高聽者的辨識力,主動發現演講者的問題,防止自己出現類似的錯誤,事實上這也是對已有知識的一種積極的鞏固方式。借用克拉申的“i+1”理論(Krashen,1982)來闡釋,相比教師集中授課令學生輸入新的語言知識,學生聽取他人“個人口頭報告”時所吸收的新知識往往更加生動、有趣:有一定的上下文,融于整個報告的情境中,即不過難也不過易,稍稍高于聽者目前的語言水平,屬于“跳一跳夠得著”的內容。如果學生在自己的演講中也嘗試使用了這部分語言知識,經過教師的檢測與糾正,能取得更好的循環復習的效果。一年中,該中級班持續采用該教學策略,事實證明,學生的表達能力有了較大提高,遣詞造句的完整性、規范性和演講的邏輯性都有了較大程度的改善,并且個體偏誤得到了學生的高度重視和及時糾正。
(三)合理搭配學生的語伴并定期交換,培養學生語言辨別和對比能力
情景法認為,口語是語言的基礎,準確的結構是說話的核心,因此強調在自然情景中教授口語。中級班的學生已經掌握了一定量的詞匯,培養他們在一定的情景中流利、正確地表達十分重要。對話練習是培養口語能力的重要途徑,漢語課本上的對話是一個范本,學生通過朗讀、理解、練習來獲取正確的語言知識。接下來,為了檢測學生是否真正掌握了這些語言知識,需要讓他們根據實際情況去改編書本的對話,但是改編不是漫無邊際的改編,教師需要給定核心知識,在此不再贅述。在改編對話的過程中,學生會有意無意地使用新知識,也必然要使用舊知識,改編就成為語言知識的整合過程和創造過程。對話練習的時候,教師不可能持續觀察所有的學生,因此語伴就顯得非常重要,其兼具了對話組織、語言檢測的作用,當對話的一方進行表達時,另一方則要給出恰當的語言反應,才能確保一段對話順暢進行,因此教師應當精心觀察、合理搭配學生的對話語伴。
例如在該中級班,第一,宜盡量將不同國家的學生搭配成組,因為他們的偏誤特點各不相同,一旦組織對話,個體就會最大程度地“暴露”這些偏誤,非本國語伴往往能第一時間覺察并互相指出這種偏誤;第二,一旦語伴發現了對方的偏誤,潛意識中就會進行比較分析進而與對方進行研討,事實上對雙方都是一個語言知識的循環練習過程,能有效鞏固正確的語言知識;第三,水平差距過大的學生不宜成為語伴,他們容易在話輪組織上出現“長短腿”現象。水平高的一方使用較多的語言知識,水平低的一方在理解上難免出現障礙,因此無法給出恰當的反應,水平高的一方也沒有足夠的時間解釋,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內,雙方的學習效率和學習動機都有可能減弱;第四,經過一段時間后,教師應調整學生的語伴。當一組語伴互相適應后,對彼此偏誤的敏感度會逐漸降低,有時甚至因為已經不影響理解而覺得不必要互相糾正,交換語伴之后,新的磨合重新開始,學生也有更多的機會去覺察語言偏誤,互相糾錯的行為就能持續進行;第五,學生的對話組織不可避免會附加文化色彩,例如在談到“夜生活”“理想的工作”等話題的時候,不同國家的學生會傳達出多元的思維,定期交換語伴,學生能獲取多元的社會文化知識,互相理解并提升班級的整體融合度。
(四)組織微型“聯合國”開展中國文化討論,增加班級融合度
語言和文化是相依的整體,對外漢語課堂教學中,文化因素的體現無處不在,中級班的文化教學也在逐漸深入。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班級,學生的文化背景和學習特點各不相同,較之于文化相近的歐美班、日韓班、非洲班等等,學生還要多一個彼此適應各種文化碰撞的階段。該中級班中的歐美留學生個性獨立,課堂上比較活躍,質疑思維較強,熱衷于研討式學習,新語言知識的接受量不大,在復述課文之類的課堂任務上參與積極性不高,但課后的作業較有創造力,他們特別強調學習動機,喜歡賞識和鼓勵性教育;亞洲留學生性格較為沉穩內斂,課堂上不太活躍,習慣于順從教師,初期不習慣在研討中各抒己見,新語言知識的接受量大,復述型練習駕輕就熟,課后作業中規中矩,創造性不是特別強,學習最為刻苦;非洲和斐濟留學生性格開朗、熱情,課堂上比較活躍,對課堂參與度高,表現欲強,喜愛研討,積極發言,新語言知識接受度較高,但對待課后作業積極性不高,完成質量一般。當然每個學生都有各自不同的特點,不斷改變著自己,這樣的分類僅僅是為了說明,由于文化的差異,班級在初期往往會形成相近文化的抱團現象,每一個文化相近的小群體都存在思維定勢和對異域文化的成見,造成班級融合度不高。因此,教師必須認真思考加強班級融合度的策略,引導學生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努力尋求平衡點,汲取異域文化的長處。同時,浸潤在中國文化的大環境中,一定要加強對中國文化的認可、理解和學習。
針對這種情況,教師宜采用“群體集中”原則,將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合理搭配成組,開展中國文化討論,這樣既能共同操練漢語語言知識,也能加強他們彼此的文化溝通和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能力。在該中級班,教師一般會將1名歐洲學生、1名非洲學生和1~2名亞洲學生搭配成一個微型“聯合國”討論組,給定討論主題,要求學生寫好研討綱要,制作PPT,過程中可根據水平的提高加入各種藝術形式,每月一次集中展示。如“我眼中的文化差異”一題,教師要求各討論組分別舉出所遇到的中外文化差異的例子,分析其背后的原因,研討在中國生活該如何應對這樣的差異;又如“我們如何在中國旅行”,要求各組選定一處旅游目的地,1名學生做旅行社接待,講解旅游路線,說明費用等問題,其他組員擔任地接導游,各自承擔景點解說任務;等等。據觀察,歐美留學生往往在小組中占據“領袖權”,樂于制定研討思路,亞非學生則處于配合狀態,亞洲留學生在研討綱要的撰寫方面發揮充分優勢,不斷完善文字準備,非洲留學生在集體展示時聲情并茂,演講最富有感染力,形式也最豐富。經過一段時間的融合,上述狀況有所改變,學生開始意識到自己的長處和短處,亞非留學生的主動性變強,樂于擔任研討領袖,歐美學生更加重視語言知識的細節,對他人的配合度提高,各小組之間明顯互相吸取了研討的亮點。在最后三次的展示中,原先存在的歐美、亞洲、非洲的群體特點模糊,所有小組的關注點完全集中在對中國文化的學習上,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能力和解說能力穩步提高。
(五)采取外籍教師聽課法,以多元視角改進漢語口語教學
對外漢語教學是第二語言教學的分支學科,無論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還是英語等語種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都存在許多異曲同工之處。隨著高校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對外漢語教師與其他國家的語言教師開展互相聽課、集中研討成為可能,對彼此教學大有裨益。由于文化背景和教育方式的不同,外籍語言教師分別以“群體集中”和“群體分離”的視角,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觀察有多元文化背景的班級整體狀況和內部小群體狀況,往往能提出多元化的意見,為漢語教師的教學策略提供有益補充。
本研究邀請江蘇大學4名外籍語言教師參與課堂并進行學術研討,他們持續觀察課堂,偶爾參與學生課后討論,每月定期與漢語教師進行研討,這樣的研究形式直觀、鮮活、生動,有利于理論與實踐的有效結合。在對比中國學生和外國留學生的學習特點后,結合自身教學實踐,外籍語言教師與該中級班漢語教師商討了教學中存在的問題與應對策略。研討結果除了上文所述的四點教學策略外,還包括:第一,教師宜增強賞識教育的氛圍。歐美留學生習慣于被鼓勵,持續增強賞識教育的氛圍,能有效消除他們學習漢語的挫折感③,激發他們課后學習漢語的動力,彌補他們課堂知識接受量不夠充分的缺陷;亞非留學生同樣得益于被鼓勵,尤其是韓國留學生,原先習慣于服從教師,但經過觀察,得到肯定和鼓勵之后,他們明顯獲得了更加輕松愉悅的心態,課堂活躍度增強。第二,教師宜鼓勵中外學生的交流與共融。留學生在課堂上獲得的語言文化知識必須在真實的生活環境中運用,才能得到有效鞏固。因此,留學生與中國學生結對,共同組織和參加中國文化學習活動,有助于學以致用。江蘇大學設有“牽手走世界”協會,中國志愿者經常在教師的指導下,與留學生共同參與書法、繪畫、太極、京劇等文化學習活動,既幫助留學生在真實的環境中聽漢語、說漢語,更讓留學生在交往中感受中國人待人接物的方式,體驗中國社會的風俗習慣,更好地感知中國文化。第三,教師應增加新媒體技術在教學中的運用,傳統的課本講練方式有可能使學生感覺疲倦和枯燥,因此圖文并茂、生動直觀的新媒體技術的運用對教學來說尤為重要。例如,教師在課堂上根據需要采用播放PPT、視頻、電影等形式;課后利用微信、QQ等與學生保持溝通,建立一個班級微信群,鼓勵學生在群內用中文自由討論,可以發布通知、討論作業、策劃活動等等。教師可以從學生的對話中發現他們的語言偏誤,了解他們的思維方式,進而改進教學方法;教師應為學生提供各種優質的漢語學習網站和軟件,增強學生的自學能力;此外,教師可鼓勵學生在完成一個階段的學習后,自行拍攝學習展示短片、微電影等,最大程度地激發學生的創造力,寓教于樂。第四,教師宜重視師生溝通。所謂教學相長,教師定期傾聽學生的心聲,允許學生指出自己的不足,既能及時改進教學,更能增強師生之間的情感交流,對于幫助留學生融入中國文化的大氛圍,營造班級和諧親密的小氛圍都極有好處。與各國語言教師進行教學研討,有利于漢語教師打破慣性思維,獲得更加廣博的視角與多元化的思維,以創新的姿態不斷改善適合多元文化背景的漢語中級班的口語教學策略。上述所有教學策略在實際應用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見,不同國家的語言教師之間的溝通交流在高校是可行的,更是十分必要的,能有效促進各高校漢語語言教學的進步,探索建立符合各校實際情況的對外漢語教學模式。
三
本研究是對漢語口語教學策略研究的新嘗試。但由于研究條件有限,樣本量較小,更有代表性的結果有待以后在更大樣本量的基礎上得出。另外,本研究只考察了中級班學生,同類初、高級班的教學策略同樣值得研究。期待此后更深入、更全面的考察研究,為漢語口語教學模式的建立提供更多基礎性材料。
注釋:
①這里的分組并不絕對。一般來說,該班級的歐美、亞洲、非洲學生的問題相對集中,但有時也會出現交叉,教師應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分組。
②教師給定的主題不能是任意的,應與所學內容相關,易于學生利用已有的語言文化知識進行準備。
③據觀察,對于歐美留學生來說,雖然已經進入中級漢語學習階段,但由于漢語不屬于印歐語系,他們學習起來仍然不輕松。亞洲學生由于文化相近,學習速度和知識接受量高于歐美學生,歐美學生往往有挫折感。
參考文獻:
[1]劉珣.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M].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0:135-137.
[2]《學漢語》編輯部.外國人漢語學習難點全解析[M].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2:18-36
[3]劉慧冬.初級漢語混合班聽力教學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4]Everson,M.E.& KE Chuan-ren.An Inquiry into the Reading Strategies of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J].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1997.
(徐丹 江蘇鎮江 江蘇大學海外教育學院 21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