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行為學(xué):注意力是最稀缺的社交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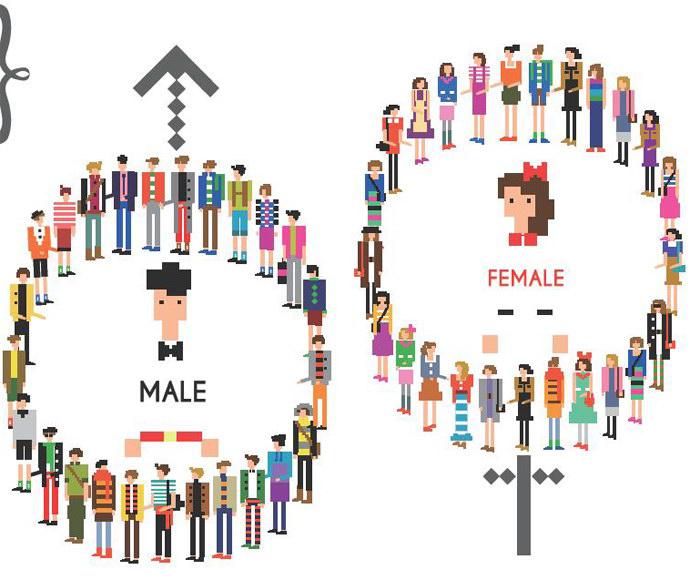

行為學(xué)研究動物(包括人類)乃至值物的行為,它以行為的名義涵蓋—切研究領(lǐng)域(包括群體行為、社會心理、物種、生態(tài)等)。既然如此,當然可以有微信行為學(xué)。
被占用的垃圾時間
我的微信行為觀察,最初印象是微信的便捷性。人口密集地區(qū),手機普及率最高。微信的核心功能是轉(zhuǎn)發(fā)消息,最初,它占用的是使用者的“垃圾時間”——即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從一個環(huán)節(jié)轉(zhuǎn)換到另一個環(huán)節(jié)時,在轉(zhuǎn)換過程中消耗的時間,通常稱為“等待”。如果沒有微信,如果必須等待下一事件發(fā)生,那么,等待就稱為“無聊”。被無聊占用的,是“垃圾時間”。
在“垃圾時間”,我們的行為模式是“觀望”——這是人類在演化到猴子時代留下來的行為習(xí)慣,有助于生存的習(xí)慣。威爾遜在《社會生物學(xué)》第二章里圖示了七種猴子的五種行為類型各自占用時間的比例,第四類型就是觀望,以環(huán)尾狐猴的觀望時間占比例最高,這種猴子的閑暇與好奇,幾乎占了它時間的50%。
技術(shù)進步,從物質(zhì)生活的維度不斷沖擊我們的社會生活維度和精神生活維度。微信轉(zhuǎn)發(fā)文章時可寫的字數(shù),早已突破了最初的限制。目前,微信轉(zhuǎn)發(fā)的文檔尺寸被限制在30MB以下,每條微信可寫的字數(shù)似乎限制在幾千字以內(nèi)。占用的既然是“垃圾時間”,太長的字數(shù)和文章也很難被持續(xù)轉(zhuǎn)發(fā)。限于帶寬,音頻文件微信傳輸仍受嚴重限制,每段不過數(shù)十秒;視頻文件,限制更大。
注意力是稀缺資源
上述源于猴子環(huán)顧習(xí)慣的微信行為,已迅速演變?yōu)楦鼜?fù)雜的行為。例如,微信使用者的行為模式依年齡而有顯著差異。退休之后的時間,可能太充裕,從而不再被區(qū)分為“寶貴的”和“垃圾的”。對退休的人而言,與其他通信手段相比,微信社會網(wǎng)絡(luò)的典型“友誼圈”(friendship circle),在相當程度上使微信交流成為情感生活的必要部分。
對轉(zhuǎn)型期中國社會而言,對那些家庭結(jié)構(gòu)突然從“鄉(xiāng)土的”改變?yōu)椤皢巫拥摹比硕裕绕淙绱恕R惨虼耍粌H對退休的人,更主要地,對數(shù)以億計的城市農(nóng)民工,微信是情感生活的必要部分。
微信是在博客和微博之后形成的社會交往方式,所以它有大量的文章可以推送。需要探討的是微信行為的激勵。最初,或許沒有商業(yè)目的,微信的交流主旨就是友誼。后來,每一微信使用者同時在幾十乃至幾百微信群之內(nèi),時間成為最稀缺的社交資源,于是,他必須篩選信息。微信使用者篩選信息的方式,類似于斯坦福大學(xué)一位重要的經(jīng)濟史家格雷夫考證的“地中海商幫”規(guī)則,或古代中國的“保甲連坐”制度。
假如我在某一微信群里讀過的信息足夠充分地讓我相信這一微信群不值得我“置頂”或被“打擾”,我可以據(jù)此從若干可選程度的“不關(guān)注”中將這一微信群整體設(shè)置在與我的性情和興趣保持一致的忽略程度上。當然,我可能因此而漏掉相當寶貴的信息。為此,我可能使用一套諸如“同步助手”這樣的應(yīng)用軟件,定期備份全部微信群的全部對話。雖然,這樣備份了之后,我可能依舊沒有機會關(guān)注被備份的大部分信息。
我曾舉例,如我有一塊2T移動硬盤,裝滿了學(xué)術(shù)文獻,我要毀滅一位年輕人的學(xué)術(shù)前途,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誘使他瀏覽這塊移動硬盤的全部信息。我的觀察結(jié)論是,很高的概率,他將放棄任何有效的學(xué)術(shù)努力。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最寶貴的是注意力而不是信息。有鑒于此,注意力是最稀缺的資源,成為微信行為學(xué)最重要的理論基礎(chǔ)。
轉(zhuǎn)發(fā)即人品 微信社會網(wǎng)絡(luò)是典型的“友誼圈”結(jié)構(gòu)——每一個俱樂部(微信群)里至少有三個人認識其他俱樂部里的至少兩個人,諸如此類,許多這樣的俱樂部經(jīng)由它們內(nèi)部的少數(shù)活躍成員與其他俱樂部關(guān)聯(lián)而成更大的一圈,這些大圈子當中少數(shù)的活躍成員再與其他大圈子當中的少數(shù)活躍成員結(jié)識。
在這樣的網(wǎng)絡(luò)里,每一個人轉(zhuǎn)發(fā)文章的行為,同時也是發(fā)送關(guān)于他自身品質(zhì)的信號的行為。
以上所述的兩種“品質(zhì)信號”案例最終形成一套我稱為“廣義身份經(jīng)濟學(xué)”的理解框架。尤其在尚未完全擺脫甚至或更深陷入“身份社會”的經(jīng)濟中,一個人可以改變自己的各種身份,如果他愿意并且有能力支付相應(yīng)代價的話。例如,在中國,由于技術(shù)進步的速度遠遠超過了道德底線上升的速度,人們不僅造假商品而且造假身份,從假文憑到假家庭直到假社會網(wǎng)絡(luò)。
改變身份之后呢?布坎南1965年引入經(jīng)濟分析的“俱樂部理論”,將俱樂部視為最廣義的經(jīng)濟物品——它的—端是純粹私人物品,它的另一端是純粹公共物品。俱樂部是偏好相類似的人的集合,旨在獲取規(guī)模消費的好處,例如校車、游泳池、高爾夫球場。融入身份經(jīng)濟學(xué)和網(wǎng)絡(luò)社會科學(xué)的分析框架之后,俱樂部的經(jīng)濟涵義更接近現(xiàn)實世界了,同鄉(xiāng)會、校友會、夫人和秘書俱樂部等。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數(shù)量眾多的微信使用者在數(shù)量眾多且品質(zhì)各異的微信群之間的流動,傾向于形成品質(zhì)各異且相對穩(wěn)定的許多網(wǎng)絡(luò)俱樂部。
人以什么品質(zhì)分群?“品質(zhì)”或“質(zhì)量”,是經(jīng)濟學(xué)最艱難的概念,至今未有成功的分析基礎(chǔ)。不過,人口學(xué)家早已提供了“品質(zhì)”的經(jīng)驗分類方法,稱之為“人口學(xué)特征”。推而廣之,任一集合A之內(nèi)的元素,只要表現(xiàn)出某一特征X,觀察者總可以用x將A的全部元素分為兩類,其一是有這一特征的,其二是沒有這—特征的。
人們的微信行為傳遞哪些重要信號可讓人們在眾多微信群之間搬家直到出現(xiàn)某一均衡狀態(tài)?對這一問題的解答,依賴于特定社會的特定時期的特定個體。
例如我自己,對粗魯言辭的承受力不高,故而言辭的文明程度是我在微信群之間搬家的重要動機。我的注意力代價,與工作性質(zhì)有關(guān),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信息的學(xué)術(shù)含量。于是,我進入和離開許多微信群的主要理由是學(xué)術(shù)或思想的,與那里的言辭是否足夠典雅無關(guān)。
民主政治被稱為“以手投票”,人們在眾多俱樂部之間的自由流動被稱為“以腳投票”。微信行為比民主政治和俱樂部物品更具有私己性質(zhì)。所以,微信行為學(xué)的原理應(yīng)涉及人類情感的交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