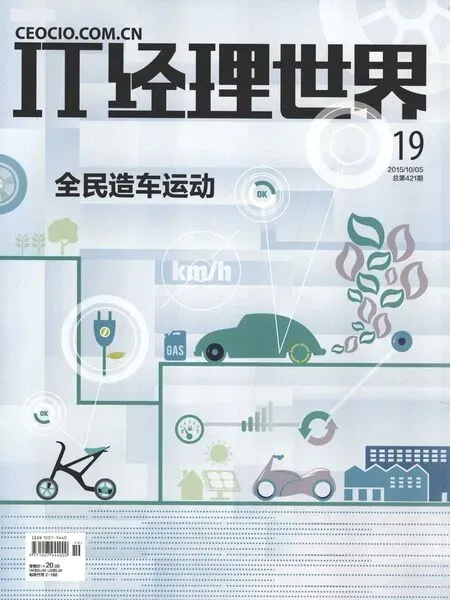消費升級浪潮下的品牌“重啟”
栗建
面對中國中產階級消費能力的猛烈爆發,迷戀數字與表格的營銷人需要走出誤區。
時下討論熱烈的消費升級,并非是從“衣食住行”到“驕奢淫逸”的簡單轉變。無論是“中產階級新物種”,還是“新消費主義”,這些試圖描摹和畫像新消費者及其消費行為的詞匯可能并不恰當和準確。
專家和研究者們正在試圖從以歐美和日本等國家的消費升級作為樣本,來解讀正在發生在中國的消費結構和消費品類的變革。在2015年,中國的人均GDP約合8016美元。從歷史上看,當在人均GDP5000~10000美元時期,美國、德國、日本等7個發達國家的人均居民消費增速明顯高于上一階段,各國消費規模也比上一階段翻了一番。
在此期間,消費規模的擴容,消費結構也發生了實質的改變。非耐用消費品占比繼續下降至40%左右,耐用消費品占比上升至15%左右,醫療保健、交通、通信、休閑與文化、教育等服務類消費占比超過40%,首次超過非耐用消費品成為居民消費的首要組成部分。
中國中產階級消費能力的爆發來的猴急而猛烈。
顯而易見的例子是,跑步和健身正在成為中國消費者的新寵。這兩項需要持續投入卻又無聊耗時的運動成了中產階級區分自我的標簽:有錢、有閑、有內涵。
當下流行的輕奢主義,代言著中產階級“有錢有閑有內涵”的優越感和身份認同。在同一價格區間,“內涵”往往要比價格更能體現專業和品味。內涵意味著登山鞋底的Vibram標志以及食品包裝上的“有機”標簽,也意味TOMS和Warby Parker體現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普世價值。相比之下,香車寶馬和洋酒豪宅顯得老土而低俗。
一方面,它可以緩解高房價和高稅收壓力下中產階級追求奢華卻財力不足的窘迫,另一方面,它又幫助中產階級實現找到屬于自己的身份標簽和價值歸屬——比普通人更有錢,比暴發戶更有品。
如果把眼光放的更遠一些,我們會發現中國的消費升級處在全球消費升級的大背景下。德國轟轟烈烈的工業4.0,美國方興未艾的共享經濟,這些新的經濟模式的出現都是生產和消費的升級。這些新的消費趨勢,隨著互聯網、好萊塢、美劇和小紅書和中國的消費升級融合,也影響著我們要什么買什么。
“量子態”的消費者
消費者越來越難以琢磨,這是讓所有人吐血的事實。
即使是貴為品牌營銷和渠道管理的大咖寶潔也失算了。寶潔CFO喬恩·默勒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消費者理念變化,消費結構調整,但寶潔未能及時應對中國近年來的消費升級趨勢,忽略了中國中產階層消費能力提升的需求。
這不是寶潔一家的問題。大多數品牌都低估了中國中產階級突然爆發的購買力和迅速提升的消費品味。當連靠“懂你”和“為發燒而生”的小米也賣不動了,我們難免陷入恐慌:不是品牌行不行了,而是消費者行不行了。
消費者研究智囊Trendwatching.com大膽總結說:不要再糾結于消費者到底行不行了,因為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行不行。現在的Pokemon Go, 昨天的DrawSomething,消費的喜好就像一陣風,來去匆匆。
捕風的人看似浪漫,其實很累的。搞營銷的腦力和體力都快要被榨干了。馴服消費者的營銷武器——STP(Segmenting細分, Targeting目標, Positioning定位),現在也大靈不靈。
新一代消費者分析工具比如大數據,聽起來很美,但用起來很爛?Netflix的產品創新副總裁Todd Yellin直言不諱地說,大數據不是一座金礦,而是一座垃圾山。在一座碩大的垃圾山里找到金子,好比在Java寫的應用里找bug,誰做誰知道。
消費者是薛定諤的貓,一旦把他們放入消費狀態下去觀測,他們就處于“不可確定”、“非人非己”的量子態。我們把消費者定位成“理性消費”動物,用數據和觀察的手段去分析,可能會遭遇經濟學中“利己主義經濟人”的假定同樣的尷尬。對于數字和表格的迷戀和依賴,是經濟學家和營銷經理們共同的誤區。
后人口學消費主義
地域、年齡、收入和性別,甚至消費者的行為,都不足以用來理解深處巨變中的消費者。
一線二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的消費觀正在趨同,甚至三四線城市的消費者比深陷“北上深杭”圍城的消費者更有消費升級的欲望和實力。同樣,80后和90后,美國米德蘭小鎮的居民和上海張江工業園的員工,在對消費品類的需求上并無太大差異。
Trendwatching.com用后人口學消費主義(Post Demographic Consumerism)來解釋在消費升級中趨于一致的消費者。全球的消費者,無論年齡和國別,都在自由地在不同身份中轉化。這一趨勢的主要驅動力為:
·信息和商品觸手可及(Access)。無處不在的互聯網和全球化,讓信息觸手可及,也讓商品觸手可及。超級品牌如Apple、宜家、耐克和優衣庫,遍布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制造獨特有統一的消費體驗:愛美、怕死、缺愛。
·包容和“自由”(Permission)。城市化和商品化讓傳統崩塌,也讓人們更加包容和自由。
·消費者的超級能力(Ability)。互聯網帶來了另一次“文藝復興”。消費者得到了解放, 他們有更多的信息渠道去了解意見商品,甚至可以有能力在不擁有所有權的情況下使用和體驗大多數商品。
·超越自身購買能力和社會地位的消費欲望 (Desire)。無論是月薪幾千還是上萬,同樣都是拿蘋果手機出街。新的身份符號,包括商品中的體驗、品質、健康、道德和有機等特質,成為不同階層共同的消費訴求。
品牌“重啟”
消費者的“不可觀測”和消費者群體界限的模糊,讓市場細分和定位沒有了用武之地,也讓品牌變得無所適從。
越是悠久的品牌,越有可能被貼上“老套保守”和“不潮不Cool”的標簽。在擁抱變化和引領潮流的過程中,“大公司病”讓這些品牌變得遲緩而多余。
更為尷尬的是,在全球經濟下行的環境下,大公司和大品牌們反而變得更加謹慎和保守。出售業務、縮減預算、瘦身裁員,這些曾經的超級公司和品牌們鮮有驚喜。
有品味的消費者選擇更個性的網紅淘寶店,而非爛大街的LV,有夢想的求職者選擇更小更美的創業公司,而非世界500強。
我們在經歷一個體驗比品牌重要的消費升級。在這個過程中,品牌的意義和價值不再依賴于品牌的歷史,也不依賴于4A公司和企業品牌部的品牌手冊和廣告,而是用戶體驗的累積。
重啟“品牌”,讓品牌在新的消費升級浪潮中生存,不僅需要產品和服務的創新,更需要重新探索品牌的意義和打開方式。
首先,品牌的意義不應只是質量和品質的“代言”,更應該從一個高高在上的符號變成可以變化和觸摸的體驗。
即使最應該“端著”的勞斯萊斯,也讓自己尊貴的豪車進入了Xbox One的Forza Motorsports的游戲,和一眾超跑飆車。還有格調不知道高到哪里去的英國伊頓公學,從2015年開始為一心想贏在起跑線上的中國家長和孩子開通了網上學習平臺。
第二,延伸品牌的價值。品牌應該嘗試“跨界”,提供滿足消費者自我實現需求的PLAN B。
比如,中產階級喜歡馬拉松,也喜歡有品質的酒店,巴塞羅那的文化東方酒店(Mandarin Oriental Barcelona)就在馬拉松比賽期間提供私人訓練師、跑步裝備以及為期5天的訓練課程和醫療支持。
再比如,中產階級喜歡旅游,也在意身材和健康,郵輪Seabourn索性計劃變身成一個海上“健身房”和“瑜伽館”。
第三,讓品牌滿足“缺愛”的中產階級補愛的需求。
對于新的中產階級來說,TOMS和Warby Parker的“買一捐一”帶來的自我實現滿足要遠遠大于傳統的奢侈品。賣香皂的Hand in Hand、賣水的Faucet Face、賣木制品的WeWood,都是實現中產階級“愛”以及“被愛”訴求的新慈善品牌。
Volvo汽車所有保護行人的努力,都幫助車主營造懂車且有愛的形象。建造太陽能公益體育場的石油公司、致力于弱勢群體教育和就業的快餐連鎖、以及那些稀里糊涂做著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同樣基于一個共同的目的:賦予消費者的愛的能力。
最后,讓品牌變得不再多余希望還有數字化轉型,讓數字化幫助品牌發現新的價值,并和消費者一起共同創造新的品牌體驗。
但這注定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挑戰性不亞于給正在高速行駛的汽車更換輪胎和發動機。全球商業流程解決方案提供商Bizagi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盡管50%以上的公司都在竭力推進數字轉型,但是70%的公司的轉型都受阻于公司內部復雜的機構和流程。其中63%的公司聲稱他們現在的商業模式無法切入數字化。全球營銷技術咨詢公司Real Story Group最近的報告稱,除了企業文化和內部流程之外,技術也是制約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因素之一。高達47%的公司認為他們缺乏合適的技術,打通企業的數據流和業務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