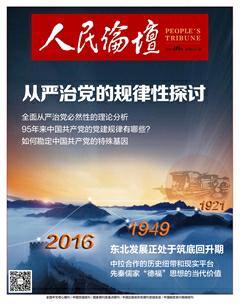陪審制度下非法證據排除模式建構
侯天傲
【摘要】通過對過程證據的審查,可以消除法官對有關證據合法性的懷疑,從而防止偽造、變造證據及非法取證等行為。在這一模式下,有陪審員的參與,可以提高司法透明度以及群眾參與積極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庭審實質化及庭審效率。
【關鍵詞】過程證據 非法證據排除 陪審團制度 【中圖分類號】D925 【文獻標識碼】A
近些年來,我國學術界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及庭審模式的改革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實踐中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越來越普遍,控辯雙方在庭審中對相關證據質證已經成為十分重要的環節。
我國引入陪審團制度的必要性
人民陪審員基數過少。陪審員數量不足的原因有:學歷要求過于單一。介于經濟因素,對于大學專科以上學歷的規定在發達地區一線城市更為合適。在實施過程中,各地都出現了普通群眾比例較低的問題。西部地區、偏遠地區以及農村地區更是無法達到相關規定;選人困難、陪審員產生方式存在分歧。我國人民陪審員不是全職,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當有工作安排時,現階段下很難要求陪審員請假參與案件審理;在陪審員產生的方式中,多數為各單位推薦產生,只有少部分是通過向法院自薦的;法律中沒有明確規定法院應當配備的陪審員人數和比例,具體招收多少陪審員,一般都由法院直接決定,這樣也就造成法院定向招人。
人民陪審員的代表性不強,無法保證群眾廣泛的參與。在分析人民陪審員的工作背景時可以發現,由于學歷等硬性要求及我國現實情況所致,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公職人員占據了大多數。農村地區、西部地區很難產生人民陪審員,因此必然導致群眾的代表性降低。這也與我國國民思想有關,許多人滿足條件但是懼怕耽誤自身發展,拒絕成為人民陪審員或擔任陪審員后很少甚至基本沒有參與過案件審理。因此就要求加強對人民陪審制度的宣傳,提高群眾的認識,并加強相關的法律保障。
陪而不審及“編外法官”。針對于某一具體案件時,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在司法實踐中人民陪審員的產生無法真正做到我國規定的隨機抽取。“來的總來,不來的從來不來”一直是陪審制的真實寫照,某些陪審員參審案件數量幾乎與法官相當,甚至超過了法官的平均值。而另一個極端的陪審員們則是嚴格按照10件以內為最佳的要求,從未違規。過多的案件也會消磨“陪審專業戶”的熱情,加之陪審員的話語權有限,參審范圍較小,陪審員在庭上“陪而不審”觀象時有發生。這兩種現象的出現都與設立人民陪審制的初衷背道而馳。
非法證據排除的模式建立
陪審員的管理和產生。陪審員的任命應當對現有的方式進行規范化,采用自薦結合推薦方式,人數應當與本法院法官人數符合一定比例,法院不得自行決定陪審員的人數。對于學歷的要求應當按照年齡階段分別規定,在偏遠地區、農村地區、西部地區等特殊地區,也應當參照當地平均教育水平設立相應的學歷基準。陪審員應當脫離法院管理選任,人民法院負責統計陪審員信息。
在具體案件中的產生應符合以下要求:陪審團成員應當遵循回避原則,不得有本法院的人員擔任,保證司法公正;鑒于對證據排查的專業性,陪審員應當具有一定的法律職業素養,因此陪審團中至少應有一人為相關法律從業人員,與普通公民共同組成陪審團;當案件需要組成陪審團對證據進行審查時,由法院在庭前會議前一天挑選出與本案無利害關系的部分陪審員供控辯雙方選擇,每方選出等額的陪審員組成陪審團。一審法院為非基層人民法院的,可以在案發地或本轄區內的基層法院數據庫中選擇陪審員。
陪審團的組成。陪審團由控辯雙方在基層人民法院的陪審員名單當中選任。與審判合議庭相同,不論審級高低,陪審團的人數應當為基數。選任時控辯雙方按順序每方選派一人或多人,后雙方達成合意再共同委任具有相關法律知識的另一人為第一陪審員,負責主持該階段庭前會議。雙方無法達成合意的,應當由法院指派一人擔任。
該組成方法筆者同時借鑒了美國審判陪審團的產生方法,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以及首席仲裁員的產生方法。能夠充分保證陪審員的中立性的同時,也可以讓控辯雙方都對陪審員的人選更加認同,也有效地避免了陪審團與法官的關聯,增強司法公信力。
陪審團的功能。當前,司法改革的熱度持續走高。除司法體制本身外,如何對庭審進行改革,加快訴訟效率,降低訴訟成本,提高司法公信力也是重點。對于非法證據排除的適用階段,各種觀點眾口不一。筆者認為,非法證據排除的階段應當適用于整個訴訟階段,并主要設置在庭前會議中集中解決。
法院應當在開庭審理的前一天召集雙方及陪審團,對證據能力問題進行集中審理。雙方通過對過程證據進行“鑒真”的方式,對涉案證據以及過程證據本身的真偽以及證明力進行質證。一旦陪審團無法對涉案證據的合法性達到內心確信的程度,雙方提供的過程證據無法排除對證據非法性以及偵查行為違法的合理懷疑,則應當立即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將相關證據排除,并將經過質證可以使用的證據遞交人民法院。若在庭審過程中有新的證據出現,法官可視情況決定是否重新召集陪審團對證據能力進行質證。陪審團應當對庭前會議的內容對法官保密,法官不可獲知是否有證據被合法排除。法官只得以經過庭前會議判定合法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定罪量刑。
過程證據的審查模式。對于過程證據的審查存在兩種模式:實質審查與形式審查。形式審查是指通過出示、宣讀、部分播放錄音錄像等方式對“過程證據”的真實性進行法庭調查,并聽取控辯雙方的質證。但對于辯方請求相關證言證物的提供者作為證人出庭的請求,一般不予支持。對錄音錄像資料也只是選擇性的播放,因此成為形式審查。
未經過程證據印證,任何結果證據都不可直接作為定案根據使用。原因包括:沒有經過印證,結果證據來源的真實性、偵查行為的合法性、提取證物的合法性都無法得到證實。在我國偵查機關擁有的巨大權利,如果沒有過程證據的完整記載,形成鏈條證明其行為以及取證的合法性,那么就無法保證司法的公正;無論是控方提供的證據還是辯方和法官主動調取的證據,有了過程證據的印證,才能保證其不存在誘證、假證等違法的取證行為,否則結果證據的合法性無從考證;如果無需提供過程證據,就會導致在取證過程中的任意妄為,導致調查取證活動的混亂,影響案件審理。過程證據的存在能夠起到杜絕作偽證,偽造、變造證據行為的作用。
通過對過程證據的審查,可以消除法官對有關證據合法性的懷疑,從而防止偽造、變造證據及非法取證等行為。在這一模式下,有陪審員的參與,可以讓公民參與到司法審判中,提高司法透明度以及群眾參與法制建設的積極性,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遏制貪腐、提高司法公信力。同時在庭前會議中集中進行非法證據排除,不僅保證了案件的公正審理,有效排除非法證據,有效節約司法資源。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①陳瑞華:《論刑事訴訟中的過程證據》,《法商研究》,2015年第1期。
②龍宗智:《庭審實質化的路徑和方法》,《法學研究》,2015年第5期。
責編/王坤娜 孫垚(見習)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