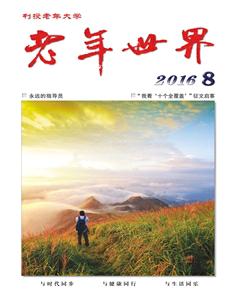歸化城的濟仁堂
謝榮霄
在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舊城),曾有不少老藥鋪,譬如坐落于大北街的濟仁堂和懷仁堂(濟仁堂分號);坐落于大召前街的德泰玉、大召東夾道的“王一貼”藥店,以及大南街上的廣巨藥房等等,這些老藥鋪為歸化城增色不少。在眾多的老藥鋪中,創辦于1921年的濟仁堂名氣甚大,創辦人是我的父親謝重吾。
一
1897年,父親出生在河北省定縣(今定州市)中古屯村,祖父謝介卿是位鄉村醫生。1913年,經人介紹,16歲的父親來到北京,在一家名叫南山堂的中藥鋪學徒。1917年,父親轉到南山堂張家口分號。學徒期滿后,他沒有留在南山堂,而是決意要“走西口”,在塞北創辦一家中藥鋪。
學徒時,父親被譽為南山堂“四大怪”(指四位各具專長的徒弟)之一。這是由于他做中藥蠟丸時的出色表現。做蠟丸,首先要做蠟皮。做蠟皮時,藥工雙手拿著個提子,提子下方有一木頭橫梁,橫梁上有細鐵絲,上面插著若干個木球。藥工拿著這個提子在滾燙的蠟鍋中不停地提上提下,木球表面包上了一層蠟皮。等蠟皮達到要求厚度時,便把提子擱在一邊,晾涼后,把蠟皮一剖為二,取出木球后,就可以用來裝藥丸。裝入藥丸后,再用鉻鐵之類的工具把蠟皮封住,于是一個中藥蠟丸就做好了。父親做的蠟丸,嚴絲合縫,看不出一絲痕跡。
當年北京的中藥行當,同行之間的競爭甚為激烈。于是,父親準備在歸化城開一家藥鋪。1921年,父親和他的表哥等人從河北定縣來到歸化城。經過一番考察,他們相中了城里小東街的一處老院(即后來的謝家大院),決定在大院的臨街房開一家中藥鋪。父親和表哥等6人合伙,投資1000塊銀圓,開了一家叫濟仁堂的中藥鋪,時年24歲的父親任經理。父親在北京學的徒,特意將濟仁堂稱為京字號國藥莊。那時舊城的藥鋪,有些由山西人開辦。把濟仁堂稱為京字號國藥莊,也隱含著與同行暗中較勁的意思。
濟仁堂開業第二年(1922年),祖父從河北定縣來到歸化城,在濟仁堂坐堂。綏遠都統馬福祥的部下鬧瘟疫,遂來濟仁堂求醫。祖父為他們配制了治瘟疫的草藥,這些人服用后,瘟疫盡去。祖父也被委任為軍醫。這些消息不脛而走,濟仁堂有了名氣,來買藥看病的人絡繹不絕,其中以回族人為多。1923年,濟仁堂遷到了繁華的大北街。1924年,在該街北門里開辦了濟仁堂分號——懷仁堂。1932年,在包頭開辦了濟善堂(濟仁堂分號)。
二
舊時,中藥鋪一般采取前店后廠和零售的經營模式,濟仁堂也不例外。它的鋪面坐落在舊城大北街大什字附近,每天車水馬龍。它的生產車間(制藥作坊)則位于舊城九龍灣街路南的一個大院里,格外清凈。從濟仁堂鋪面和制藥作坊的選址看,也可以看出父親的精明。
除精心選擇店址外,在用人上,父親也會量才量德使用。新徒弟上班的第一天,父親會安排他打掃店面衛生。之前,父親有意把一些銀圓放置在店堂里的一些地方。新徒弟打掃衛生時,應是會看到這些銀圓的。對這些銀圓,無論這個徒弟是上交柜上還是私自藏起,父親都不作聲。但他會根據這個徒弟當時的不同表現,來安排合適的工作。“揀銀圓”測試,實際上是對新徒弟的一次品行考核。
除要求徒弟掌握中草藥各方面的技能外,相貌端正又機靈的徒弟,會被父親安排到店面站欄柜(柜臺)。顧客來到店里,店員要熱情接待,有問必答。一旦發現有怠慢顧客,使顧客空手離去的徒弟,要進行處罰。濟仁堂制作的丸、散、膏、丹以貨真價實、童叟無欺享譽歸綏地區,藥店雇工人數最多時達90多人,后來還培養出8位各具專長的徒弟,被稱為濟仁堂的“八大金剛”。
為使濟仁堂被更多的人所知曉,父親命人在大青山的一面山坡上,用黑色油漆書寫了“濟仁堂”3個巨字。在濟仁堂門楣上方,懸掛了有“濟仁堂”字樣的巨匾。此外,他還訂制了一批類似書包的白布包,上面印著“避瘟散”之類的紅字,人們背著這些包行走在大街小巷,就是流動的廣告。而在歸化城三賢廟巷席力圖召后墻上,也有濟仁堂的廣告,是用紅色油漆書寫的。
那時,父親親自去外地采購藥材,中藥材市場有假冒偽劣貨,憑借多年的經驗,父親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在驗貨時,對一些藥材,他只要踢踢裝滿藥材的麻袋,就知道是真貨還是假貨。他的這一絕招,一直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父親對一些細節從不放過,比方用紙包好的草藥,藥包方方正正,還附帶一個過濾湯藥的小紗籮子。父親在生活上對徒弟們很關心,濟仁堂有食堂,平時徒弟們都在那里吃飯。過春節時,濟仁堂大擺宴席犒勞徒弟,席上會有魷魚、海參等名貴菜肴,宴席從農歷正月初一一直擺到正月十五。
三
上世紀20年代,歸綏地區民眾飽嘗了土匪橫行、軍閥混戰、日寇入侵、饑荒、社會動蕩等痛苦。和舊城眾多行當一樣,中藥行當也受到了這些天災人禍的沖擊。
受時局影響,1932年,濟仁堂出現了虧損。為維持生存,父親和其表哥在歸綏東瓦窯村開辦了盆窯。但盆窯生意也不景氣,屢屢出現虧損,只好放棄,繼續經營濟仁堂,但仍是虧損,雇工也銳減。濟仁堂所用藥材有許多來自外地。據濟仁堂當年的徒弟回憶,日寇侵華時期交通受阻,濟仁堂所需藥材無法運抵歸綏,父親遂求助于某位軍事要人,這位要人派出了軍列,父親喬裝成押車的軍人,購回了急需的藥材。
抗戰勝利后,濟仁堂的經營狀況開始好轉。1946年,父親出任了藥業公會監事(1952年擔任了藥業公會副主任)。隨著業務的發展,濟仁堂于1948年從通州招收了一批新徒弟。同年,父親在察素齊收購了大量防風,這批中藥材賣價甚高,讓大傷元氣的濟仁堂腰包鼓了起來。
據記載,1950年春季,政府禁止種植、販賣和吸食鴉片,市里成立了戒煙所,采取強制辦法進行戒煙。市衛生局指定濟仁堂、春和玉兩家藥鋪承制戒煙丸,并在戒煙所內生產。因藥丸內含有鴉片成分,因此還有公安、民政部門的人員現場監督。父親歷時3個月,圓滿完成了任務,吸食鴉片者服用戒煙丸后,效果良好。
1956年,呼和浩特市中藥行業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期間,父親擔任了清產核資委員會委員,后被安排到呼和浩特市國藥總店任副經理和濟仁堂門市部主任。總店成立了制藥廠(大唐藥業公司前身),并召集各藥鋪的技術權威如宋鳳鳴、齊有先和父親等人,對各藥鋪多年來有效驗的傳統藥方進行審核修改,并加工生產,分撥到各門市部銷售。1959年,在呼和浩特地區的醫藥行業中,國藥總店率先進入國營行列。
摘自《內蒙古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