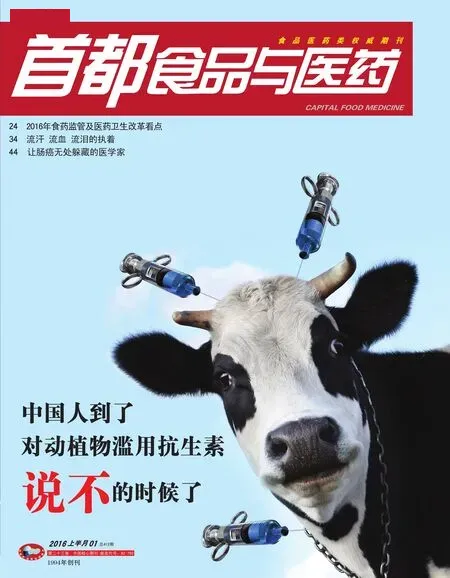人文醫學的星星之火打造有溫度的醫療道阻且長
●許方霄/本刊記者

希波克拉底曾說,醫術是一切技術中最美、最高尚的,愛人與愛技術是并行的。但如今在我國,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部分醫生只注重自身醫術的提升,卻忽視了“愛人”的重要性,面對患者時,表情冷漠、語言生硬。生理上的不適加上精神上的不快,很可能激化醫患矛盾。為了配合醫改,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北京市醫院管理局于2012 年就著手宣傳人文醫學服務理念了。什么是人文醫學?我國人文醫學道路走到什么程度了?對于未來,人文醫學這條路又該怎么走?就此,記者采訪了連續三期參加北京市醫管局的人文醫學培訓班,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心臟外科主任醫師趙鐵夫。
要把病人當人看
記者:前一段時間,北京市醫管局正式啟動了人文醫學巡講團,作為連續三期參加人文醫學培訓的醫務人員,對人文醫學您有何認識?
趙鐵夫:據我了解,這套人文醫學體系是從美國引進的,在美國人文醫學體系的基礎上,中國醫師協會又做了一些本土化的處理。在醫學界有兩個概念,一個是人文醫學,另一個是醫學人文,其中人文醫學的根還是定格在醫學上,它的服務理念是醫務人員要懂得病人的心理和需要,從實際出發為病人服務,換位思考多為病人著想,其主旨就是在醫學實踐的過程中要把病人當人看,考慮到對方是生了病需要幫助的個人或家庭。醫學人文更多的強調人文的理念。
一名真正的好醫生,高尚的醫德、精湛的醫術和藝術性的服務缺一不可,醫學越先進,對醫生醫德及服務的要求就越高。我們都知道,美國對病人的態度特別好,好到病人想跟他發火都發不起來,這種服務我們真該好好學習。
記者:近年來,美國的一些醫學院開設了一門新的醫學教育,叫“敘事醫學”,也是強調醫生與患者之間的交流,在輕松和諧的環境下完成診療活動。請問,人文醫學與敘事醫學是同一個概念嗎?
趙鐵夫:我認為,敘事醫學是包含在人文醫學內的,但與人文醫學還不太一樣。敘事醫學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內外科醫學院的普通內科醫師和臨床醫學教授麗塔·卡倫于 2001 年在美國醫學協會期刊中提出的新名詞,指出醫生要反思自己的實踐;認真而坦誠地與其他醫生談論自己對醫療實踐的反思和困惑;盡可能準確地理解病人,特別是對危重病人所經受的苦難,能感知死亡對人的意義等,敘事醫學還強調文學敘事能力對于醫學的積極意義。但我感覺現在的敘事醫學更多的是在炒概念。

“話療”是一劑良藥
記者:人文醫學在我國目前還算是一個新事物,它建立的初衷是什么?您覺得它有存在和發展的必要嗎?
趙鐵夫:現在國家在做分級診療,不管在專業上還是教學上,未來會越來越好,等建立起分級診療制度之后,我們就能騰出更多的時間,但這些時間不是讓你做假文章或假科研,而是讓你好好對待病人。那么,現在就應該有個儲備和準備了吧?這也是花這么大精力去推廣人文醫學的初衷。
我認為推廣人文醫學很有必要。我有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至今難忘。有個20 歲出頭的四川小伙子曾過來找我,很內向,一直都是他叔叔替他說。在問了相關情況,又看了化驗單后,我理所當然地認為只要一個小手術就能解決,就給他安排一周后手術。由于那天我不在醫院,所以這個小手術就安排給其他大夫了,但術后第二天,科室主任說這個小伙子情況不太好,讓我去看看。他一直說肚子疼,我一摸他肚子,發現脹氣脹得厲害,渾身末梢冒汗、濕冷。要知道,在心外科,病人一旦出現末梢濕冷的情況是很可怕的,一般也就只能活半天了。當天下午,我推掉所有工作給那小伙子手術,折騰整整一下午,除了查明肚子脹的原因外,什么癥狀都好了。第二天早上剛過六點,我就來到病房看他,卻發現他不在病房,打聽后得知是被他叔叔帶回家了。這種情況回家就得死啊!
隨后,主刀大夫告訴我,在我做完手術后,他們讓病人戴呼吸機做了CT,發現他有高度腸阻,非常嚴重,已經有地方破了,便連夜請了幾位大專家,但在討論之后,認為已經沒意義了。怎么會這樣呢?后來,主刀大夫在詳細問了病史后,才得知這小伙子父母雙亡,一直和叔叔一塊兒生活,初中畢業后就出來打工,吃飯也不注意,平時在游戲機廳一待就一天,經常便秘,這事他叔叔都不知道。住院后,當護士問他有沒有大便后,他都說有,其實,在來醫院之前,他已經有一周沒有大便了。
我經常會想,如果當初他坐在我面前的時候,我不只聽他叔叔說,而是讓他自己多說點話,是不是就能說出這點事來了?是不是就能考慮到有這么個問題了?這個失敗的經歷也時刻提醒我,要讓病人把話說全,讓他們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我也希望隨著人文醫學在國內的推動和發展,醫生腦子里這些揮之不去的東西越少越好。這也是人文醫學里重要的內容。
記者:在參加完人文醫學培訓之后,您自身對人文醫學有何感想或人文醫學給您帶來了哪些益處?是否有具體事例?
趙鐵夫:2013 年我第一次參加師資班的學習培訓,是在迫于無奈被點名的情況下參加的,說實話,因為工作太忙,當時特別不愿意去。由于醫生大多都有很強的專業自豪,所以當時我就暗想:我當這么多年醫生,還用你們這些不是學醫的教我怎么看病、出門診?你們出過幾個門診啊,給我講這些?我每天要出那么多門診,照這種方法根本就沒法干。但在學習結束后,我就想著能不能用他們講的方法試一試,但嚴格按照步驟實踐后,我卻突然覺得自己不會看病了。在和培訓老師交流后,我選擇堅持下來,隨后便發現一些驚喜——病人不跟我發火了,說話的態度也變了。以前都說:“大夫,橋堵了,你看怎么辦吧。”而現在說:“趙大夫,我這個橋堵了,咱們怎么辦?”可能對病人來說這兩句話沒有多大區別,但我們聽著會感覺有很大不同。此外,我發現來找我的病人多了,而且很多之前都不是由我為他們做手術的。
比如,有一個順義的老先生到診室坐下后,我問他:“老先生,您怎么不好啊?”“唉。”老先生嘆了口氣,沉默大概3 分鐘后,才說:“30 年前的一個下雨天,我出去遛彎,結果感冒了……”實際上,這位老先生得的是冠心病,和他說的一點關系都沒有,卻足足說了10 分鐘。按照我以前的想法,當時就應該打斷他,然后誘導他把主癥說出來,但我還是強忍耐心聽下來了。其實他的病情并不需要特別處理,口服藥物就行,而他之前在順義的醫院也看過,找的醫生還是位大專家,但是老先生不信任順義的醫院,覺得那位專家說的話也都不靠譜,其實人家的方案完全正確。雖然藥物已經吃了3 個月了,但沒什么療效。我囑咐他再吃上1 個月,然后再來找我看看。1 個月之后,這位老先生真的找我來了,我意外地發現他的狀態特別好。
醫生在開醫囑、做檢查等專業過程的同時,更多的內容應該是“話療”,多說幾句就能對病人起很大作用。美國有一份統計,在所有醫囑中,只有三分之一的醫囑能被正確執行,另外三分之二的醫囑沒有被準確執行甚至沒有被執行。1987 年有個對高血壓病例的統計——第一次見醫生時就把話說全,說出自己想法的病人血壓控制得特別好。我不認為語言交流能降血壓,但最起碼他們能更準確地執行醫囑。很多時候療效不好不是藥和方案的問題,而是醫囑沒有得到有效執行。就像順義那位老大爺,因為他本身就不需要特別治療,你讓他把話說完,可能這10 分鐘就讓他痛快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
改善現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記者:當前人文醫學在國內的發展現狀怎樣?
趙鐵夫:全國各地有遠見的醫院如今都在推動人文醫學的發展,但只是星星點點地開展,目前還沒有發展起來。就拿北京市來說,北京市醫管局從2012年就聯合中國醫師協會醫學人文專業委員會開展了人文醫學職業技能的培訓,截至目前,已為市屬醫院培養了人文醫學培訓師資累計150 余人。這些師資中大部分人員已經成為人文醫學培訓的骨干力量。如今,北京市醫管局是主教練,管著22 家市屬醫院,目前也正在穩扎穩打,并建立自己的長效機制。前一段時間剛成立的人文醫學巡講團巡講工作也已經正式開始,人文醫學巡講團有24名成員,這些成員是從歷次師資培訓中優中推優,產生的核心骨干,在22 家市屬醫院巡回宣講。
對于這套借鑒美國的體系,我們在逐步本土化和完善,因為文化差異的原因,美國有些東西在中國不太現實,而在中國應該強調的東西美國卻沒當回事。這是在以往人文醫學技能培訓的基礎上的優化與升級,同時也標志著市屬醫院人文醫學培訓系列工作逐步形成了規范和常態化。
此外,我國醫生在意識上與美國等發達國家還是有差距的。我拿有些國外對人文醫學的培訓表給醫學生考核時,明確提出不考專業,只考他們和病人的溝通能力,結果96%的學生都不合格,與美國差得太大了。此外,我還發現,在讀的博士研究生臨床溝通能力最差,其次是碩士研究生,這幫真正該學習的人卻是最差的。我時常在想,醫生應該在什么時候接觸人文醫學?是不是在住院醫師的時候就該加強?目前看來應該更早,在本科生的時候就該加強,但是具體是在大四還是大五,還得依據數據來定,這項工作目前也還在探索中。
記者:您認為在人文醫學這條道路上該做何改變或努力,才能達到引進人文醫學的初衷?
趙鐵夫:臨床大夫都注重醫術,希望培養好自己手中的技術,判斷準確、用藥得當,追求醫術精準,注重技術一點錯沒有,以后也會越來越推崇技術,但要清楚,病人不是一塊材料,在注重技術的同時,大夫也要把患者當人看。醫生很忙很累,這個我比誰都知道,但是忙、累與關懷是兩回事。“怎么了?”和“您哪兒不舒服啊?”無論說哪句話,結果是一樣累,也許說話語氣只是大夫的個人習慣,但是病人聽著感覺是不一樣的。在語言上做些人文關懷,這不費事,只需要改變一下習慣就可以。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巡講團將結合市屬各醫院的需求和特點,開展市屬醫院間的巡講與培訓,逐步提升醫務人員的人文技能、方法和素質,我也愿意參與其中,在具體醫療的大環境中,希望能通過我個人的努力,讓更多的醫生萌生“試一試”的想法。如果一名醫生愿意這么做,那么就有一批病人受益,如果愿意嘗試的醫生越來越多,對以后的頂層設計也有好處。但想改善目前狀況,我個人認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這項工作還得從年輕大夫入手。因為同級的大夫認為你沒有那個權威,講得對或不對他們都不愿聽,更別說那些資歷更老的前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