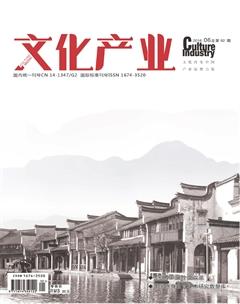真反思與偽科學
劉黎
摘 要:作為一部歷史紀實作品,《走出現代迷信》一書旗幟性的號召我們回到歷史脈絡中,對其進行一番回顧和前瞻,一本書或許只渺小如黑暗中的一艘小舟,在思想的波濤洶涌的海上顯得那么微不足道,然而畢竟已揚帆起航,就必將驚動黑夜。
關鍵詞:歷史;迷信;反思
一、歷史照進現實
歷史與現實并不脫節,是相互映照的。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提到過歷史的反復性,中國在曲折中邁過的這100多年的歷史,又何嘗沒有經歷過一次次歷史的反復呢?即便反復的是結構而未必是事件,然而對歷史的一次次理解偏差卻會導致現實理解的錯誤。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在賀照田《當信仰遭遇危機》一文中提出,在相當的意義上,我們今天所艷稱的中國大陸“新時期”,便是在未對陳映真所提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民主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巨大差距”等重要問題,作充分細致、深入的歷史—結構性分析與反省的基礎上展開的。因為他們自認為代表著“人民”的心聲。更讓人驚異的是,直到今天,對這些問題亦談不上有充分細致、深入的歷史—結構性分析與反省,當然,更談不上以這些分析、反省為視角,對中國大陸“新時期”的發生乃至整個“新時期”的變遷作出分析。
對于一個歷史中存在的關鍵問題,諸多知識分子們為何會集體性的未給予應有的重視?更重要的,當時一批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怎會被“現代迷信”蒙蔽雙眼?作為新世紀的知識青年,我們該怎樣去認清那戴著科學面具的“現代迷信”?從而對我們所經歷或未經歷的,所思考或未思考過的歷史做一次真正的反思呢?就這一點而言,《走出現代迷信》一書有著相當深刻的意義,作為一部歷史紀實作品,它旗幟性的號召我們回到歷史脈絡中,對其進行一番回顧和前瞻,一本書或許只渺小如黑暗中的一艘小舟,在思想的波濤洶涌的海上顯得那么微不足道,然而畢竟已揚帆起航,就必將驚動黑夜。
二、于無聲處聽驚雷
《走出現代迷信》第一部分從這場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背景談起,接著細致重現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的前前后后,最后敘述文章發表后引起的各路反應;第二部分則是十年后對包括陶鎧在內的十余位參與過歷史的學者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訪談。
首先,談及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開始,很多人可能會直接提到作為歷史敘述中著墨最多的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事實上,1976年年底到1977年年初,走出十年動亂的人們還未來得及歡呼雀躍,心又緊緊的收縮了。11月30日,吳德提出要把“批四人幫”和“批鄧”的結合起來,到77年初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祭奠活動的時候,汪東興規定不準周恩來的紀念展覽對外開放,不準《人民日報》發社論,接踵而來的沖擊,引出了兩報一刊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兩個凡是”的提出,這讓人不得不聯想到1976年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人民希望鄧小平盡快出來的心情受到了打擊,好在1977年中央工作會議中華國鋒透漏出了新的氣息,雖然”“兩個凡是”未提出改變,但在華的表述中,已經將“毛”與“四人幫”的思想進行了區分,這是我們理解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契機。處在那樣一個破而未立的時代,全中國都急切地需要一個“認識”去梳理這團糾結的亂麻,這種“認識”是對歷史,對革命,對理論,對體制科學而非“信仰”的認識。
“1978年四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報》社,一張刊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哲學》第五十七期大樣由理論部送到新任總編楊西光手中。按照常規,他將履行最后裁決權,審定之后四月十一日見報。”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這份并沒有出刊的雜志會在百年之后仍不斷的被人提起,只是恐怕后人不會知曉,當時的那張油墨未干的紙片,只是輕輕落在一間不算寬敞的辦公室橢圓形木質書桌上,而它,驚人地代表了歷史的一個新的開端。也許是腦海中長期縈繞的一個夙愿,一份誘惑,存在于楊西光胸中醞釀已久的那個“去眛”的主題和心愿被一份文章重新激發,總之他堅持要將這份文章刊發,而且是“放在第一版發”。經過重重波折,1978年5月十七日,這份修訂了十次、前后歷時七個月的文章終于在《光明日報》一版下辟欄刊出。并在當天,被《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全文轉載;在地方,《遼寧日報》等十多家報紙刊載,一時激起千層浪,引起了上下左右的不同反響。
這場關于理論與實踐的討論問題與“歷史—人事”息息相關,楊易辰在《撥亂反正必須解放思想》一文中就拋出了這個重要問題。“實事求是地總結二十八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究竟是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是反對無產階級大革命?”(242)要讓那些在文革中受沖擊的知識分子們不要再心有余悸,真正解放出來,來擁護這次討論,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四人幫”已經搞壞了之前的一套理論路線,人們背后的心理框架也依舊存在,要想正面挑戰“兩個凡是”,就必須打開歷史的缺口,正面去討論具有多方面歷史效應的毛的遺產問題。當然,這一切都是為了讓大家的力量擰成一股繩從而鞏固社會基礎。
得出歷史結論時,那些在當時提出對這篇文章的反對之聲的人未必該定位為歷史的落后分子,無論是批評也好反對也罷,正是這些各種各樣的聲音匯成不同的激流,激流在不斷的撞擊,從而迸發出更強大的力量,才推動了歷史的進步。理論與實踐的爭論只是表面,怎樣通過這樣一場爭論來解放思想,推翻“偽科學”,得出“真反思”才是硬道理。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是名符其實的偉大的歷史轉折。這是歷史敘述中慣常的描述。于光遠作為一位歷史的親歷者與參與者,他認為,從1976年10月6日到1978年12月的這兩年,可以看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第一個階段(起始階段)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第二個階段(改革階段)之間的過渡階段。從三中全會后的1979年才真正進入到了“改革階段”。即是說,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起始階段向改革階段邁進的分界線。從1979年進入改革階段至今,我們又經歷了一個三十年,在這三十年中,中國地經濟體制、社會體制也在經歷著一步步地變革和發展,可見三中全會所確定下來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是長期起作用的。我想進一步追問的是,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我們還應該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同改革又有著怎樣的辯證關系呢?
三、從迷信到科學
40年后的我們重新討論這場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價值和意義,從而對我們所經歷或未經歷的,所思考或未思考過的歷史做一次真正的反思。問題的關鍵在于,何為現代迷信?最開始的一種落后意識最終怎能演化成一個民族的自覺行為?
“迷信是對某一些事物迷惘而不知其究竟,但又盲目地相信其說。“迷信”的含義更多的傾向于“盲目的相信、不理解的相信”。因此,理論上,人類對任何事物都可能存在著“迷信”的觀念,即使是在有些人從事科學工作,但他們也會抱某種‘科學迷信。”
就是說,迷信源于一種無知,與盲目。但迷除了人類幼年時代對大自然的無知而外,總是某種教化甚至訓誨的結果,是一種有意的行為。“一種事物,必有迷人之處,人家才信;有‘迷有‘信缺一不可。”這就要提到中國的這場現代迷信了。
舉例來講,《東方紅》的作者李有源是個農民。“大救星”是典型的農民觀念,但這支歌唱到后來,其規格已經高于國歌。也就是傳統農民的觀念在飄揚的五星紅旗下不僅為民眾、而且為全黨,包括黨的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所接受。歸根溯源,農民參加革命,脫下舊衣換上軍裝,卻不能徹底地改換幾千年來刻在身上的烙印,即使有一些知識分子和受過現代教育的學生來投奔革命,但缺乏民主的舊中國只有用武裝的革命來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只有由共產黨直接組織隊伍,建立政權,進行戰爭,需要絕對服從;另外,當時的共產國際影響也很大,中國共產黨很長時間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受共產國際的極其嚴格的集中領導,上級對下級有絕對權威。這種組織原則和行為方式,對中國共產黨有著很深的影響。所以,盡管革命的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但生活與行為方式是高度集中和等級森嚴的,這對哪些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也不能不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新傳統與之前提到的老傳統碰到一起,就使得中國的封建主義帶上了一層激進的“革命色彩”與“神圣色彩”,顯得神圣而不可侵犯。
即使和平之后,黨的骨干既非農民,又非士兵了,但一開始就立足于戰爭而誕生的黨并沒能對其自身進行比較完善的現代教育,在這樣的基礎上,一旦革命勝利了,黑暗的舊中國變成了光明的新中國,黨與領袖的威信就容易登峰造極,從而形成“現代迷信”,造成個人崇拜。
本雅明曾提過審美介入政治生活即“藝術政治化”的問題,強調法西斯主義在政治崛起的同時,也在構建政治的靈光,打造法西斯藝術的崇拜價值,而造成了一種領袖崇拜,反觀當時的的中國,一個被唯一的媒體反復宣傳的領袖人物,加上許多儀式,許多物品,許多歌曲,許多書籍奉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場轟轟烈烈的現代造神運動又豈能避免?
要從迷信走向科學,必須理清二者之間的界限。
科學拒絕迷信,但科學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摻雜了各種各樣的迷信,如果一個人不能無條件的相信一些理論,他將無法構建新的理論。科學也不能太靠近懷疑論,懷疑論對真理的存在與獲得秉持著極度的不確定性,使得科學難以形成任何定論。最終由于科學的實用性,使其需要在迷信和懷疑論中間尋求一個平衡點。
任何科學都在不斷的發展,馬克思主義這種科學當然也需要隨著客觀世界的發展而發展,翻開歷史的教科書,正像鄧小平在1976年六月二日講話中所說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同實際情況相結合,就像沒有生命了一樣,停滯了,僵化了,死亡了,或者說沒有生命力了,也就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了,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還堅持什么呢?”
可見,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馬克思主義也不例外。既然是其所處時代的認識和學說,那么就會難以避免的被打上時代的烙印,也就是說必然有它的局限性。由此可見,要想從對馬克主義經典的現代迷信中走出來,發展和不斷的重新認識是一個關鍵詞。20世紀70年代的這場思想解放的意義也正是在此。
四、浮出歷史地表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共產黨經過多次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決策的民主化與科學化也在進一步提高,然而社會主義仍處于發展階段,危機和挑戰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社會主義的發展也并不平坦,怎樣在當下視野重新認識我們的社會主義,今天還需要解放思想嗎,又該堅持怎樣的標準?
汪暉老師在其《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中提到了一個“新啟蒙主義”思想的概念,所謂的新啟蒙主義思想“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而是一種廣泛而龐雜的社會思潮,是由眾多各不相同的思想因素構成的。”“這種新啟蒙主義思想表現在政治上,要求重建形式化的法律和現代文官制度,通過擴大新聞和言論的自由,逐步建立保障人權、限制統治者權力的議會制度(它被理解為政治自由)但是,由于對毛澤東時代的群眾運動的恐懼,許多人對于政治民主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形式民主、特別是法制建設方面,從而把“民主”這一廣泛的社會問題局限于上層社會改革方案的設置和專家對于法律的修訂和建議方面……更令人驚異的是,有些學者無視現代憲政民主中包含的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的內含,完全排斥直接民主在民主實踐中的意義,甚至把民眾的普遍參與看成是專制主義的溫床。”
內蒙古一家國有企業,拖了職工半年多工資,但廠領導進出乘坐卻是卡迪拉克豪華轎車,當記者問公司的管理者,為什么職工工資發不出,還用豪華轎車時,企業領導卻響亮的回答,豪華轎車是國有財產,我又沒上一份錢口袋,那完全是工作需要。可見,所謂的“公有制”對普通職工是多么的虛無縹緲,對掌權者,是多么的實惠。那么,對于“全民所有制”名義下的物質,誰有使用權呢,那就是實際“占用”這件物質的某個“單位”的一部分人,誰有支配權和處置權呢?所謂的“全民所有制”,對其他千千萬萬的百姓而言,究竟意義在哪兒?
顯然,這種“民主觀”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和民主的精神背道而馳的。正基于此,我們才說,在今天的社會,思想解放的提出仍是很有必要的。要真正堅持實踐標準,需要有真正的民主與科學精神。決定的方針,政策,計劃,辦法是否正確,是否具有真理性或是在多大意義上具有真理性,最終要由實踐的結果來證明。
此外,民主討論,集思廣益,并經過科學的分析與論證,這樣才能較好地集中眾多的實踐經驗,包括過去的當前的,使作出的決定具有較多的真理性,即比較符合較多的真理性。這種方法就是“決策的民主化與科學化”。
另一方面,對于當代的知識分子或是說理論工作者來說,首先應該認識到,“注定要在一種距離理想狀態遙遠的知識處境中工作,這是整個世界以當下現實為自己思想關切的知識分子不得不面對的宿命。這一事實應該使思想者對世界深存敬畏,對思想的后果深存戒懼。”這種敬畏的背景來自于,由于現下思想開展所需依憑的知識、理論儲備的荒蕪與單薄,有關現實的知識得來的倉促與直觀,加上此單薄、直觀的后面是對若何有效學習、若何有效面對世界問題的思考的嚴重不足。聯系前言中提出的“被遮蔽的歷史”,我們應該看到,知識分子或是理論工作者們針對的并不是上帝規定給人類知識與思想的限度所可能帶出的那些問題,而是那些我們本來應該避免卻因努力的不夠、反思的不足和心態的非建設性而沒有避免的問題。
怎樣抓住那些建設性的問題?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到社會上實踐中去,這是這次討論帶給我們的第二個啟發。只有注意去傾聽時代的呼聲,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為人民而吶喊。這里我不禁想到了天安門事件的犧牲者張志新,我們可以叫她思想解放的先驅,也可以是戰士。她的偉大之處在于別人緘口時她喊出了第一句,別人趴下的時候她勇敢的站了起來。從某種意義上,當代的知識分子或許正是欠缺了這種敢為人先,做召喚者和開拓者的精神與勇氣。
毛澤東曾經說,和不和工農結合是決定一個知識分子是革命還是反革命的關鍵。也就是,知識分子是否努力去和工農結合為什么曾經對革命那么重要?如此去做的知識分子群為什么就能在中國現代史發揮那么重要的作用。這與這批知識分子能形成恰切有力地政治實踐感,社會實踐與文化實踐感是有著深切關聯的。那么問題是,這些經驗只為建立穩定有力地現代國家的革命時段才重要嗎?相信我們已經有了答案。
五、結語
要想進步,反思是前提,然而無限的反思,而不去真正證實反思所提出來的問題,這就會成為一個新的障礙,那就是在抽象的無限的反思中兜圈子。或許我們更需要的是去理清“思想”和“現實”、“理論”與“實踐”內在聯系,這才是助我們在反思之后重新出發的關鍵步驟。
參考文獻:
[1]陶鎧,張義德,戴晴.《走出現代迷信》[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2]于光遠.1978:我所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3]賀照田.為什么要深度解讀中國近現代思想史[J].東方文化,2004(6).
[4]賀照田.當信仰遭遇危機——陳映真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論[J].開放時代,2010(12).
[5]楊易辰.撥亂反正必須解放思想[J].人民日報,1978(8).
[6]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J].天涯,1997(5).
[7]羅崗.“韋伯翻譯”與中國現代性問題,《理解中國的視野》[M].上海:東方出版社,2014.10.1.
[8]賀照田.當代中國思想論爭的歷史品格與知識品格,《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M].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