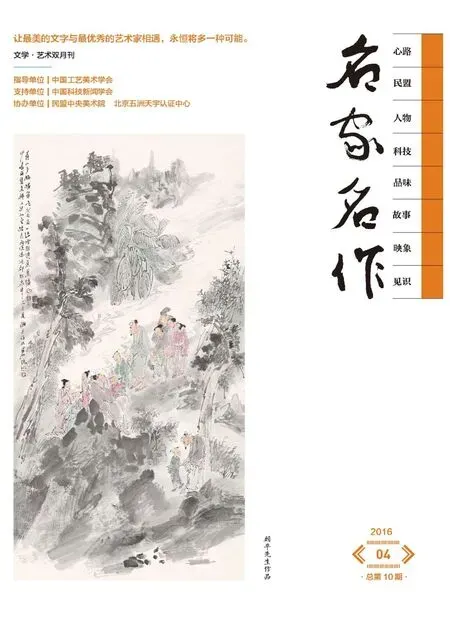心中蓮花開
曾 強
心中蓮花開
曾強

《祈禱》劉步蟾/作
一
如夢如幻,卻又真真切切;真真切切,恰已似泡似影。
欣賞劉步蟾先生的佛教畫,不由得就像看到了蓮,一片蓮,一片搖曳的清純和祥美,一方熠熠生輝的天國凈土,一個澄澈清麗的理想世界。
這個世界,“無苦道滅集”(《心經(jīng)》),是開放的,也是包容的;是端嚴的,也是莊重的;是光明的,也是璀璨的;是具象的,也是虛妄的。
六祖慧能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因此,當劉步蟾先生把佛世間用一幅幅精妙入微完全契合佛教儀規(guī)的圖畫展現(xiàn)出來時,祥美不僅僅是一種華麗的裝飾,一種恬靜的沐浴,還是一幅幅坦淡的心相,是一首首需品味的偈語,是一個個禪意的提悟。更徹底地說,這也是耐心而至善的教誨,或者是,一種普度和流布。
是的,是畫家美好心相的福澤流布。也是,對眾生的普度。
——多純美的蓮呵!
二
佛教畫題材是中國繪畫藝術(shù)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原始巫術(shù)刻畫(字)文化中分蘗、發(fā)展,佛教人物畫最先獨立成畫種。其內(nèi)蘊,都具有勸世、醒悟、懺悔、度眾等明確濃烈的宗教意味。后來逐漸發(fā)展,對佛菩薩畫、經(jīng)變畫、曼陀羅畫等各種佛造像都規(guī)定了嚴格的儀度。《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七卷明確說,佛造像“若不彩畫,便不端嚴;佛若許者,我欲裝飾”。因而,佛教繪畫雖然有著同其他人物繪畫相同或類似的技法,而光憑莊嚴法相、天冠和纓絡(luò)衣飾、標準手印等,構(gòu)筑端肅、莊重、靜穆的意境氛圍,析出的靈靜、神明、慈祥和感召,就不是哪個人敢輕易以身試“法”的。
佛法有據(jù),佛法有道,佛法有靈。
好的佛像畫就像世間的蓮,對眾生來說就是最直觀最便易最有說服力的佛的顯像化身,能使人“轉(zhuǎn)識成智”,進入理想“佛土”。
細觀劉步蟾先生的這些佛教繪畫,可以感知,得法,入心,有靈,如道。
劉步蟾先生的佛教繪畫,一般有兩種筆意。一種是水墨寫意畫,如《達摩面壁》《山中老僧》《六祖禪師》等,這些作品,人物背景多用古法,鐵線勾畫了了,逸筆草草;淡墨渲染,五彩靈動輕盈;輔之以其獨特的古韻悠長的草隸文字,疏密結(jié)合,融為一體;但其畫中,又靜中有動,動之有物,物有所托,人有所依,于空曠畫境中塑造和充盈濃濃禪意。譬如《達摩東渡》,畫面上達摩祖師郁悶生“執(zhí)”,頭頂及迎面是如堵的書法,象征了達摩面見梁武帝而機緣未濟,執(zhí)意去面壁嵩山少林寺的精彩瞬間。

《歲月》(右圖)劉步蟾/作
另一類是工筆畫,如《菩薩像》《生肖護生諸佛像》等。這些畫作秉承他數(shù)十年沉湎于佛教寺廟壁畫臨摹的傳統(tǒng)功力,糅合自幼熟知的民間喜聞樂見的彩繪形式,在尊重程式化“意度量”佛造像的前提下,面容細微處如眼神、嘴唇等,其實都作出獨具匠心但人們幾乎毫無察覺的提振性改變,線條繁縟、流暢、生動、準確,色彩艷麗、柔和、鮮活,富于裝飾,使法相或莊嚴或威武或慈祥或靜穆,皆如法如理,氣度非凡,韻味鮮活,叫人“在拈花微笑里領(lǐng)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禪境”(宗白華《美學(xué)散步》)。
三
優(yōu)秀的佛教藝術(shù)家,應(yīng)該也是佛教另一類高僧大德。佛教繪畫不僅僅是“度他”,更是“度己”。只有一步步“度己”,才能更好地“度他”。
劉步蟾先生的佛教繪畫修為,顯然具有了這樣善根,善性和善念。
我于數(shù)年前兩次見過劉步蟾。先生灑脫而樸素,平和而謙虛,慈悲而恭敬。雖高深如淵,聲名顯赫,但寬大如海,待人如佛。
劉步蟾先生幼年失怙。母親含辛茹苦勤儉持家把他養(yǎng)育成人,使他深刻思想,銘記感恩;尤其是母親尊老愛幼慈悲仁愛的佛家情懷,更在劉步蟾心靈中種下一生的善。
于繪畫,劉步蟾先生從小就摯愛有加。在艱難困苦的日子里,他把繪畫當作生活的主要支撐點,苦中尋樂,苦中味樂,苦中作樂。他時時注重觀察身邊的各種景物,細心體察周邊的事物,敏銳閱歷社會,用心體悟人生真諦,積極提煉和汲取人性中善的因子。他從七歲就刻苦臨摹所能見到的古今各種繪畫范本,由素描而水彩,再油畫、水墨國畫,畫技初成。后憑借扎實的繪畫功底考入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面對肆意汪洋的美術(shù)營養(yǎng),他如魚得水、如饑似渴,全面、系統(tǒng)地學(xué)習(xí)各種美術(shù)技法和理論,又得到繪畫大家葉毓中先生親傳,畫技畫意畫境不斷精進。
在繪畫實踐中,也許是一種昭示,或傾心,劉步蟾先生尤其喜歡畫佛教題材。他特別悟解葉毓中先生的“塑佛即佛,繪天即天,唯心所造,相應(yīng)無礙”。他反復(fù)揣摩佛家的三種境界;第一種,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種,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種,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濾淀內(nèi)心浮躁冗雜,潛心空靜澄明,“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修畫,修身,修行,也修性,終得“明鏡亦非臺”這種佛家崇尚的高層次境界。到后來,連葉毓中先生看了他的畫也連連感嘆:“禪耶?畫耶?步蟾已得化境!”

《山寨春曉》劉步蟾/作
入畫境,入心境。是為化境。但這歸根到底其實就跟蓮花一樣,是一種能夠融入的庸常平凡的生活。文化生活、道德生活和理想生活。當然,這樣的生活,無時無刻不浸透著一種“潤物細無聲”的大善、至善。
所以中央電視臺早在2005年推出的《中國當代畫家》中劉步蟾先生的專題片時,解說詞就這樣評說,“在這個浮躁的年代里,劉步蟾給我們提供了一種獨特的人生方式”。
是的,這是一種我們社會最需要也最應(yīng)該具有的生活方式。
從這個意義上說,劉步蟾先生的佛教繪畫,給我們提供了面壁社會參悟人生的慧眼。
四
人人是佛,佛是人人。我們都具歡喜心,慈悲心和平常心。歡喜可生明凈,慈悲萌發(fā)大德,平常才能不常。人世如此,佛教如此,能叫人直面感知的佛教繪畫藝術(shù)尤其應(yīng)該如此。
劉步蟾先生的佛教繪畫,我以為就是“人人是佛,佛是人人”的具體闡釋。
劉步蟾因畫佛菩薩而享得大名。但據(jù)我所知,他依舊淳樸如初,赤誠如嬰兒。他默默不停地做公益、做功德,做善行;每天修身、修心,修性,自省以“般若波羅蜜多”。他修了再修,一覺再覺,通過繪畫的方式來盡力施善,養(yǎng)德,弘愿,體現(xiàn)“畫是我,我是佛;佛是畫,我也是畫”的佛緣真諦。
周敦頤認為,蓮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愛蓮說》)。
畫中,蓮相即佛菩薩相;心相,也即佛菩薩相。而佛菩薩相,就是我們心靈可以皈依的純樸而寡欲的善相。
所以,細觀劉步蟾的佛菩薩畫,就像置身蓮國,能感覺到不絕如縷的佛光沐浴——這像是溫馨體己的切實關(guān)照,更仿佛與我們細語談心。

劉步蟾簡介:
劉步蟾,法號行一。現(xiàn)任中、日、韓禪研文化中心會長,中國佛教藝術(shù)家協(xié)會主席,曲阜中國畫研究院藝術(shù)顧問,中國禪音書院院長,農(nóng)業(yè)部創(chuàng)作室專職畫家,中國水墨藝術(shù)研究院藝委會主任,青海利生慈善協(xié)會副會長,中國佛教藝術(shù)館館長。中國書協(xié)會員,中國美協(xié)會員,廣西師范大學(xué)客座教授,享受國務(wù)院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