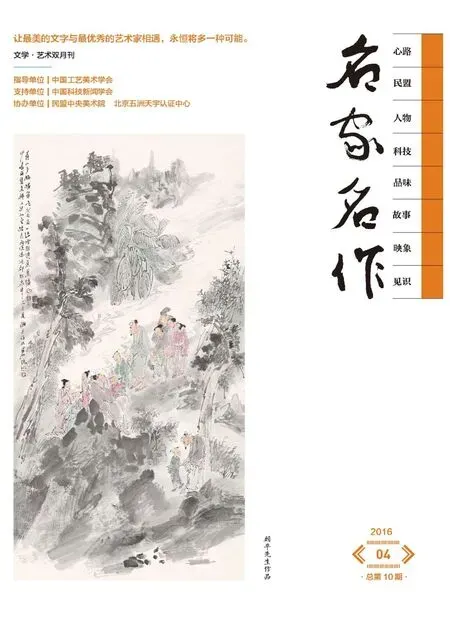孤獨的堅守
黃軍峰
孤獨的堅守
黃軍峰

《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
半入江風半入云。
此曲只應天上有,
人間能得幾回聞。
郭立軍/作
給郭立軍先生的書法作品寫些文字,是件頗為頭疼的事情。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寫過數十位書畫家,至于郭立軍先生的書法藝術,我始終不敢觸碰。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沒有過于張揚的個性,我不想把一些套到任何人頭上都能說的俗話作為應付;他長年累月堅守“二王”之道,關于“二王”的論述不勝枚舉,寫出新意來實屬不易。
起筆的沖動源于不久前的一次閑聊。郭立軍先生數十年如一日的定性堅守,有敬仰,有真誠,有態度,應寫;其謙遜獨立的思考,有深度,有想法,有內容,該寫;其藝術成長的路徑,尊傳統,循墨道,夠沉實,得寫。如果說前些年郭立軍先生的書法作品宛若一位清秀純真的少女,那么他近兩年的作品,更像一位少婦,那是歲月洗禮青春之后的另一番風韻。我一直堅信,任何藝術的成長急功近利來不得,投機取巧更來不得。郭立軍先生的書法之路步履沉實,砸地有坑,業內人贊道不已,業外人拇指高翹,這時我突然覺得,壓抑很久的想法,就要泄洪了。
從最初的顏柳到后來的“二王”,再到王鐸、何紹基、任伯年、鄧石如,等等,郭立軍先生的書法作品,猝然給了我無限想象的空間:他讓我們看到了披星戴月,書房里挑燈獨悟的那個人;讓我看到了書法藝術的包容及一位成功書法家寬厚的心胸。那是沉醉于文房四寶之中情與欲的升華和洗禮。他寫的是敬畏,敬畏那片最優美的天地;他寫的是性格,那個不驕不躁、沉實厚重的人。
相信但凡有些書法常識的人,一提到這門藝術,不能不想到王羲之和王獻之。這些年來,很多頂著“書法家”頭銜的人,論及自身的藝術成長,也總要或多或少拿“二王”來說事。似乎,學習書法,沒臨習過“二王”,就掉了架子。但是,如果細細觀察不難發現,真正在藝術上衷于“二王”,且數十年不離不棄的人,實在鳳毛麟角。
實話實說,作為書法藝術的膜拜者,最初接觸書法我也臨過《蘭亭序》,我也癡迷于“二王”。只不過沒有他執著,沒有他有悟性,沒有他的心態平和,所以,半途而廢,急功近利,最終只能棄而敬之。郭立軍先生則不然。我最初知道這個名字就是因為“二王”,這些年來始終如此。他多年致力于一個根基,我覺得這實屬難得。更難能可貴的是,是其一幅幅清秀雅致的小品。寫這樣的作品,沒有定力與難能可貴的心性,來不得。原因就在于,他既把書法當成職業,又當作興趣的支撐,拋去功利,他只是那么孤獨地寫著,沒想到,寫著寫著就寫出了境界。

《東林寺酬韋丹刺史》
年老心閑無外事,
麻衣草履亦容身。
相逢盡道休官好,
林下何曾見一人。
郭立軍/作
真可謂: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
其實,當今的書法藝術總讓人費解。這其中,有夸大其詞者,有急功近利者,有道貌岸然者,林林總總無外乎一個原因,那就是利欲熏心。這些年,我很少關注書法展覽,那些自命為書法家的“大師”,總喜歡以丑為美,總喜歡花樣百出,且要硬生生地與古人掛鉤,美其名曰循古、金石之類,也許我知淺識薄,總覺得這樣有些別扭。郭立軍先生卻并非如此。我覺得,郭立軍先生的書法造詣歸結于他的為人上。或者說,他的書法里隱隱流淌著的,是帶有文人氣質的孤傲,更有帶著雅士的隨和。更奇妙的是,他的書法在安靜之余,卻又不乏乖巧和靈變,一個方塊字的某一筆,只經他稍加“修飾”,立馬變得乖巧、俏皮、可愛、喜氣,那感覺妙極了。
修養往往決定一個人在藝術上的現在與未來。
郭立軍先生與書法結緣那年,僅有八歲。其老家雄縣之人大都喜歡文物古玩,瓷器上的名人題字成為郭立軍先生與書法的“初戀”。也因為如此,他這一生與書法接下了不解之緣。
當時,村里一位老先生告訴他,寫字時,在手腕上掛一秤砣,功力會大增。那時他年紀尚小,就便掛了七八個銅錢在手腕上,增加手上的負擔,想要以此來增強手腕的控制能力和手臂的力量。結果不到一周,他的手腕就腫了。郭立軍先生突然發現,這并不是練習書法的捷徑,書法練習非一日之功。任何事情都要腳踏實地,沒有捷徑可走。從此以后,郭立軍日日研習,從未間斷。
求學時期,對郭立軍先生練習書法影響最大的便是河北大學的熊任望教授。熊教授是國學大家,他告訴郭立軍,書法一定要深入古人,認真臨摹揣摩古代的經典作品。書法切入所取的格調一定要高,不能只盯著近現代人的作品。這為郭立軍先生之后的書法研習指了一條明路。
路通了,但還需要走。可是對于郭立軍先生而言,他的書法之路也誠如人生之路一樣,總少不了荊棘和牽絆。
有段時間,郭立軍先生寫了很久仍找不到行草書的節奏。自己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甚至痛苦到不想再寫字。可他知道,一旦放棄就等于中斷藝術修行。后來,他遇到了安徽省書協的副主席王亞洲,向他請教行草書的書寫節奏問題。“可這是人家研究多年的經驗,怎么會輕易傳授給我呢?他只對我說,你就臨帖吧。”郭立軍并不死心,又多次去家中拜訪,到第四次時,王亞洲老師終于被感動,決定告訴郭立軍其中的奧秘。王老師業余時間特別喜歡吹笛子,在笛曲方面造詣很高。他只為郭立軍播放了一首他自己吹奏的笛曲《掛紅燈》,郭立軍瞬間頓悟。那一刻,他明白了書法的節奏不是來自于書法,而是來源于音樂。王亞洲老師的點撥,化解了他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的疑慮。
……
在深深淺淺的聊天中,很多事情,郭立軍先生輕描淡寫。我知道,在這輕描淡寫之中,蘊含著的,是一位書法家一路走來的不容易。只不過這些,對于一個鐘愛書法藝術的人而言,總顯得那么微不足道。
這些年來,郭立軍先生始終沒有間斷過對“二王”的研究。在此之前,我以為他不過是以“二王”起家的書法家而已。聊過之后我才發現,原來他對“二王”的理解如此深刻。我想,作為一名書法家,這樣的品格不能少。只有將經典與傳統融化于內心,不斷在經典之中尋找靈光點,一遍又一遍,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是一種超越和成長。
《書譜》中有這樣一段話: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鐘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而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鐘張信為絕倫,其余不足觀。……吾書比之鐘張,鐘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

《題大庾嶺北驛》(右圖)
陽月南飛雁,
傳聞至此回。
我行殊未已,
何日復歸來。
江靜潮初落,
林昏瘴不開。
明朝望鄉處,
應見隴頭梅。
郭立軍/作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鐘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于前規;摭以兼通,故無慚于即事。”
在郭立軍先生看來,王羲之的書法風格是遒美,其實這很表面。王羲之的書法方圓并用,剛柔相濟,篆隸皆備,變化無端。其隨心所欲,行所當行,止所當不得不止。而且,在許多筆畫中你可以看到其中篆書的筆意、隸書的筆意,以至于有刀刻之痕。既有魏碑風,也有折釵股,也有飛白書。雖然各種元素的運用只占其書寫總量的一部分,如果不細心,也許你分辨不出來,但僅僅這一些開始的應用已經足夠達到豐富多彩、美不勝收的程度。這不僅是技法問題,這是審美,也是人的內性之美。
現在人常言,書法藝術“取法乎上”。郭立軍不排斥這樣的說法,但他更注重的是內在情感的表達。試想一下,王羲之寫《蘭亭序》考慮過技法嗎?王羲之寫的,是內心的表達,是人性的化身,是完完全全自我情感的呈現。
書法的背后是人,表現人才是書法的真正目的,是書法的最高境界。人的個性、人的觀念、人的情感、人的品質和修養,總之是人的內在的東西才是書法家所要真正表達的東西,它才是書法取之不盡的真正的藝術源泉,而技巧只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弘一法師晚年的書法,形式簡單,用筆純粹,極少變化,卻境界高遠,人皆愛之。這是與他所追求的佛法修道之境界相一致的,佛道之內修而明達,純粹而高遠,正與此風相吻合,所以這樣的形式就是最好的形式。
很長一段時間,郭立軍先生讀《心經》,寫《心經》,日不能歇,頻頻成作。同一種內容,每次看到,感覺卻都不一樣。突然明白,郭立軍是不是在佛經里悟到了什么?可能吧,但最重要的是,有些悟是后天的,有些悟是先天的,尤其是在書法藝術上,孰輕孰重,我不敢斷言。有一點毋庸置疑,郭立軍愛書法、愛寫字的這種路子和方式讓我汗顏,讓我喜歡,起碼我從他寫字的這種態度上,明白了很多。
我相信,幾年之后,會有更多的人,尤其是以書法為職業的人,能看透其中的玄機。我更堅信,這樣矢志不渝地走下去,郭立軍先生的書法作品一定能寫出自己,寫出關于書法藝術的另一道風景……

郭立軍簡介:
郭立軍,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河北省書協理事,河北省書畫藝術研究院副院長,河北省第十一屆青聯委員,河北師大歷史文化學院書法客座教授,東垣書社副干事長,河北電視臺《品真》欄目特約藝術嘉賓,河北省資本研究會特聘藝術顧問。其書法作品多次在國家級大賽中獲獎,并被文化部《中國書畫人才詞典》授予“當代優秀書畫人才”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