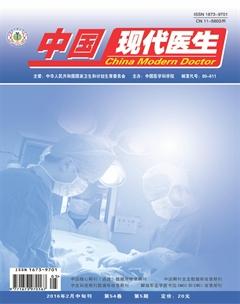MIPO技術(shù)治療高能量Pilon骨折
龔子順 蓋偉 李長(zhǎng)飛 朱東波 鄧介超



[摘要] 目的 觀察應(yīng)用MIPO(minimally invasive plate oseoynthesis)技術(shù)治療Pilon骨折的臨床效果,探討在高能量Pilon骨折應(yīng)用MIPO技術(shù)治療的臨床應(yīng)用價(jià)值。 方法 回顧分析2008年8月~2012年8月間38例在我院應(yīng)用MIPO技術(shù)治療的高能量Pilon骨折患者為MIPO技術(shù)組。入組患者平均年齡39.2歲,按照Ruedi-Allgower骨折分型,其中Ⅱ型28例,Ⅲ型10例;對(duì)照組采用切開復(fù)位內(nèi)固定術(shù),共納入42例患者,Ⅱ型骨折25例,Ⅲ型骨折17例。采用踝關(guān)節(jié)Olreud-Molander功能評(píng)分對(duì)踝關(guān)節(jié)功能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對(duì)兩組的手術(shù)前后X線資料和隨訪結(jié)果進(jìn)行數(shù)據(jù)分析。 結(jié)果 兩組病例均獲得隨訪,平均隨訪時(shí)間為1.9年(1~3.2年)。兩組患者Olreud-Molander踝關(guān)節(jié)評(píng)分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 結(jié)論 結(jié)合完善的術(shù)前計(jì)劃、恰當(dāng)?shù)氖中g(shù)時(shí)機(jī),應(yīng)用MIPO技術(shù)治療高能量Pilon骨折能夠取得良好的效果。
[關(guān)鍵詞] 高能量損傷;Pilon骨折;MIPO技術(shù);骨折內(nèi)固定
[中圖分類號(hào)] R687.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 1673-9701(2016)05-0004-05
Pilon骨折(也稱脛骨遠(yuǎn)端平臺(tái)骨折或脛骨遠(yuǎn)端爆裂骨折)是指累及脛骨遠(yuǎn)端干骺端與關(guān)節(jié)面的劈裂壓縮或粉碎骨折,可同時(shí)伴有內(nèi)踝骨折、外踝骨折或后踝骨折,并且常伴有腓骨下段骨折和嚴(yán)重的軟組織損傷,是骨科常見(jiàn)的關(guān)節(jié)內(nèi)骨折之一。雖然在臨床工作有多種方式治療Pilon骨折,但無(wú)論應(yīng)用何種治療方式,其預(yù)后并不十分理想。在Pilon骨折治療過(guò)程中,高能量Pilon骨折的治療,在臨床上仍具有一定困難性和挑戰(zhàn)性。
本文對(duì)38例高能量Pilon骨折患者進(jìn)行回顧性比較分析,所有病例均采用Ruedi-Allgower骨折分型[1]中的Ⅱ、Ⅲ型Pilon骨折。所有病例均應(yīng)用MIPO(minimally invasive plate oseoynthesis)技術(shù)進(jìn)行手術(shù)治療。隨訪結(jié)果按Olreud-Molander等[2]踝關(guān)節(jié)功能評(píng)分進(jìn)行功能評(píng)價(jià)。根據(jù)X線資料(治療前后)和隨訪結(jié)果,對(duì)高能量Pilon骨折應(yīng)用MIPO技術(shù)治療的臨床效果進(jìn)行深入分析,對(duì)于高能量Pilon骨折來(lái)說(shuō),完善的術(shù)前計(jì)劃、合適的手術(shù)時(shí)機(jī)、熟練地應(yīng)用MIPO技術(shù)等問(wèn)題進(jìn)行討論,為治療高能量Pilon骨折的方法選擇提供理論依據(jù)。現(xiàn)報(bào)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08年8月~2012年8月在我院治療的高能量Pilon骨折且獲得完整臨床資料共80例患者,MIPO技術(shù)組為運(yùn)用MIPO技術(shù)治療共38例,男25例,女13例;年齡18~60歲,最大59.3歲,最小18.5歲,平均39.2歲;病因:交通傷19例,高空墜落傷11例,機(jī)器碾軋傷8例。所有病例單側(cè)新發(fā)骨折,合并損傷包括:顱腦損傷2例,內(nèi)臟損傷1例;伴有其他部位骨折包括:脊柱骨折6例,跟骨骨折3例,距骨骨折1例。根據(jù)Ruedi-Allgower骨折分型[1]:Ⅱ型28例;Ⅲ型10例。切開復(fù)位內(nèi)固定術(shù)組42例,Ⅱ型25例,Ⅲ型17例;病因:交通傷20例,高空墜落傷22例。合并損傷:顱腦損傷3例,內(nèi)臟損傷2例;伴有其他部位骨折包括:跟骨骨折5例。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手術(shù)方法
1.2.1 MIPO技術(shù) 患者平均在傷后13.5 d進(jìn)行手術(shù),其中21例患者采用腰硬聯(lián)合麻醉,17例采用全身麻醉。術(shù)中應(yīng)用止血帶。麻醉滿意后,取仰臥位,伴有腓骨骨折先行腓骨固定,取腓骨嵴后側(cè)縱行切口,注意避免損傷腓淺神經(jīng),顯露腓骨,復(fù)位,選用重建鋼板或解剖板固定。脛骨遠(yuǎn)端骨折,C型臂透視決定鋼板長(zhǎng)度和放置位置,脛骨遠(yuǎn)端前內(nèi)側(cè)鎖定接骨板近端至少保留4孔,避開軟組織嚴(yán)重?fù)p傷部位,應(yīng)用MIPO技術(shù),沿內(nèi)踝切口,充分顯露脛骨遠(yuǎn)端內(nèi)側(cè)面,注意保護(hù)大隱靜脈,C型臂透視下,間接復(fù)位;對(duì)于關(guān)節(jié)面粉碎嚴(yán)重(關(guān)節(jié)面移位較大)、間接復(fù)位不滿意的,則另行一切口進(jìn)行輔助復(fù)位,以距骨作為骨折復(fù)位模板,恢復(fù)關(guān)節(jié)面解剖形態(tài),充分利用復(fù)位鉗或克氏針進(jìn)行臨時(shí)固定,C型臂透視,復(fù)位及長(zhǎng)度恢復(fù)后,LCP板橋接固定(脛骨前內(nèi)側(cè)鎖定板)。檢查骨折是否穩(wěn)定,尤其是前方骨折塊,若存在固定不確切,需螺釘單獨(dú)固定,增強(qiáng)穩(wěn)定性;對(duì)于關(guān)節(jié)面嚴(yán)重壓縮或干骺端骨缺損,需用自體骨進(jìn)行植骨。確定復(fù)位固定滿意后,關(guān)閉切口。
1.2.2 切開復(fù)位內(nèi)固定術(shù) 平均在傷后14 d手術(shù),其中31例患者采用腰硬聯(lián)合麻醉,11例采用全身麻醉。術(shù)中均應(yīng)用止血帶。術(shù)中取適合充分暴露骨折端的手術(shù)切口,直視下復(fù)位骨折,克氏針臨時(shí)固定,并用C型臂確認(rèn)復(fù)位滿意。以LCP接骨板固定骨折,C型臂透視下確定骨折對(duì)位對(duì)線良好。放松止血帶,止血沖洗,逐層關(guān)閉切口。
1.3 術(shù)后處理
根據(jù)術(shù)前患者軟組織情況決定術(shù)前是否應(yīng)用抗生素,根據(jù)術(shù)中情況,決定術(shù)后抗生素使用時(shí)間;患肢抬高,觀察末梢血運(yùn)變化,指導(dǎo)患肢功能煅煉;術(shù)后根據(jù)情況1~3 d進(jìn)行換藥,依據(jù)傷口及軟組織情況,指導(dǎo)踝關(guān)節(jié)功能煅煉;1~2周進(jìn)行非負(fù)重下功能煅煉。出院后,復(fù)查骨折愈合情況,指導(dǎo)患者逐漸由非負(fù)重練習(xí)過(guò)渡到部分負(fù)重練習(xí),直至最后完全負(fù)重行走。
1.4 術(shù)后隨訪及療效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
術(shù)后分別于3、6、12、24、36個(gè)月,以門診復(fù)查方式進(jìn)行隨訪。
術(shù)后踝關(guān)節(jié)功能根據(jù)Olreud-Molander功能評(píng)分[2]:優(yōu):>92分,無(wú)疼痛,無(wú)腫脹,步態(tài)正常,運(yùn)動(dòng)范圍正常;良:87~92分,微痛,輕微腫脹,步態(tài)正常,3/4運(yùn)動(dòng)范圍;可:65~86分,活動(dòng)后疼痛,步態(tài)正常,1/2運(yùn)動(dòng)范圍;差:<65分,行走時(shí)疼痛或靜息痛,腫脹,跛行。
術(shù)后骨折復(fù)位Burwell-Charnley放射學(xué)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3],解剖復(fù)位:內(nèi)外踝無(wú)側(cè)方移位及成角移位,分離與嵌插<1 mm,后踝向近端移位<2 mm,未發(fā)生距骨移位;復(fù)位一般:內(nèi)外踝無(wú)側(cè)方移位及成角移位,外踝前后移位2~5 mm,后踝向近端移位2~5 mm,未發(fā)生距骨移位;復(fù)位差:任何內(nèi)外踝側(cè)方移位、外踝前后方向移位、后踝移位>5 mm,發(fā)生距骨移位。
1.5 統(tǒng)計(jì)學(xué)處理
采用SPSS16.0軟件進(jìn)行統(tǒng)計(jì)處理,對(duì)主要指標(biāo)做描述性分析,計(jì)數(shù)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yàn),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
2 結(jié)果
2.1 術(shù)后隨訪情況及并發(fā)癥
兩組病例完整隨訪,隨訪時(shí)間為1~3.2年,平均為1.9年。骨折愈合時(shí)間2~19個(gè)月,平均4.3個(gè)月。
MIPO技術(shù)組病例未發(fā)生骨折不愈合、感染、釘板斷裂及螺釘進(jìn)入關(guān)節(jié)腔,其中5例切口皮緣壞死,3例通過(guò)換藥后痊愈,2例遷延不愈,最終竇道形成,究其原因?yàn)樯顚渔i釘裸露(圖1)。其中1例在術(shù)后6周將鎖定釘取出,經(jīng)換藥,切口愈合,另1例拒絕取出鎖定釘,遺留勞累后即伴有竇道滲出。其中5例伴有慢性疼痛(活動(dòng)后疼痛和靜息痛),其中3例發(fā)生創(chuàng)傷性關(guān)節(jié)炎。
2.2 術(shù)后踝關(guān)節(jié)Olreud-Molander功能評(píng)分比較
MIPO技術(shù)組優(yōu)良率為86.84%,切開復(fù)位內(nèi)固定組優(yōu)良率64.29%,兩組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χ2=78.467,P<0.05)。見(jiàn)表1。
2.3 兩組復(fù)位效果比較
兩組骨折復(fù)位按照Burwell-Charnley放射學(xué)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3]的復(fù)位效果比較。MIPO技術(shù)組解剖復(fù)位21例,復(fù)位一般14例,復(fù)位差3例。切開復(fù)位內(nèi)固定組解剖復(fù)位29例,復(fù)位一般11例,復(fù)位差2例,兩組比較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χ2=3.092,P=0.079>0.05)。見(jiàn)表2。
表2 兩組復(fù)位效果比較
3討論
1911年,法國(guó)放射學(xué)家Etienne Destot首先對(duì)此種類型骨折有所描述[4],并使用Pilon骨折一詞。Pilon骨折損傷機(jī)制較復(fù)雜,骨折及軟組織損傷常較重,且脛骨遠(yuǎn)端血供差,軟組織薄弱,并發(fā)癥多,預(yù)后不肯定,是骨科疾病中的一個(gè)難題。高能量Pilon骨折主要是軸向壓縮力,通過(guò)垂直方向?qū)⒆饔昧ο蛳聜鬟f,使脛距關(guān)節(jié)遭到距骨撞擊,所致?lián)p傷常較重,脛骨干骺端及關(guān)節(jié)面損傷嚴(yán)重,通常伴有腓骨骨折,同時(shí)軟組織損傷亦較重,局部易腫脹和易形成張力性水皰,最終治療結(jié)果難以令人滿意。高能量損傷其并發(fā)癥的發(fā)生率相對(duì)增高,如早期的軟組織損傷情況、傷口的愈合情況,晚期的骨折延遲愈合、畸形愈合及不愈合情況、骨髓炎及創(chuàng)傷性關(guān)節(jié)炎等諸多問(wèn)題。Pilon骨折屬于關(guān)節(jié)內(nèi)骨折,若治療不恰當(dāng),踝關(guān)節(jié)功能嚴(yán)重受損,而且高能量Pilon骨折的患者又多為青壯年,故此在治療選擇上,如何使踝關(guān)節(jié)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復(fù)、減少并發(fā)癥的發(fā)生,仍是骨科中最具挑戰(zhàn)性的難題之一。
隨著醫(yī)學(xué)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和研究的深入,針對(duì)Pilon骨折的治療方式也相應(yīng)靈活,根據(jù)情況采用切開復(fù)位內(nèi)固定、外固定架固定、有限切開內(nèi)固定結(jié)合、分多次行切開復(fù)位內(nèi)固定及踝關(guān)節(jié)融合等多種治療方式[5]。近年來(lái),隨著對(duì)微創(chuàng)理念及技術(shù)研究的不斷深入,在治療Pilon骨折過(guò)程中,微創(chuàng)技術(shù)也得到了廣泛的應(yīng)用[6]。
微創(chuàng)固定技術(shù)MIPO(minimally invasive plate osteosynthesis,微創(chuàng)接骨板固定)是Krettek等[7]于20世紀(jì)90年代提出,包括關(guān)節(jié)外骨折的經(jīng)皮微創(chuàng)接骨板固定技術(shù)(minimally invasive plate osteosynthesis,MIPO)和關(guān)節(jié)內(nèi)骨折的經(jīng)關(guān)節(jié)經(jīng)皮接骨板固定技術(shù)(transartic-ular approach and percutaneous plate osteosynthesis,TAPRO)。高能量Pilon骨折治療過(guò)程中應(yīng)用MIPO技術(shù),通過(guò)合適手術(shù)入路,將損傷嚴(yán)重的軟組織有計(jì)劃的避開,即減少了切口感染、皮膚壞死的發(fā)生率,又能通過(guò)切口顯露踝關(guān)節(jié),對(duì)關(guān)節(jié)的復(fù)位不產(chǎn)生絲毫的影響。術(shù)中采用無(wú)創(chuàng)技術(shù),不剝離骨膜,最大程度地減少和避免血運(yùn)的破壞,鎖定鋼板屬于彈性固定,骨折區(qū)域存在微動(dòng),同時(shí)骨折區(qū)域的微動(dòng)通過(guò)刺激骨痂的生成間接加速了骨折的愈合。
3.1軟組織損傷程度的判斷和早期處理
通過(guò)對(duì)病史的詳細(xì)詢問(wèn),細(xì)致地查體,分析其受傷機(jī)制。對(duì)病史的詢問(wèn),初步推斷其受傷機(jī)制,簡(jiǎn)單地了解一些患者的基礎(chǔ)疾病;研究其受傷機(jī)制,預(yù)估造成Pilon骨折的外力強(qiáng)度,對(duì)骨折程度和軟組織損傷情況有初步判斷;仔細(xì)認(rèn)真地查體,除外是否存在合并傷,查看軟組織情況和末梢血運(yùn)情況。造成Pilon骨折的高能量損傷所產(chǎn)生的暴力除對(duì)骨折造成明顯的移位,其對(duì)軟組織造成的損傷也很嚴(yán)重。若不及時(shí)正確地預(yù)判軟組織情況,由此引起軟組織問(wèn)題,會(huì)嚴(yán)重影響Pilon骨折治療的效果[8]。患者入院后,盡可能恢復(fù)患肢一個(gè)暫時(shí)維持骨折穩(wěn)定和肢體長(zhǎng)度的環(huán)境,如行跟骨牽引或外固定架(圖2),使骨折斷端減少對(duì)軟組織的刺激,輔以消腫藥物及抬高患肢等治療[9]。完善術(shù)前X線及三維重建CT,務(wù)必仔細(xì)分析術(shù)前X線及三維重建CT,必要時(shí)行健側(cè)X線檢查,制定詳細(xì)的術(shù)前計(jì)劃[10]。
3.2 手術(shù)時(shí)機(jī)的選擇
避免手術(shù)并發(fā)癥的關(guān)鍵是手術(shù)時(shí)機(jī)的選擇。伴有高能量損傷Pilon骨折,其局部通常伴有嚴(yán)重的軟組織損傷,小腿遠(yuǎn)端軟組織比較薄弱且包容性又較差,因此如手術(shù)時(shí)機(jī)選擇不當(dāng)會(huì)帶來(lái)諸如皮緣壞死、傷口感染、內(nèi)定外露、骨外露嚴(yán)重致手術(shù)失敗等手術(shù)并發(fā)癥。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護(hù)軟組織,減少并發(fā)癥的發(fā)生,手術(shù)時(shí)機(jī)正確選擇也是Pilon骨折治療過(guò)程中的一個(gè)重點(diǎn)。一般情況下,軟組織損傷具有滯后性的特點(diǎn),創(chuàng)傷后7~10 d行手術(shù)治療不失為一個(gè)謹(jǐn)慎的辦法[6]。Borrelli提出,有些高能量損傷導(dǎo)致軟組織損傷嚴(yán)重的,手術(shù)甚至需要等待10~21 d后進(jìn)行[11]。Sirkin提出,Pilon骨折應(yīng)于傷后立即行腓骨骨折切開復(fù)位內(nèi)固定術(shù)治療,視軟組織情況在行脛骨骨折切開復(fù)位內(nèi)固定術(shù)或平均等待傷后13 d軟組織腫脹消退后再行手術(shù)治療[12]。評(píng)估軟組織腫脹程度的一種重要方法是查看皮膚是否存在褶皺,皮膚存在褶皺初步證明腫脹的軟組織已開始逐漸消退。最后根據(jù)軟組織穩(wěn)定情況(平均13.5 d,一般10~21 d),再進(jìn)行手術(shù)治療,這樣即規(guī)避了原始損傷和手術(shù)對(duì)軟組織造成的重復(fù)損傷,又能讓軟組織在術(shù)前得到一定的恢復(fù),增強(qiáng)局部抵抗力,降低手術(shù)風(fēng)險(xiǎn),減少并發(fā)癥的發(fā)生。
3.3 病例選擇和術(shù)前計(jì)劃
Pilon骨折,尤其是高能量Pilon骨折,其脛骨干骺端骨折移位較大、關(guān)節(jié)面損傷嚴(yán)重,同時(shí)局部軟組織損傷嚴(yán)重。治療Pilon骨折,尤其是高能量Pilon骨折應(yīng)用MIPO技術(shù)時(shí),并不是所有病例都適合。通過(guò)分析治療Ⅱ型Pilon骨折時(shí),均可應(yīng)用MIPO技術(shù);在治療Ⅲ型Pilon骨折時(shí),一般選用無(wú)腓骨骨折或簡(jiǎn)單腓骨骨折的病例。通過(guò)詳細(xì)分析術(shù)前X線和三位重建CT,有時(shí)加拍健側(cè)X線,制訂術(shù)中復(fù)位步驟及骨折復(fù)位的最終位置;手術(shù)切口的選擇,要避開軟組織損傷嚴(yán)重區(qū)域;若術(shù)中需要輔助切口進(jìn)行復(fù)位時(shí),要充分考慮輔助切口的位置,避免切口皮緣過(guò)近可能造成的皮緣壞死等并發(fā)癥;若存在腓骨骨折,還要兼顧腓骨復(fù)位切口入路[13]。術(shù)前計(jì)劃的充分準(zhǔn)備,才能應(yīng)對(duì)手術(shù)中各種可能出現(xiàn)的狀況,將骨折風(fēng)險(xiǎn)降至最低,從而也間接地降低了并發(fā)癥的發(fā)生。
3.4 術(shù)中注意事項(xiàng)
Blauth等[14]提出治療Pilon骨折的“3P”原則,即(perserve,perform,provide),要求盡量恢復(fù)踝關(guān)節(jié)的復(fù)位、力線及穩(wěn)定性,最終達(dá)到骨折愈合,獲得一個(gè)良好、無(wú)痛、正常的關(guān)節(jié),同時(shí)減少感染和創(chuàng)傷并發(fā)癥是Pilon骨折治療的最終目標(biāo)。因此,選擇脛骨內(nèi)側(cè)入路,選擇合適長(zhǎng)度鋼板(C型臂選擇或通過(guò)測(cè)量健側(cè)X線選擇,鋼板為脛骨遠(yuǎn)端內(nèi)側(cè)LCP接骨板)在骨折遠(yuǎn)近端分別切開,遠(yuǎn)端切口要求減少深層軟組織的剝離,沿脛骨內(nèi)側(cè)面的皮下組織與骨膜間向近端剝離,充分保留骨折區(qū)域的血供,利用跟骨牽引或牽開器的的縱向牽開,利用周圍組織所形成張力的使骨折得到良好的復(fù)位,即利用韌帶所產(chǎn)生的張力使Tillaux-chaput骨折塊及后踝Wagstaff骨折塊得以復(fù)位,利用距骨的模板作用進(jìn)行關(guān)節(jié)面骨折的間接復(fù)位,利用克氏針進(jìn)行臨時(shí)固定,若關(guān)節(jié)面粉碎嚴(yán)重,可行一輔助切口,但要注意切口之間距離(避免切口間皮緣問(wèn)題),通過(guò)直視下進(jìn)行復(fù)位,充分顯露關(guān)節(jié),注意關(guān)節(jié)面的復(fù)位順序是由外向內(nèi)、由后向前進(jìn)行,并且后方的Volkmann骨折塊是關(guān)節(jié)復(fù)位的重中之重,將距骨作為模板對(duì)骨折進(jìn)行復(fù)位,恢復(fù)關(guān)節(jié)面的解剖形態(tài)。復(fù)位過(guò)程中若發(fā)現(xiàn)關(guān)節(jié)面嚴(yán)重壓縮或干骺端存在骨缺損,務(wù)必要進(jìn)行植骨(最好為自體骨),不僅有利于骨折的愈合,而且增強(qiáng)了骨折的穩(wěn)定性。放置長(zhǎng)度適宜的鋼板,注意應(yīng)近端至少保留4孔,以保證其穩(wěn)定性。
3.5 植骨
應(yīng)用MIPO技術(shù)治療Pilon骨折時(shí),在Ruedi-AllgowerⅡ型或者Ⅲ型骨折,若沒(méi)有行輔助切口輔助復(fù)位時(shí),一般無(wú)需植骨。若需要進(jìn)行輔助切口輔助復(fù)位時(shí),建議予以植骨,而且要充分植骨。Pilon骨折治療過(guò)程中,若需要進(jìn)行輔助切口復(fù)位的,一般多伴有嚴(yán)重粉碎的骨折,關(guān)節(jié)面不同程度的塌陷,有游離骨折塊,這些因素都會(huì)影響骨折愈合。手術(shù)將塌陷的關(guān)節(jié)面復(fù)位,勢(shì)必形成一空腔,若不植骨,關(guān)節(jié)面會(huì)再次塌陷,骨在空腔中難以長(zhǎng)入,更易使骨折出現(xiàn)延遲愈合或不愈合。因此,在手術(shù)操作過(guò)程中,要盡量減少剝離、減少游離骨折塊形成,需要植骨的盡量取自體髂骨進(jìn)行植骨。
3.6 術(shù)后并發(fā)癥
切口皮緣壞死和感染,通過(guò)分析多發(fā)生在皮膚形成張力性水皰的軟組織區(qū)域;手術(shù)操作進(jìn)一步加重切口局部的腫脹,使切口處皮膚張力增大;再有鎖定釘?shù)拇嬖冢瑯訉?duì)皮下組織及皮膚產(chǎn)生刺激,尤其是局部條件差的區(qū)域,不斷產(chǎn)生滲出,使皮膚難以愈合。故此選擇合適的手術(shù)時(shí)機(jī),即能使得軟組織得到初步恢復(fù),也增強(qiáng)了局部軟組織的抵抗力;同時(shí)對(duì)手術(shù)入路進(jìn)行選擇時(shí),避開皮膚條件差的部位,尤其是認(rèn)為存在深部軟組織受損部位[15]。手術(shù)時(shí)間掌握在一次止血帶(90 min)下完成,因?yàn)樗芍寡獛Ш螅轮溲菇M織腫脹加重,這也增加了切口皮緣壞死和感染的機(jī)率。
在應(yīng)用MIPO技術(shù)時(shí),Olreud-Molander功能評(píng)分[2]可和差的病例均出現(xiàn)在Ⅲ型骨折中,可能與骨折移位、關(guān)節(jié)面塌陷及軟組織損傷損傷程度有關(guān)。但同時(shí)也注意到Olreud-Molander功能評(píng)分[2]與骨折復(fù)位Burwell-Charnley放射學(xué)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3]不完全平行,也就是說(shuō)骨折復(fù)位好,患者活動(dòng)度未必就好。在Ruedi-AllgowerⅢ型骨折,對(duì)于關(guān)節(jié)面粉碎嚴(yán)重的,即便輔助切口輔助復(fù)位,有時(shí)亦不能完全解剖復(fù)位,其產(chǎn)生的后果則是使創(chuàng)傷性關(guān)節(jié)炎及踝關(guān)節(jié)疼痛的發(fā)生率相對(duì)增高。Kellam等[16]指出,骨折的原始損傷移位及其碎裂程度并不是發(fā)生創(chuàng)傷性關(guān)節(jié)炎重要原因,而如何重建關(guān)節(jié)面并使其真正達(dá)到解剖復(fù)位,才是創(chuàng)傷性關(guān)節(jié)炎的發(fā)生的重要原因。
總之,治療高能量Pilon骨折應(yīng)用MIPO技術(shù)能很好地保留軟組織、骨折端的血運(yùn),有利于骨折愈合,鎖定鋼板自身成角固定,對(duì)骨面無(wú)壓迫,即符合生物學(xué)固定原則,又達(dá)到生物學(xué)固定的要求,使患者可以早期進(jìn)行功能鍛煉,對(duì)踝關(guān)節(jié)功能恢復(fù)提供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完善的術(shù)前計(jì)劃、合適的手術(shù)時(shí)機(jī),在治療高能量Pilon骨折應(yīng)用MIPO技術(shù),均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是手術(shù)治療高能量Pilon骨折一種比較理想的選擇,尤其是高能量PilonⅡ型骨折。
[參考文獻(xiàn)]
[1] Ruedi TP,Allgower M. Fracture of the lower end of the tibia into the ankle joint[J]. Injury,1969,1(1):92-99.
[2] Olreud C,Molander H. A Scoring scale for symptom evaluation after ankle fracture[J]. Arch Orthop Trauma Surg,1984,103(3):190-194.
[3] Burwell HN,Charnley AD. The treatment of displaced fractures at the ankle by rigid internal fixation and early joint movement[J]. J Bone Jiont Surg Br,1965,47(4):634-660.
[4] Evan H,Lon S. Displaced Pilon fractures. An update[J].Orthop Clin Nor Am,1994,25(4):615-630.
[5] Calori GM,Tagliabue L,Mazza E.Tibial Pilon fractures:which method of treatment[J]. Injury British Journal of Accident Surgery,2010,(11):1183-1190.
[6] Dresing K. Minimally invasive osteosynthesis of pilon fractures[J]. Oper Orthop Traumatol,2012,116(2):532-535.
[7] Krettek C,Schandelmaier P,Miclau T,et al. Transarticular jiont reconstruction and indirect plate osteosynthesis for complex distal suprulondylur femoral fractures[J]. Injury,1997,28(suppl1):31-41.
[8] Tong D,Ji F,zhang H,et al. Two-stage procedure protocol for minimally invasive plate osteosynthesis technique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complex pilon fracture[J]. Int Orthop,2012,36(4):833-837.
[9] 陳大偉,李兵,俞光榮. Pilon骨折的研究現(xiàn)狀和外固定支架治療[J]. 中華創(chuàng)傷雜志,2013,29(10):1011-1014.
[10] Watson JT,Moed BR,Karges DE,et al. Pilon fractures:treatment protocol based on severity of soft tissue injury[J].Clin Orthp Relat Res,2000,(375):78-90.
[11] Borrelli J Jr,Catalano L. 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of plion fractures[J]. J Orthop Trauma,1999,13:573-582.
[12] Sirkin M,Sanders R,Dipasquale T,et al. A staged protocol for soft tissue management of complex pilon fractures[J].J Orthop Trauma,2004,18(8 Suppl):S32-38.
[13] Amorosa LF,Brown GD,Greisberg J. A surgical approach to posterior pilon fractures[J]. Journal of Orthopaedic Trauma,2010,(3):188-193.
[14] Blauth M,Bastian L,Krettlek C,et al. Surgical op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tibial pilon fractures:a study of three techniques[J]. J Orthop Trauma,2001,15(3):153-160.
[15] Liporace FA,Yoon RS. Decisions and staging leading to definitive open management of pilon fractures:where have we come from and where are we now[J]. Journal of Orthopaedic Trauma,2012,(8):488-498.
[16] Kellam JF,Waddel JP. Fracture of the distal tibial metaphy-sis with intra-articular extension:the distal tibial explotion fracture[J]. J Trauma,1979,19(8):593-601.
(收稿日期:2015-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