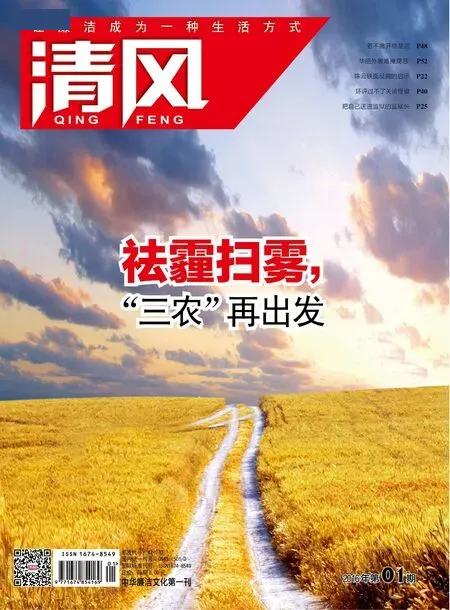湘西瀘溪縣“叫板”貧困不用嘴
文_本刊記者
湘西瀘溪縣“叫板”貧困不用嘴
文_本刊記者
馬王溪村位于湖南西部的瀘溪縣浦市鎮,據說原來叫螞王溪村,“螞”是螞蟥的螞。當地有個傳說,以前這里有一只千年螞蟥精,它吞噬資源,吸走人們的精氣,使得當地人的生活十分艱苦。對于湖南西部的絕大多數農村而言,似乎都有一只“螞蟥精”作祟,使得人們生活捉襟見肘,而這只“螞蟥精”就是貧窮。
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曾寫道:“湖南自古稱山國,連山積翠何重疊。”多山是湖南的一大特點,位于湘西的瀘溪縣更是如此,山明水秀風景奇美的另一面則是交通不便地勢崎嶇。“要想富,先修路”已經成為當地數年來的共識,交通不便,貧窮自然接踵而來。對于湘西的很多地方而言,貧窮仍然是當前最主要的難題。近年來,隨著國家扶貧力度的加大,地方政府窮則思變,一些農村也出現了新的生機。
國家級貧困縣里有個小康村
原來村子里的孩子是在一所廟里上課,一到冬天寒風似刀。現在村里建起了學校,有了現代化的教學設備,前兩年甚至給操場鋪設了塑膠跑道。
馬王溪村之所以不再是螞王溪村,因為他們已經趕走了那只“螞蟥精”。“去年我們村的人均收入是1.85萬元,州委書記夸我們是湘西第一村。”馬王溪村黨支部書記石澤林告訴本刊記者。
瀘溪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已經戴了多年,這成為當地的一塊心病。雖然是國家級貧困縣,經濟基礎薄弱,但無論是當地官員還是當地群眾都在圖謀思變。
石澤林早年在南方一個陶瓷廠打工,學到技術后,他就回到家鄉創辦了陶瓷廠,如今陶瓷廠已經成為村里的經濟支柱產業。“一個人富起來不算本事,要讓全村人都富起來才是真本事。”石澤林告訴本刊記者,這些年村里的變化可謂日新月異,原本村里家家都是土屋或木房,而現在全村基本都住進了兩三層的小洋樓。
村民們的經濟收入多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思維和視野也變得開闊起來。石澤林成為村支書后,在他的帶領下,一些村民也紛紛創業,搞養殖、種草莓、種桃子。有人先富起來了,其他人看著也眼紅,心里自然會著急。“大家都是兩個肩膀一個腦袋,他行我為什么不行?”謝龍生原本是在石澤林陶瓷廠打工,有了一筆積蓄后,自己開辦了生豬養殖廠,幾年下來,家里的收入明顯增多了,生活條件有了明顯改觀。據了解,馬王溪村這個人口只有1722人的村子去年的生豬養殖規模超過了1.2萬頭,而謝龍生的養殖廠在其中貢獻頗高。一種創富不服輸的干勁在村子里蔚然成風。
除了養殖業,種植業在馬王溪村也得到了極好的發展。草莓園、黃桃園、葡萄園、苗圃園等成網格狀分布在整個村子的公路兩旁。在村民的草莓采摘大棚內,剛成熟的草莓摘下來直接就可以吃。“純天然,無公害,絕對沒用過任何農藥。”村民告訴本刊記者,這是吸引游客的一大亮點。馬王溪村距瀘溪縣城二十幾公里,距辰溪縣城不到二十公里,距鳳凰也只有三十幾公里,水果成熟時吸引了一批住在城里的人前來采摘,為他們提供了一筆可觀的經濟收入。
相比起來,村子里變化最大的就是學校了。原來村子里的孩子在一所廟里上課,一到冬天寒風似刀。現在村里建起了學校,有了現代化的教學設備,前兩年甚至給操場鋪設了塑膠跑道。今天的馬王溪村早已改變了人們對湘西地區的普遍看法,雖然位于國家級貧困縣里,但卻獨樹一幟,成為“民富其實”的小康村。

村民在馬王溪村陶瓷廠上班
去城里,說走就走
“原來一年到頭也去不了縣城幾回,現在想什么時候去就什么時候去。”
馬王溪村幾十公里之外的潭溪鎮大陂流村目前有1820人,是一個相對傳統的農業村,村民多為土家族。村支書向常生介紹,目前村子里的年人均收入在3000元左右。椪柑是村子最主要的經濟作物,幾乎家家戶戶種椪柑,經濟收入主要源于此。記者采訪時正是椪柑收獲的季節,很多村民家中都堆著剛剛采摘回來的椪柑,等待來果商前來收購。
楊茶花今年62歲,家中有5口人,除兒子在外打工,其余家人都在家中務農。全家的經濟收入一方面靠農業生產和椪柑,另一方面靠兒子打工掙錢。楊茶花告訴本刊記者,她家每年能收獲椪柑2萬~3萬斤,這筆收入在2萬元左右。“原來一年到頭也去不了縣城幾回,現在想什么時候去,就什么時候去。”
如今,大陂流村有些人建了樓房,但也有人依舊居住在土家族傳統的木房子里。記者隨機敲開了一戶人家,卻發現外表看上去略顯破舊的木屋子里別有一番氣象——電視、冰箱、洗衣機等常用家電一應俱全。
在一處村民的屋子里,農家特有的火坑格外引人注目,柴火燒得很旺,老人正坐在火坑邊扶正火上的燒水壺。他叫向清選,今年68歲,兒子正值壯年,但卻因為抑郁癥住院,兒媳在廣州打工,三個孫子在村里上學。雖然經濟條件相對困難,但好在村委會為他們申請了醫療補助和低保名額。“雖然我們現在條件比別人差一些,但跟以前比還是好很多,至少不用為吃飯發愁。”向清選告訴記者,這些年無論是家里的椪柑銷售,還是兒媳打工的收入,都在增加,兒子雖然住院,但家里還是過得去。
大陂流村依山傍水,地勢崎嶇,很多房子都建在半山腰上,群眾生活非常不便。當地人說,以前他們吃水基本靠挑,照明基本靠燒。現在是電到戶、水到家,逢年過節樂哈哈。村支書向常生告訴本刊記者,由于地勢限制,很多房子建在半山腰,僅建房用的材料就很難運上山去。而從上面運東西下來更是不易,別的東西還好說,生活垃圾卻是一大難題。很多生活垃圾常年堆積無法下山,風一吹,各種塑料垃圾滿天飛。近兩年,瀘溪縣響應國家號召加大了對環境保護的力度,大陂流村也在住戶較集中的地方新建了垃圾池,用于回收群眾的生活垃圾,并由村委會出錢雇專人定時清理,居住環境比以往好了許多。
脫貧先要轉變思想
政府給建設好了基礎設施,修了路、通了水電,但最終還是需要自身努力改變村子的現狀。
就在本刊記者采訪時,湖南省扶貧辦工作組正在瀘溪開展扶貧工作。在瀘溪除了馬王溪村是發展相對較好的村子外,還有許多如大陂流村等發展一般,甚至發展更差的村子。馬王溪村與其他村子相比其實并沒有多少天然優勢,為什么它卻能脫穎而出,成為國貧縣里的小康村呢?
不可否認,近年來中國的農村發展取得了極大的成績,由于國家對于農村基礎設施的大力投入,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農村的生活環境更是明顯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諸多問題。農村發展中的空心化、土地拋荒等諸多問題也是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
日前就曾有學者表示,“走過一村又一村,村村城市;走過一城又一城,城城農村”,尖銳地指出了當前農村發展過程中盲目城市化的現象。而農村空心化現象更是日益普遍,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即是農村空心化引發的社會問題。
農村如何發展才是真的良方呢?馬王溪村村支書石澤林的一句話引起了記者的注意:“農村要發展,首先農村要有人。”農民富裕的途徑很多,外出務工是當前很多農民的現實選擇,但農民富了,農村卻并沒有富,農業并沒有得到發展,“三農”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相比之下,在湘西馬王溪村,當地的陶瓷廠創造了超過200個就業崗位,村里一些大戶的養殖基地、種植園都創造了就業崗位。“在家里就能就業掙錢,又何必去外地呢?”石澤林介紹說,2014年他們做過統計,僅村里相關產業發出的工資就將近1000萬元。
劉榮(化名)在馬王溪陶瓷廠上班,如今每月工資3000多,而且在本村上班還能兼顧種地。她早年喪夫,就是靠著在陶瓷廠上班的工資和務農的收入生活,而且還供了兩個兒子上大學,這在當地成為一樁美談。
“我們自己創造就業崗位,把村民留在了農村。”石澤林告訴本刊記者,村里有了人就有了生機,就會使村子富有創造力。政府為鄉村建設好了基礎設施,但最終還是需要村民自己努力致富。如今,農村建設中發展產業似乎并不鮮見,但馬王溪村卻有自己的亮點。自從石澤林當上馬王溪村村干部后,他定下了這樣一條規矩:村里支持農戶發展產業,但每戶發展的產業不能與其他人相同,而且必須嚴格按村委會的規劃。
也正是這條規矩,使馬王溪村的發展降低了很多風險。每戶只能發展一種產業,不能與其他人重復。雞蛋沒有放在同一個籃子里,遭遇某些意外因素時也不至于全村遭殃。此外,可以避免村子內部的惡性競爭,最大限度地團結整個村子。這一思路,在當前農村多地方采取“全村一鍋米,一煳煳到底”的現實背景下,非常具有借鑒意義。
馬王溪村曾經是貧窮落后的“螞王溪”,但短短十多年卻一躍而成為“湘西第一村”,這其中有政府幫扶之功,但更多還是村子自力更生之效。石澤林說,村子里曾是垃圾到處飛,賭博扎成堆。但是現在大家思想觀念變了,與其坐等國家來扶貧,不如自己來脫困致富。
2013年,石澤林當選為村支書后,他和村委會其他成員共同制訂了村子未來發展的“五年計劃”,計劃試圖在5年內將村民的年收入翻一番。“這個任務看上去非常艱巨,但是事在人為嘛。”石澤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