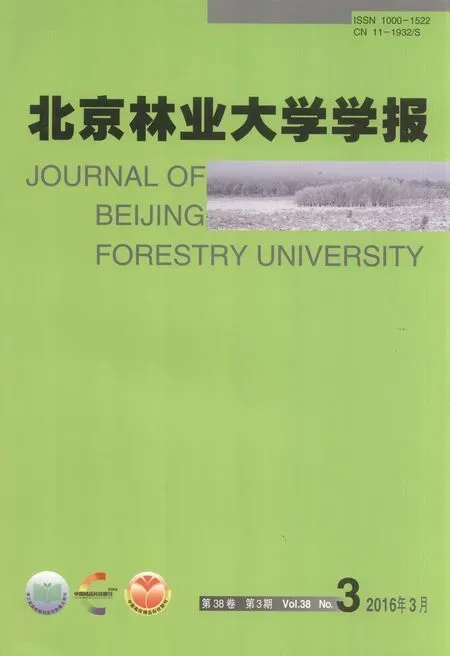注重鄉村文化記憶保護與傳承的景觀設計研究
——以貴陽花溪大塘濕地景觀設計為例
張蕾花,何嵩濤,徐英紅,王甜甜,馮鳳嬌
(貴州大學林學院)
注重鄉村文化記憶保護與傳承的景觀設計研究
——以貴陽花溪大塘濕地景觀設計為例
張蕾花,何嵩濤,徐英紅,王甜甜,馮鳳嬌
(貴州大學林學院)
文化記憶認同已成為城市現代化變遷中的世界性課題,拯救與活化普遍存在于保護名錄之外的富有集體記憶、維系地方文化認同感的鄉村場所,急需當下景觀設計研究者的重視與研究。以與鄉村生活區為鄰的貴州省貴陽市大塘濕地景觀設計項目為例,以文獻研究和實地調查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總結出注重鄉村文化記憶傳承的“記—探—尋—悟—憶”的設計思路和方法,對鄉村文化記憶的保護與傳承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鄉村文化記憶;保護與傳承;景觀設計
早在1964年5月,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簡稱ICCROM)在巴黎通過了關于歷史文物保護的第一個國際憲章《國際保護與修復憲章》,其中首次提出關于鄉村環境的文化保護:“文物古跡不僅包括單個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夠從中找出一種獨特的文明、一種有意義的發展的城市或鄉村環境。”[1]而強勢的現代化打破了原來相對封閉的地方文化系統的發展,導致產生“表層文化”現象,大量現存的、蘊涵著社區情感與集體記憶的歷史性場所正在遭受著前所未有的破壞[2],文化記憶認同已成為城市與鄉村現代化變遷中的世界性課題。
有效延續人們的歷史記憶與情感依賴,急需深層文化的召喚與回歸。一方面,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加強了文化記憶多種形式的保護與傳承;另一方面,處于保護名錄之外的富有集體記憶、飽含地方文化認同感的鄉村場所,卻處于被遺忘的角落,相比官方認定的、紀念碑式的建筑遺產或者成規模的歷史地段來說,地方性的記憶場所更具普遍性、多樣性,更貼近百姓的社會生活與文化情感[3]。這種以鄉村文化為主體的記憶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增加的時間價值和滲透的人文精神,構成了鄉村的精神和靈魂,不僅是個體在所屬文化群體與其場域內形成歸屬感的前提,更是獲得、保持、創新自身文化的前提,理應喚起學術界對這類文化遺存場所的重視。
關于“文化記憶”,揚·阿斯曼在《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一文中對其進行了界定:它是每個社會和時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圖片和禮儀儀式的總和[4]。此外,揚·阿斯曼在《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一文中,通過對交往記憶和文化記憶的對比,對“文化記憶”進行了詳細總結:以神話傳說和發生在絕對過去的事件為內容,以被創建的、高度成型的、慶典儀式性的節日或社會交往為形式,并以文字、圖像、舞蹈等媒介進行傳統的、象征性的編碼及展演的總和[5]。
而由于“鄉村文化記憶傳承”的景觀研究方面的文獻相對較少,目前還沒有針對“鄉村文化記憶”的具體概念,筆者通過大量的資料研究暫給其一個定義:“鄉村集體中關于過去共有的并將一致性和獨特性的意識建立其上的知識傳統,包括物質載體和精神載體兩個層面。”筆者于2014年12月主持設計了貴州省貴陽花溪大塘濕地景觀設計項目,本文以此為例,總結注重鄉村文化記憶傳承的景觀設計思路和方法。
一、“記”——文化記憶探源
花溪大塘濕地位于貴陽市花溪區政府東3 km的把火村(咸豐年間《貴陽府志》用此名[6])內(見圖1[7]),兩面山林一面墓林,濕地之水源自兩山之間的地下泉水,把火村民國初曾設置大塘鄉[6],花溪大塘濕地因此得名。該濕地面積4萬m2,位于清溪路東1.1 km、花溪福澤陵墓園南220m處。北鄰把火村,南鄰大塘寨。西北方向與花溪公園隔路相望。大塘濕地水位常年穩定,猶如一首老歌,靜默流淌,情深意長,滋潤著把火村全村552戶百姓,1 600多人。
無文字文化中,文化記憶并不是單一地附著在文本上,還可以附著在舞蹈、競賽、儀式、面具、圖像、韻律、樂曲、飲食、空間和地點、服飾裝扮、文身、飾物、武器等非文本形式之上,群體通過這種文本形式或非文本形式對自我認知進行現實化和確認[5]。而如今的與生活區為鄰的花溪大塘濕地所在地——把火村,群體生活方式是少數民族大雜居小聚居,以苗族和布依族為主,其中苗族占少數民族總人口的90%。把火村在空間、地點、樂曲、服飾、飾物、舞蹈等方面給予了濕地豐厚的文化底蘊和內涵,對鄉村文化記憶的保護與傳承方面的研究起到很好的基奠作用,所以把火村整體文化記憶探尋集中表現在如下3個方面。
(一)民族文化探尋——原始的圖騰崇拜與鮮活的儀式場所
首先,遠古時代,少數民族對魚龍文化有所崇拜,是最早的精神文化圖騰。地位上,它們都作為司雨之神而受崇拜祭祀;文化內涵上,魚和龍同為多子之物,都是古代民間乞子、多福之拜物。當今苗族的刺繡、蠟染、銀飾等即有以龍鳳、魚為崇拜物的主題樣式(見圖2[8]、3、4[9]、5)。
其次,從苗族服飾圖案符號所代表的文化內涵看,苗族服飾距今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他們將本民族的認同世代口傳身授,將流傳千年的故事、先民居住的城池、遷徙漂泊的路線等點滴一針一線繡進衣冠服飾,世代“穿”承,永不忘懷。另一方面,從總體來看,不僅保持著中國民間的織、繡、挑、染的傳統工藝技法,還穿插使用其他的工藝手法,如挑中帶繡,或染中帶繡,又或織繡結合,因而,苗族服飾被譽為“無字史書”和穿在身上的“史書”。現今把火村的苗族服式中亦有不同程度的展現(見圖2[8]、4[9]、6[10])。
除此以外,《苗族古歌》是苗族聚居區流傳下來的唯一非宗教典籍傳世記史詩。據史料記載,古老的苗族先民把蝴蝶媽媽——楓香樹看成是萬物的始祖(見圖6[10]),因苗族自古無文字,人們的婚姻戀愛等契約無法記載,便選楓樹刻木為證,即讓祖先為證。同時從《楓樹歌》的記述看,苗族也將楓樹視為一種神靈信仰,如以楓樹為中柱,就象征祖先與家人同在,保佑后代興旺發達,平安康樂;田坎邊栽種楓樹,以求五谷豐登;村寨周圍遍植楓樹,以保佑全寨安寧等,所以,村民每到新的地方必須在田坎、村寨周圍種植楓香樹。而現今把火村不僅暗藏古老神秘的楓樹神話,也有鮮活的實物代表——濕地南側的楓香古樹,不僅有著百年歷史,更重要的是在諸多變遷中較好地保存下來,還伴有藤枝纏繞(見圖7、8),有“藤纏樹,連理枝”之說,象征并保佑著花溪把火村“男女喜結連理”的美好姻緣[11],并有許多青年在此許愿。
(二)山水文化探尋——神秘的意境傳說與溫潤的自然稟賦
花溪大塘濕地西北、東南臨山,如同聚寶盆地,呼吸自然之氣;水域源自山下泉水,水位常年穩定。遠望:入口西北方向700m處,兩山夾道(見圖9),猶如龍門,初道窄,行70 m,豁然開朗。漸觀:漸行約300m,近現土地屋舍,時有灰鶴起舞;東北又行400余m,阡陌交通,野鴨嬉戲,濕地隱現。近尋:西北緊鄰花溪福澤陵園(見圖10),梵音裊繞,檀香彌漫的襯托,更能體會到大塘濕地獨有的美。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視線處理上,把火村注重空間組織作用,而在選址中,則更偏好隱藏和屏蔽性結構。這也較好地證明了人們親近山水、自然的同時,也有一定的景觀吉兇意識。另外,由于把火村位于苗嶺中部“大成山脈”東側的盆地中,而“大成山脈”是貴州省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創新的重要基地,所以把火村本身就富有濃厚的文化氛圍。
(三)生活文化探尋——寧靜的田園氣息與緊密的家族鄰里
濕地早期水質清冽,盛產鯉魚。當地居民多以漁業為生。濕地邊緣鄉土植被茂盛,常綠樹、落葉樹兼備,馬尾松姿態古奇,刺楸、構樹整體粗獷而充滿野趣,夏季漫山的楊梅如披了紫霞一般,濕地與林坡交界處蜿蜒的小道若隱若現之余,還隨時伴有野鴨嬉戲、灰鶴起舞的驚喜。時有追尋《桃花源記》之感,又有《桃花源記》不及之處……其潛在的美純粹、寧靜,無時無刻不滲透著原始本真、震撼人心的力量。
同時,把火村內少數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生活方式及文化差異,使生產技能、生活飲食習慣、風俗、語言信仰等方面展現出一定的傳統和文化差異,村落中各民族關系由最初的建構、相繼的發展變化,到最后的民族關系經驗積累、建構與維護,展現出較為和諧、融洽、團結、友好、協助、穩定的家族鄰里關系。
二、“探”——文化記憶的“矛盾”認知
筆者親臨現場,為把火村淳樸靜謐的自然人文氣息感動的同時,也時時刻刻感受到場所內部面容時有傷痕、略顯憔悴的身影:濕地岸邊時常伴隨部分坍塌情況,其水質亦常年受到生活污水及農藥殘留等的污染,并出現部分斷流;場址周邊有殘破的建筑物和其他構筑物,空間植物單一,略顯孤寂。
以Massey等為代表的一些地理學家認為,場所的獨特性不僅僅源自場所內部,也反映在它和外界的獨特聯系中[12]。將大塘濕地置于內外環境對比中,不難發現,場所獨有的特殊性恰恰促成了以下3大矛盾的形成。
(一)“靜”與“寂”的矛盾
一方面,大塘濕地作為花溪把火村唯一的濕地景觀,有一份不同于市中心濕地公園的遠離鬧市的“靜”,又有一份家有良田菜畦、空漫鳥語花香的安寧與和樂;另一方面,該場地正北及西北方向緊鄰花溪福澤陵園,其莊重、肅穆的墓園氛圍,給場地閑適、純粹的自然特質提出了挑戰。如何更好地展現場地本身的閑適與寧靜,而不被福澤陵園的孤寂與墓氣掩蓋?
(二)“悠”與“游”的沖突
一方面,場地有其本身的閑適與寧靜,時有灰鶴起舞,又有野鴨嬉戲;另一方面,隨著游人駐足停留日漸增多,難免會受到開發的影響。如何使游人在得到放松、愜意體驗的同時,而保持場地不被開發破壞,仍能較大程度地保持原有的自然與本真?
(三)“根”與“枝”的疏離
把火村有漢族和苗族、布依族等少數民族,雖然少數民族人數居多,但少數民族文化漸被漢化和疏離,如何重拾本族文化,有效幫助少數民族文化走向回歸,是另一個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總之,面對諸多矛盾與沖突,如何在符合自然規律、滿足社會功能、遵循生態原則的同時,更藝術性地解決文化記憶的傳承問題,我國建筑學家馮紀忠先生給出了答案:“文化因素,使環境超越自身的物質結構和基質,形成一種潛在的價值。”[13]這也恰恰成為解決場地內外環境矛盾沖突的堅實后盾和有力突破口。
三、“尋”——傳承原則與思想
針對場地的諸多挑戰,在盡量不破壞原場址的基礎上,如何化“憂”為“喜”,以更好的姿態傳承和發展原有的文化記憶。諾伯格·舒爾茨曾提出“場所的變遷不可避免,而回應的方式就是創造性的再詮釋”[14]。因此,建構“新”的文化記憶成為本研究最核心的問題。
而創造性的再詮釋需要謹慎對待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去做,可以保證能夠有效去除表層符號堆砌等自然文化入侵方式,多留一些自然遺產?阿爾多·羅西曾強調,地域歷史和記憶對于已知與未來環境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意義,如此才能留住自然與文化歷史的根,才能在有限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挖掘、提煉,進而最終結成文化精華,這才是“文化記憶”傳承的推動力與核心價值。而地域歷史和記憶又根植于生活,生活化的景觀內容是文化景觀里最真實、接地氣,最具活力、且有時效的部分。因此尋求生活化的景觀不僅可以巧妙地融合自然,亦可以彰顯對自然的敬畏和人文關懷。所以對地域歷史和記憶的尋求點,不僅要關注當下風景的使用性,更要關注未來的可持續性,而前者更多關注景觀的情感氛圍,后者相應更關注思想意義,兩者都是“文化記憶”保護與傳承的關鍵點。如此這樣才能經受住現代人和未來人們的檢驗。
基于此,筆者認為設計應該遵守以自然為根,以人性化需求為本,以文化為魂的原則與思想。原場址是尋求文化記憶的見證,也是構建“新”文化記憶最好的藍本。所以,場址調研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以對原住居民探訪為主,對場地早期風貌有所總結;另一方面,調查場址現有風貌。這兩方面分別在自然、人與文化之間有不同程度的展現,只有尊重自然基理,以人性化需求為本,以場地原有的文化為魂,在“踏尋”原有文化記憶足跡的同時,才能進一步獲得相應的感知與體悟。
四、“悟”——建構新鄉村文化記憶
筆者通過運用更多關注景觀情感氛圍和思想意義的“情景化景觀”表達方式,將抽象藝術作為形式語言,在情感和思想上,通過藝術形式去表達對該場地的理解。以更忠實于場地本真的態度和方式去解決問題、創造生活。
(一)場地基理之“悟”——鯉魚形
一方面,結合上述文中所述的傳承原則和思想,該場地以自然“天地”為根,以人性化需求為本,以文化為魂,對應如下:①天地——濕地現有自然水域、沼澤地、人工池塘、農田、桃花林、濕地植物及建筑等土地類型(見圖11)。②人——濕地早期水質清冽,且盛產鯉魚。人們多以發展漁業為生。③“神”——少數民族早期對“魚”有所崇拜(見圖3、4[9]、5)。另一方面,筆者對現有場地進行地形繪制時(見圖12),發現地形基理形似鯉魚,如鱗、背鰭、胸鰭、腹鰭和尾鰭等意象凸顯。這與當地早期盛產鯉魚、漁業發達及魚的圖騰崇拜關系緊密(見圖4),正是構建新文化記憶的源泉。
(二)把火村入口之“悟”——龍門
場地入口西北方向700m處,兩山夾道,猶如龍門,初行窄而后開朗(見圖9)。以把火村入口為界,入口外展現的更多為喧鬧的城市生活場景,入口內有一份不同于市中心濕地公園的遠離鬧市的“靜”,又有一份家有良田菜畦、空漫鳥語花香的安寧與和樂。更有兩條盤龍似的山脊作為入口屏障,一動一靜之間,恰有入世出世之感。
(三)場地功能之“悟”——休憩
大塘濕地作為花溪把火村唯一一個濕地場所,不僅是周邊村民日常休息的地方,清明時節,也是去福澤園祭祖拜佛的香客駐足停留之地。由此,更加深刻地彰顯了場地本有的寧靜氣質:人們不僅可讓身體得到短暫休憩,更可以深刻表達內心的感恩與釋懷。
(四)場地氣質之“悟”——禪意
該場地正北及西北方向緊鄰花溪福澤陵園,作為高原祭祖拜佛圣地,整個園區重巒疊嶂、梵音裊繞,檀香彌漫、綠樹成蔭、鳥語花香的氛圍,更為大塘濕地增添了一份獨有的靜謐,也為人們帶來一份更近乎修心的體驗之美。
基于此,結合對把火村整體文化記憶探尋的3個方面,即具有原始圖騰崇拜與鮮活的儀式場所的民族文化,具有神秘意境與自然稟賦的山水文化和充滿田園氣息與友好的家族鄰里關系的生活文化,筆者探尋到村內集中表達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是對自然、靜謐、和諧的向往與需求,由此筆者確定了“鯉魚躍龍門后的憩與禪”的主題定位(見圖13)。這不僅是苗族對古老始祖文化保平安、祈幸福的精神寄托,而且也最大程度地符合大塘濕地景觀獨有的靜謐氣質,有利于以立體的方式展現并傳承當地特有的文化記憶。
五、“憶”——新鄉村文化記憶的升華
(一)山水的禪意體悟
側線處的一池加魚脊處的三山(景山、鏡山、凈山)(見圖14),位于一池“大塘流鯉”(見圖14)的較高處,沿鯉魚感覺神經最敏感的側線部位由西向東依次排列,是游人階段性感官體驗(豁然—漸佳—迷離—曲幽)(見圖15)駐足之處。
(二)道路的禪意體悟
胸鰭、背鰭、腹鰭、臀鰭、尾鰭處——鰭形思步道,作為濕地內部唯一游憩道,為盡量保護濕地內部環境,場地內沒有設車行道。木棧道時而接近草地,時而穿越林中,又或瀕臨水域,或跨越濕地曲幽,尾鰭處的思步道對面即為瀑布景觀——九天銀河,山水由上而下,恰如大塘之水天上來,又如鋰魚躍龍門后,“神龍”擺尾,重新潛入濕地的特寫鏡頭。其景觀體驗由東向西依次為:曲幽—迷離—漸佳—豁然,與上述“一池三山”的景觀體驗完全相反,于不經意間完成了人世頓悟的感官體驗。同時與大塘回廊以及場地原有的自然小道構成完整的步行系統(見圖16~21)。
(三)建筑景觀的文化追憶——點睛之“風荷樓”
風荷樓位于景山處,幽曲之間,踏級而上,或偶遇農場,或漸入佳境,入口平淡隱現,與道路喧鬧隔離(見圖22);同時以蓮花為山形基底,與佛意相通,寓意風調雨順,因荷諧音為“合”與“和”,寓意少數民族大融合及生活和睦和美,是苗族始祖文化的追憶與傳承。其建筑樣式源于苗族獨有的民居建筑——吊腳樓,是在對傳統文化挖掘、傳承的基礎上再創新。作為濕地“鯉魚”的點睛之筆,也是濕地的核心建筑景觀,不僅可眺望濕地風景,更具備文史館藏、交流功能,是村民和游客舉行儀式等集體文化活動場所(見圖23),有效保證了儀式在空間上的群體聚合性。
(四)小品與植被景觀的文化追憶——腹鰭處的古楓香及如意亭
如意亭與古樹楓香對望,此處的楓香古樹本身不僅有著數百年歷史,還伴有藤枝纏繞,有“藤纏樹,連理枝”之說,象征“男女喜結連理”的美好姻緣。人們在品味農家鄉野之余,坐在如意亭下,回望楓香古樹,不僅可以隨時尋味祈禱,還能融入到傳統民俗氛圍和活動中。
六、結 論
本方案在完全保留原濕地的綠色和藍色基底的基礎上,凝練出魚型概念:沿魚側線和魚脊,布置一池三山,沿胸鰭、背鰭、腹鰭、臀鰭、尾鰭有效提煉出鰭形思步道,并將魚首作為整個場地的文化活動中心,而魚目處布置濕地的核心建筑景觀,也是構建把火村新文化記憶的核心景觀載體,起點睛之用。整體用藝術的形式巧妙解決了場地本身矛盾沖突及根本的文化記憶傳承問題。并且以富有民族特色的圖騰——“魚”為文化核心,通過現實語境里的再詮釋,使歷史傳統精神內涵得到延續和發展的同時,也建構了該地特有的新的文化記憶。與此同時,通過對其他儀式和神話的調查、保存和傳承,可以進一步輔助鞏固并傳承集體認同,并由此保證了文化意義上認同的再生產,即新文化記憶的建構與升華。籍此方案,探索注重“傳承鄉村文化記憶”的景觀設計課題的方向。大塘濕地不僅是緊鄰鄉村生活區的文化聚集場所,同時因其三面山林環抱的自然特質,并富于少數民族早期魚龍文化、苗族始祖文化及佛教文化的精神,所以它也是人類在森林文化生活傳承方面的一個微觀展現。而當今林業發展的研究以森林功能、社會功能、生態功能為主,對其文化和精神功能方面涉及較少,鑒于此,筆者希望在森林文化和精神功能表達與傳承方面,為林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鑒。
[1] 朱蓉,吳堯.城市·記憶·形態:心理學與社會學視維中的歷史文化保護與發展[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3.
[2] 陸邵明.記憶場所: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新趨勢[C]∥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廣西壯族自治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人民政府,中國城市規劃學會.2012城市發展與規劃大會論文集.北京:《城市發展研究》編輯部,2012:8.
[3] 陸邵明.拯救記憶場所建構文化認同[N].人民日報,2012-04-12(23).
[4] 姚繼中,聶寧.日本文化記憶場研究之發軔[J].外國語文,2013(6):13-19.
[5] 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M].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6] 花溪區地方志編撰委員會.貴陽市花溪區志[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
[7] 百度地圖.貴州把火村[EB/OL].[2016-01-19].http://map. baidu.com/?newmap=1&ie=utf-8&s=s%26wd%3D&qq-pfto=pcqq.c2c.
[8] 中國文化產業藝術網.苗族刺繡幻化多彩[EB/OL].[2016-01-19].http://www.cnwhtv.cn/2012/0229/6045.html.
[9] 中國行業信息網.貴州苗族特色蠟染[EB/OL].[2016-01-19].http://www.cnlinfo.net/info/56735390.htm.
[10] 蝴蝶媽媽與苗族起源[EB/OL].[2015-12-27].http://blog. sina.com.cn/s/blog_698b430101012g5b.html.
[11] 楊正偉.試論苗族始祖神話與圖騰[J].貴州民族研究,1985(1):51-59.
[12] MASSEY D B,JESSP.Place in theworld?places,cultures and globaliza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1-4.
[13] 馮紀忠,王伯偉.舊城改建中環境文化因素的價值和地位[J].建筑學報,1987(10):44.
[14] 王燕飛.大學校園景觀與場所精神[D].南京:南京林業大學,2009.
(責任編輯 孔 艷)
Landscape Design Em phasizing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 M emory: Taking the Design of Datang W etland in Huaxi,Guiyang as an Exam ple
ZHANG Lei-hua,HE Song-tao,XU Ying-hong,WANG Tian-tian,FENG Feng-jiao
(College of Forestry,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550025,P.R.China)
The identity of culture memory has become a global issue in the transition of urban modernization,saving and activating the rural areas that are rich with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strong emotional attachments to ordinary people but normally not registered in the protection list of cultural relics,is badly in need of attention and research from the current landscape designers and researchers. Taking the landscape design project of Datang Wetland neighboring of a countryside living area in Guiyang City of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and combining literature research wit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e,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design ideas and methods emphasizing the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 memory,i.e.,a loop of from“remembering to exploring to looking for to realizing and lastly back to remembering”,owing a certain
ignifica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memory.
rural culturememory;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landscape design
TU986.2
A
1671-6116(2016)-03-0021-08
10.13931/j.cnki.bjfuss.2016004
2016-02-19
張蕾花,碩士。主要研究方向:景觀設計實踐與理論。Email:zhangleihua@126.com 地址:550025貴州省貴陽市花溪區貴州大學林學院。
責任作者:何嵩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山地景觀規劃與設計。Email:hesongtao@126.com 地址:550025貴州省貴陽市花溪區貴州大學林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