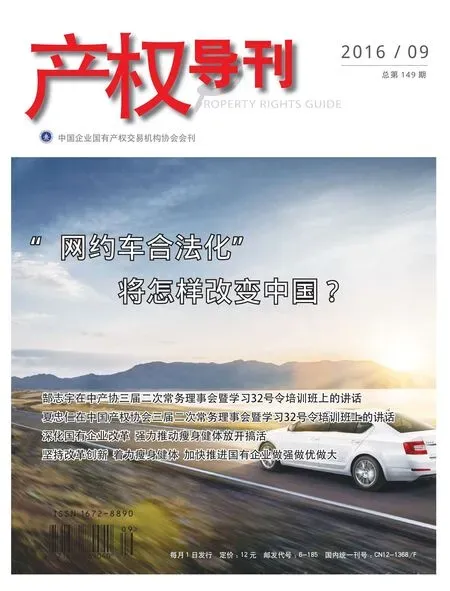當代中國收入差距治理研究
◎ 劉長軍(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100101)
當代中國收入差距治理研究
◎ 劉長軍(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100101)
古人云:“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今人曰:“經濟學不只要研究總產出水平,而且還要研究有關資源如何配置和財富分配的廣泛程度。”由此可見,收入差距問題是古今中外共同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本文旨在考察當代中國收入差距現狀,并對其做深刻的元哲學思考,以便有效規避當下收入差距困境,順利構建和諧社會。
1 我國當前收入拉開差距的分配現狀
改革開放之前的20多年時間里,在我國分配領域呈現出高度平均化特征:從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來看,改革前夕城鎮內部的基尼系數大約為0.16左右,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為0.22左右。這表明我國分配領域的收入差距,遠遠低于同期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基尼系數(0.34 ~0.43)①。
但是,改革開放之前重公平輕效率的平均主義原則,忽視了能力與收入之間相關聯的公正性要求,忽視了付出—獲得之間的激勵效應,由此抑制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社會財富的大量增加,導致了經濟的低效率和人們生活的貧困化。無庸置疑,我們的改革開放就是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觀念主導下,打破這種較為嚴重的平均主義的分配格局,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由此一來,我們的收入分配就實現了從平均主義到收入拉開差距的變化。因此,我們應該看到在人們承受范圍之內的收入拉開差距(適度的從而保持在人們可承受范圍內的差距)的積極意義,因為這正是改革過去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的初衷和我們要達到的目的。
追根溯源,在分配方式上,既存在按勞分配,也存在按技術、資本、管理等要素投入數量及其產生的效率進行分配的方式,分配方式上的多樣化,以及個人的能力、體力、智力差異,必然產生一定的收入差距。從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來看,1995年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為0.34,比1978年的0.21上升了13個百分點,同期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為0.28,比1978年的0.16上升了12個百分點。從我國居民財產分布與財產收入上來看:從無“產”到有“產”、從部分人有“產”到全體居民有“財產”、從較少“財產性收入”到擴大群眾財產性收入。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30多年的時間里,我們打破了絕對平均主義的束縛,在市場競爭與“勞”“酬”相統一中合理拉開了收入差距,實現了從高度均等化到明顯拉開收入差距的轉變。
2 警惕無序性收入差距
在學界看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農業經濟到工業經濟的轉變過程中,雖然“中國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別雖然持續擴大,但仍然大致適當,沒有發生兩極分化,無論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都不存在。”②但與此同時,在通過自己的天賦、才能、勤奮等富起來的合理與合法形式之外,我們要警惕當下無序的收入差距問題,我們要看到腐敗收入、內部人控制、設租尋租、壟斷性收入、集團消費轉化為個人消費、偷稅漏稅、走私販私、制假販假、假冒偽劣商品等非法非正常經濟行為。它們游離于市場經濟的灰色地帶,導致了我國居民無序的、非正常擴大的收入差距,帶來了諸如貧困、社會沖突、階層分化、低收入者享受不到改革開放的成果等一系列后果,甚至引起了人們懷疑改革的正當性。
各種非法非正常收入在當下中國的大量滋生,歸根結底是改革不到位、不完善的結果,是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制度缺陷的產物。從轉軌時期二元體制運行的角度來看,雖然我們確立了市場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但有時計劃在資源配置中的調控作用過大,因此,新舊體制之間難免出現錯位與缺位現象,甚至權力對資源進行強制調控過程中,出現權錢交易現象。但是從哲學的高度來看,對于有著濃厚的封建底蘊而又跨越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中國來說,在發展帶有“資本”的市場經濟道路上,我們既存在著資本主義國家早已經消除了的等級、特權和官本位現象,存在著公共權力與私人資本聯姻、公共政治與私人經濟結盟的現象,也存在資本主義國家未能解決也不可能解決的形式自由、形式平等這雙重問題,因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走的格外沉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總而言之,雖然“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其所仇的其實并不是富起來的目標與內涵(內容),而是富起來的途徑與手段(形式)”③,但是,隨著非法非正常收入數量的增長,以及這種非法非正常收入只是集中于少數高收入階層,并且規模及其對居民收入差別的影響日益加大,導致部分居民不但享受不到改革開放的成果,而且承擔了額外的改革開放的成本,導致財產占有分化加劇,導致人們仇富、仇官等心理失衡,從而給和諧社會的建構埋下了隱患。

3 協調收入差距無序化的元思考
毫無疑問,針對改革進程中過大的收入差距,特別是針對超過了人們的承受能力,引起了人們心理上產生不滿的非法非正常收入差距問題,我們要在注重效率從而做大蛋糕的基礎上,更加關注公平問題。
公平問題是社會主義應有之義。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④胡錦濤指出:“要通過發展增加社會物質財富、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過發展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不斷促進社會和諧。”⑤這昭示著,沒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豐裕,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也不可能最終實現社會主義本質所要求的公正與和諧;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充裕而適時推動社會公平與公正,就無法調動人們從事生產和創造財富的積極性與熱情,因而也就不可能實現生產力的發展。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本身就包含了關于和諧社會財富創造與財產利益關系協調之間的辯證關系問題,它從原則高度為財產利益關系的協調指明了方向。
社會主義社會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目標,主要體現在我國經濟關系中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上,也就是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上。如果說,市場經濟中非公經濟,以及按要素分配方式主要發揮著拉開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加大貧富懸殊的作用,那么,公有制經濟與按勞分配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保證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進而發揮著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因此,我國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就為全體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我國按勞分配法律主體地位的確定和為大多數社會成員所接受的事實,既保障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合法收入共識,也取締了非法非正常收入的社會生長土壤。
當然,我們也要批判兩個錯誤性認識:其一,收入差距與收入差距擴大問題系改革之過,因此我們要重走“老路”——絕對平均主義;其二,收入差距與收入差距擴大問題系制度使然,因此我們要走“邪路”——西方私有化之路。針對過去平均主義的“老路”,鄧小平曾經深刻指出:“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人民生活永遠改善不了,積極性也永遠調動不起來。”⑥同樣,針對中國走資本主義“邪路”的危害,鄧小平也一針見血地提出:“在中國現在落后的狀態下,走什么道路才能發展生產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⑦“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⑧事實上,收入差距及其擴大化問題不是改革之過,而是改革不到位甚至缺位所帶來的“副產品”。因此,繼續深化改革,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從而形成解決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的物質基礎的同時,加強法治型市場經濟建設,取締非法非正常收入,“建立起既有市場機制的基礎作用,又有政府有效宏觀調控的經濟,收入差距就可以逐步走向合理化。”
總之,我們既要理性看待改革進程中收入差距的合理性,也要警惕“部分的收入差距擴大是無序的,是與市場化改革進程相悖的,需要通過包括政治改革在內的改革深化來糾正的。”⑨只有從經濟發展、體制轉軌、政策調整、收入再分配等幾個方面入手,繼續深化體制改革,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也與之相適應的政策措施,創設機會均等、公平競爭、合理調節收入差距的體制與機制,才能有效規避無序差距問題。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中國農村公共財產治理研究(14XKS046)”的階段性成果)
[1] 趙人偉、李實.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及其原因[J].經濟研究,1997,(9).
[2] 陳宗勝、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對居民收入差別的影響及其經濟學解釋.載高培勇主編.收入分配:經濟學界如是說[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3] 劉榮軍.財富、人與歷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鄧小平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 鄧小平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鄧小平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鄧小平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 趙人偉等主編.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