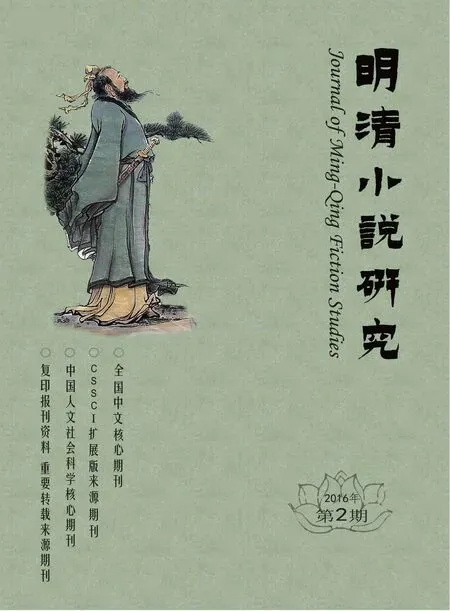以“花界提調”之名論晚清上海都市文人的另類話語空間
·李 默·
?
以“花界提調”之名論晚清上海都市文人的另類話語空間
·李默·
摘要花榜評選是文人熟知的狹邪娛樂,而“花界提調”則是文人們從古至今樂于扮演的娛樂角色。然而同樣是這個名號,在晚清上海租界報人李伯元及他的同好們身上包含的權力結構和價值體系卻截然不同。其不再從屬于傳統士大夫文化,而是跳脫出來融匯到現代化和半殖民地化的都市文化中。它所“提調”的不再是對雅妓名士的風月游戲,而是一只手伸向全新的現代都市狹邪文化加以描摹,一只手去向廣大的內陸來客加以介紹和勸戒。而在這微妙的一來一去之中,晚清上海的李伯元們悄無聲息的取得了自己在新興現代都市的另類話語權。
關鍵詞花界提調李伯元《游戲報》狹邪文化
1897年6月,李伯元創辦了《游戲報》,并且一炮打響。《游戲報》最初走紅于何時,具體已不可考。但是就已有資料可以知道,自李伯元在《游戲報》上舉辦花榜評選以后,其報紙銷量飆升,“花榜揭曉之日,就本埠一隅而論,初出五千紙,日未午即售罄,而購閱者尚紛至沓來,不得已重付手民排印,又出三千余紙,計共八千有奇”①,數量一時甚至超過了《申報》。李伯元就此站穩腳跟,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新式的職業文人。也正由于《游戲報》以嫖界為核心的內容旨趣,李伯元也被冠以了“花界提調”的名號。
在對這一類文人身份的轉型研究上,稿費制度的建立、報紙媒體新的形式和科舉制度的廢止都是文人在上海都市環境中職業化不得不考量的問題,當然也有了相當的研究。然而如果我們以李伯元這個個體為例,當他科舉失利來到上海,在擁有稿費、報紙等新的事物的同時,他同時也面臨著一種“失去”,他原先所身處的階層在傳統中國所擁有的不言自明的文化優勢在上海近現代的都市環境里變得不再明顯。稿費所代表的經濟規律和報紙代表的新的都市文化需要和趣味取代了文人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的生存邏輯和服務對象。一定程度上,我們或可戲稱為另一種從廟堂到廣場的變化。但是在新文化運動甚至是新小說運動都還未到來的時候,新的文化環境中李伯元們如何面對這種“失去”,如何以一個底層的傳統文人的身份在都市中奪取話語權?或者換而言之他們如何為自己的表達同時創造經濟支持和某種合法性?
本文試圖從李伯元對上海租界狹邪文化的運作入手,探討他取得都市話語權的另類途徑。
一、知遇和回報——名士雅妓愛情背后的傳統文人話語
花榜評選并非李伯元首倡,“花界提調”也不是李伯元原創。自古以來從狹邪文本誕生開始,文人對于妓女的品鑒和排位活動一直未曾中斷過。唐代《教坊記》和《北里志》就已經有對當時名妓的小評,這種小評逐步發展漸漸變成了對名妓名錄的羅列和集合,最后變成一種排名和對比。到了明崇禎年間,據《板橋雜記》記載“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諸姬于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墻。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這時,花榜的評選已經頗有樣式和規模。而文人在這里顯然扮演的是為名妓揚名,執掌風月大權的伯樂。
到了19世紀后半葉,上海租界更是花榜頻開,“1877年有公子放所定上海書仙花榜,1880年有庚辰春季花榜、庚辰花榜特科。1881年辛巳春季花榜、秋季花榜。1883年癸未秋季花榜、癸未冬季花榜。1888年戊子夏季花榜。1889年書寓花榜,曲中花榜”②。這一系列的花榜都是由當時的洋場文人主持,以宴請詩詞為形式,個別文人主導,小規模的傳統樣式的評選,也捧紅了許多早期進入上海租界的妓女。
縱覽這些花榜評選,無非是一種文人的狹邪游戲,以游戲筆墨為形式,考評吹捧名妓為消遣。以此為比較,在狹邪文學類型中諸多雜記、畫舫錄、冶游錄記載妓女的體例形式也都與花榜筆墨相差無幾,基本都是名妓名號加上贊詞并添以軼事,都是文人對妓女的品鑒,所以花榜評選在相當程度上很能代表狹邪文化的文學生產方式。而正是這一游戲筆墨縱情狹邪的文學生產卻包含了傳統士大夫政治生活中的權力結構和價值體系。
一方面,士大夫們將花榜與政治生活人才選拔同構,在一種戲仿中規劃理想的政治生活。
在《花月痕》中,當文采風流又身攜官職的韓荷生看到教坊司有欠公平的花選名次以后,大發牢騷將花選名單按照自己的標準改過一遍,從而使得主角之一的劉秋痕從第十變成了花選狀元。而這一舉動所蘊含并非因為男女情愛的萌發,而是韓荷生單純從自身士大夫的道德審美標準出發,對劉秋痕的才貌所遭受的不公正評價進行了翻案。在《花月痕》的世界里,名妓的地位的高下取決于士大夫世界的標準,所以當韓荷生改過花選以后,小說言道“數日之間,便轟傳起來。看官,你道那教坊司敢不更正么”③。這種對明珠蒙塵的翻案,對名妓的賞識,形成了一種我們或可以稱之為“知遇之恩”的權力結構。我們可以看出這一結構實際上是來自士大夫的對自身政治命運的一種理想。《花月痕》第二回提到主角韋癡珠時說他“文章憎命,對策既擯于主司,上書復傷乎執政”④,而后來飛黃騰達的韓荷生此時也自況“淪落天涯,依人作計,正復同病相憐也”⑤。所謂韋癡珠擯于主司不正是后來教坊司對劉秋痕貶低的前奏?而韓荷生賞識名妓劉秋痕又何嘗不是翻版了他自己依人作計得遇伯樂的事實?對現實遭遇的強烈不滿和失落,以及對幫助自己突破現實的外在力量的翹首以盼使得文人筆下朝廷人才政治和花榜評選形成了同構。無疑文人們在花榜選舉上的慧眼如炬正是他們對于開明政治本身的一種模仿和訴求。
從另一個方面,早期的花榜選舉的權力結構也反映了更大的外部社會階層事實。在政治人才選拔中被挑選的士大夫在花榜選舉中變成了挑選者。在士大夫世界中失意的文人,仍然處在在士農工商社會的頂端。比起教坊司的評選,士大夫和他背后深厚的文學素養和審美所作出的選擇顯然也更受名妓的青睞。在花榜游戲中,士大夫的所占有的主流社會文化的話語權享有絕對的權力。花榜以及其背后的名妓和狹邪文化不僅僅是一場筆墨游戲,由于它們被士大夫話語所掌控,以至于它們本身也融入到士大夫的價值體系和人生規劃之中。
失意的士人遭遇名妓,彼此賞識,在名妓的支助之下獲得宦途的成功,從而反過來救名妓于風塵。這個被無數次重復和變奏的文人名妓的愛情敘事,其背后起到巨大作用的社會階層權力事實其實被無視了。《花月痕》開篇即道“有幾個梁夫人能識蘄王,有幾個關盼盼能殉尚書”,魏秀仁以韓世忠和梁紅玉的典故無意中揭示了名士名妓的愛情背后士大夫的權力價值觀。韓世忠落魄時被教坊女梁紅玉賞識而支助,后得封蘄王,梁紅玉也成了正妻。但是魏秀仁卻說有幾個梁夫人能識蘄王,如若蘄王最后不能抗外族有功,那么梁夫人的一片愛重是否就不再有被贊美的價值了?在魏秀仁看來,這種愛情背后能否慧眼如炬識得英雄似乎才是其成立的根本條件。而關盼盼則明明對自己被逼殉情一事有著慘烈的反抗,但是魏秀仁卻一意曲解成一種愛情的證明。“有幾個”“能殉”?似乎不殉則不能證明名妓名士的愛情。這一敘事幾乎是直指古來青樓文學的本質,狹邪文化在士大夫的價值體系中的地位這時也才得以揭示。士大夫的宦途難免受制于朝政起伏,然而即使在失意之時,士大夫們崇高的社會地位仍然使得他們不斷設想可以求知己于江湖,名妓愛情和青樓文學的價值則由此而生。名妓的崇拜和理解成為了君主的賞識和理解的替代和補充。而這種替代也只是暫時的,其最終目的仍然是通過這暫時的沉溺和失意重新顯達于宦途。謝安“儲妓東山”的典故在狹邪文學中被頻繁運用是有其意義的,儲妓是人生低潮時的慰藉,而其后“東山再起”才是這個典故最終的指向所在。
在魏秀仁等一幫晚清“溢美”狹邪小說作者眼中,花榜評選的背后其實是對知己文化的尋找,是對士大夫政治知遇的一種戲仿,是士大夫完美人生規劃的一種寄托和補充。擴大化來看,青樓文學相當程度上也是如此,那些記錄名妓軼事的雜記和各種花叢冶游故事,實際上也是一次又一次相對隱蔽的花榜評選。他們將一個又一個符合士大夫審美的妓女形象提拔到士大夫的文學世界中來,寄托自己對當下現實和自身境況的慨嘆,何嘗不是文學層面的大型花榜評選呢?這些具象和抽象的花榜評選既反映了傳統名妓文化對士大夫文化深深的依附關系,也反映了傳統冶游娛樂在士大夫文學世界的真正定位。顯然此時,在當時的狹邪娛樂文化中,士大夫的話語權是無可置疑的。
然而這種傳統的權力結構和價值體系在《游戲報》的花榜選舉中卻不復存在了。
二、上海租界新式妓女與新興媒體
1897年李伯元創辦《游戲報》后,便在報紙上開辦花榜評選,據稱由洋場文人袁祖志列舉了評選凡例,分為藝榜和艷榜。袁祖志是老一輩上海文人,此時已是七十高齡,算是德高望重,并且也是花叢老手,曾在80年代力捧上海名妓李三三,使得李三三于“1882年壬午花朝艷榜得第二名”⑥。這一切仿佛和《花月痕》的花榜評選并無兩樣,恰似早期上海洋場文人花榜游戲在報紙媒體上的翻版。然而,緊接著的花榜結果卻引起了軒然大波,直接暴露了在都市娛樂文化場域中,傳統文人價值和話語權力悄然喪失的局面。而李伯元的三次回應,更是揭露了在花榜評選這一游戲背后士大夫權力位置和傳統價值被顛覆以后,他迅速應對并重新尋找文化場域話語權的心路歷程。
《游戲報》創辦伊始,即有《游戲主人告白》云:“本報每年出花榜四次,本年夏季準在六月出榜。諸君選色征歌,如有所遇,授函保薦,將生平事實、姓氏居里,詳細開明,以便秉公選取。”⑦但李伯元顯然似乎沒有遵守這則帶有民主色彩的承諾。1897年夏,花榜揭曉:艷榜狀元王秀蘭,榜眼金小寶,探花祝如椿,傳臚王春花;藝榜狀元張四寶。這一結果,直接引起了很多讀者的不滿。就《游戲報》刊登的回應和來函而言就可看到諸多端倪。《游戲報》43期和61期分別登出兩則文章《論花榜金小寶詞史不取狀元之故》和《閱本報名妓牢騷一則再申論之》,這兩篇都是李伯元回應讀者不滿金小寶只得榜眼而非狀元的文章。而第87期《游戲報》登出的《論滬濱書寓當以陸蘭芬為第一》又干脆提出了一名沒有上榜的妓女陸蘭芬應該是狀元。在第一篇文章中,李伯元承認金小寶的舉薦來函是最多的,變相承認了他其實沒有遵守自己許下的諾言。至于原因,李伯元在這兩篇文章中先是辯解金小寶過于高調,雖然保薦多但遭批評也多,而且他所評的狀元“含蓄而有味”,“如薄荷糕潔白可愛雖有一種清涼之氣其實非人人貪嗜之物”;金小寶“盡美而略近刻露者”,“如紅燒肉其一種沉浸濃郁之味令人個個垂涎”。說到底,李伯元對妓女的審美和道德要求仍然是傳統士大夫似的。所以金小寶并不符合李伯元對花榜狀元的心理預期。這恰如《花月痕》中韓荷生將花榜原本的第一名潘碧桃調到第六,理由是“美而艷。然蕩逸飛揚,未足以冠群芳也”⑧;把最后一名劉秋痕放至榜首,理由是“秋波橫慧,若態生姿……蓋其志趣與境遇,有難言者矣”⑨。兩相對比,理由何其相似,士大夫對清高含蓄內斂的贊美到李伯元這里依然一以貫之。
但是顯然李伯元發聲的狹邪文化圈已經和韓荷生發聲的狹邪文化圈完全不同了。韓荷生重評花榜以后,無人可以置喙。而李伯元的結果卻遭到再三抗議。
首先,花榜對于李伯元不再是對于韓荷生那樣的游戲意味。花榜結果遭到抗議這固然是李伯元還未能服眾的緣故。然而,古來花榜的舉辦起先必然有可服眾之人來首創或者定音,這個游戲才能進行。李伯元此時才來上海第二年,雖然有袁祖志為其壓陣,但是結果卻是他自己定的,不能服眾是必然。作為都市文化圈“新人”,花榜對于李伯元并非只是游戲,也是一種炒作手段,此時是他“有求于”讀者,而非讀者先天的服膺于他。顯然在悄然之間,兩者的權力位置由于花榜的意義變化而發生了變化。讀者如果有所不滿自然不怕李伯元這位初生牛犢。
第二,花榜在報紙上舉辦也極大的沖擊了原有花榜評選的權力結構。《游戲報》是商業報紙,而非同人刊物,經濟效益是其必然要求。所以即使李伯元已經是滬上名人,他依然不能完全無視報紙讀者的要求去吹捧他們所不喜歡的妓女。像袁祖志一樣集結一幫文人為了個人喜好捧紅李三三這類雅事是不符合李伯元的需要的。如果說以前的花榜選舉戲仿的是中國的封建士大夫政治,那么《游戲報》的花榜選舉則微妙的透露出一點“民主”政治的意味。選舉中并不存在一個德高望重者對花榜排名下論斷,而是通過投票的多寡來確定名次。事實上,由于報紙的覆蓋面廣,參與者并非小圈子的熟人,所以不同于小范圍文人內部的娛樂事件,也不再可能有某個人能對整個上海妓界和全部嫖客文人擁有絕對權威的話語權。每個人只能推薦或者批評自己熟知的幾個妓女。權力被分散了,單一的話語權被數量上占多數的話語權所取代。原本自上而下的“知遇”的權力結構無法支持報紙的結果取得權威,只能轉變為自下而上的民主的權力結構。而這種分散的意見必然導致一定的爭議,這也是“民主”的必然結果。從李伯元的兩篇回應來看,在短時間內他顯然并不是很適應這種爭議性,只是一味試圖自辯來說服反對意見。
除了以上兩點,最重要的還數引起爭議的金小寶、陸蘭芬等名妓的出現。事實上正是由于她們本身既受到眾多嫖客喜歡同時又不受傳統士大夫喜歡才會引發這樣的矛盾。這一局面實際上反映了作為士大夫文化生活補充和調劑的名妓和狹邪文化已然跳出其掌控的事實。
以“四大金剛”為首的上海名妓和傳統名妓一樣,她們的權力都大部分來自于追求她們的男人以及這些男人身上帶有的社會地位的標簽。當傳統妓女獲得這種權力以后,她們唯一可以運用這個權力的方法就是從良。傳統妓女的魅力來源于士大夫世界的欣賞,所以她們運用權力的方式只能是士大夫社會給她們提供的出路。在士大夫世界,杜十娘縱有萬金,失去了恩客只能自盡。而欣賞四大金剛的嫖客卻大多數不是士大夫,他們魚龍混雜,有旅滬過境的商人,有本地的市民,其中四大金剛客人的流動性是非常突出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中就有金剛上外地討債救助之類的故事,而從《九尾龜》也可以看出她們的客人一個接一個基本都是外地鄉紳和商人。來來往往的客人流動不息,這時又有誰是會靜下來如同《花月痕》《品花寶鑒》一般細細追求心心相印的紅顏知己呢?都市快速的節奏使得能抓住人的是那些顯眼的、耀眼的甚至扎眼的妓女。四大金剛從自我的肉體魅力起步,在都市的新聞競爭中不斷推陳出新博得大眾的眼球,她們可以運用的不是傳統士大夫所欣賞的才藝和品德,而是上海近代都市慢慢確立起來的對于“新”的崇拜。現代性對于新鮮感的追求,現代都市對于刺激和目光的需求,在四大金剛的形象上得到了非常完美的體現。她們的身邊有著各種流言蜚語,有一些的惡心程度令人難以忍受。比如金小寶擅長畫墨蘭,而《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竟然說她是因為長期生育得病而小便不禁時常尿床才有了這種傳言。但是她們卻沒有因此而黯淡,相反越多的故事新聞流言蜚語圍繞在她們身邊,她們就越吸引人。四大金剛在上海走紅了很長時間。我們可以說這些匪夷所思的新聞反而給她們帶來了更多的利益和權力。所以四大金剛的權力不來自于士大夫價值觀,也不來自于一個地方固定的對于她們道德水平的風評,她們的權力來自于現代都市的權力場。這種權力變得具有個人性和生產性。錢與身體的簡單交換漸漸被名妓們淘汰了,曾經杜十娘抱著一匣子稀世珍寶自盡正是因為她除了這些只有自己的身體,甚至于這些錢最終也只是為了以愛情的名義保全自己的身體,當這種保全落空時,經濟資本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上海低等的妓女們仍然保留著這種交換的模式,她們即使行騙也只是利用自己的身體,比如《海上花列傳》中的幺二利用拍賣自己的假的處女身來騙取趙樸齋的錢財。但是高等妓女們卻手段更加高超,她們拍賣自己的“青睞”。《九尾龜》中四大金剛之一的陸蘭芬只用一個媚眼就引得旁人對一個嫖客的極端艷羨,這固然仍有色相的成分,但更多的是陸蘭芬已經掌握的社會名氣成為了她的資本。她利用各種新奇觀感給自己不斷聚集都市影響力。而這些象征資本又可以轉化為經濟力量,從而支持她擁有更多的資源并有資格做出更多的選擇。如果說傳統名妓是單純的待估的商品只能等待救風塵,那么晚清上海名妓則更像是一個以自身身體為基礎將都市娛樂景觀不斷轉化生產為資本的文化工廠。而在這個意義上,四大金剛成為了對上海近代都市文化的最好詮釋。
當李伯元為代表的底層文人階層作為新人進入到都市文化場域的時候,他們愕然發現,這一文化場域中的權力位置早已發生了變化。他必須通過報紙這一商業媒體來曲折實現的士大夫的文化號召力。更重要的是,士大夫所秉信的價值體系不再受到都市娛樂文化的青睞,新的文化詮釋權反而被上海名妓四大金剛們所掠取。這時誕生的李伯元《游戲報》花榜評選所遇到的波折好似成了洋場文人尷尬文化地位的縮影。
三、“花界提調”——對都市娛樂空間的發現
當《游戲報》選擇舉辦花榜選舉的時候,絕不是和前人一樣簡單的試圖對名妓們給予“知遇”。當晚清上海的狹邪小說作者們將“四大金剛”們納入筆下時,他們也絕不是抱著和那些畫舫錄冶游雜記一般對蒙塵的明珠評鑒補遺的心情。在晚清的上海租界,進入近代都市的上海文人們不得不認識到,在這個全新的文化環境中,他們與生俱來的文化話語權已經受到了莫大的挑戰。文人社會和文人政治賦予他們與生俱來的象征資本在這里的優勢微乎其微。這一次,對全新娛樂文化環境的天然詮釋的權力被賦予了名妓。文人們要重新獲得對娛樂狹邪空間的話語權,必須與“四大金剛”們合作才能辦到。
而與名妓合作,與都市日常娛樂生活合作,則成為李伯元以及其后來人從自我心理層面最終突破了士大夫生活的價值體系和權力結構的一個重要途徑。李伯元、孫家振等等在傳統中國士大夫世界并不算成功的文人,也正是通過這種心理上的轉變,從而開始適應全新的都市文化,由此也試圖在其中給自己尋找一個全新的話語權位置。
參與報業基本上是晚清絕大多數狹邪作者們進入到上海文化圈的一個門徑。而報紙可以說是上海又一知名的文化景觀,同樣坐擁著巨大的資本力量。只是對這一景觀的競爭也同樣激烈。李伯元剛到上海便參與了《指南報》的創辦。這是一份大報,主要內容基本是自己撰寫與轉載其他中外報紙的新聞時要相結合。其創刊號上聲明其宗旨有六:“采萬國之精彩”,“擴朝廷之聞見”,“擴官場之耳目”,“開商民之利路”,“寄環海之文墨,以文會友”,“寓斯民之風化”⑩,透露出李伯元野心之一斑。然而,在當時《申報》和《新聞報》已經相繼揚名許久,各自劃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這兩份報紙都是外國人創辦,在報紙的經營方面可以說得心應手。如果說《申報》大體上是偏政論新聞,那么《新聞報》就是偏商業信息,各有專長。《指南報》創辦之初也邀請了《新聞報》的前主筆袁翔甫參與,以期一炮打響。但是過于大而無當的目標市場使得《指南報》很難在同樣領域超過前兩個報業巨擘。顯然并非一個響亮的口號就能讓一個底層士大夫在上海獲得名氣,站穩腳跟。于是在一年以后,李伯元又創辦了一份小報《游戲報》。這本身就可以看成李伯元面對新的文化環境的一種應對。
《游戲報》作為中國近代第一份小報,以嫖界新聞軼事為主要內容,首先決定它占據了別的媒體比較忽視的都市娛樂場所——妓院。晚清上海妓院經濟極其繁盛,有著與其相關的一整條娛樂經濟鏈條。茶館、煙館、戲院、書場、跑馬場等等當時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少不了妓女的身影。所以圍繞著妓院這一主題,《游戲報》獲得了許多相關的都市生活指南功能。譬如在1897年8月14日第52期登載的《英界煙間表》為代表對上海玩樂場所的詳細介紹,這一點正好充分利用了報紙信息的服務性,而這些信息是當時對上海市民日常娛樂生活十分重要卻又相對空白的部分。另外,上海作為中外新舊夾雜的都市,其實有許多為傳統中國文化無法接納的新興文化,大報往往抓住了外來的更高層次的文化變遷,而忽略的日常都市生活中這一變化的影響。而《游戲報》則是用十分認真的態度在為這一變化做著詮釋。例如66期的《學騙》、68期《記西夷論樂》、74期《觀美國影戲》、80期《論送節禮》、94期《論吃飯難》、100期《滑頭說》、115期《叉麻雀說》、125期《坐自行車密法》等等,一方面這些文章展示了上海中西合璧的繁華新穎的生活,另一方面它又提醒和教導讀者如何在這種新穎的日常中從容的生活。這時的李伯元其實已經開始從他所預期的勸誡世人的話語訴求轉向了服務市民的話語。
《游戲報》準確地瞄準了都市日常娛樂生活服務這一被無視的社會資本。而真正要占有這一空間內的話語權,幫助《游戲報》最終走紅,卻還是依靠了與上海娛樂業一大地標上海名妓的合作——花榜選舉才能一蹴而就。
前面已經提及這次花榜評選雖然取得巨大轟動,但是也備受非議。對此李伯元先后回應了三篇文章:43期的《論花榜金小寶詞史不取狀元之故》、61期的《閱本報名妓牢騷一則再申論之》以及91期的《游戲主人告白》。這三篇都放在頭版,風格卻很有不同,很可以管窺《游戲報》借由花榜走紅的過程。
《論花榜金小寶詞史不取狀元之故》一篇語言敦厚,提筆即寫聽聞有為金小寶陸蘭芬一輩抱屈者,復述對方言語用了近一半文章,闡述自己理由時也十分小心翼翼,再三說明評選來函中毀金小寶者十分多,以增強自己的信服力。更夸張的是,李伯元最后說他是因為擔心金小寶過于高調惹人輕辱而無法立足才特意將其抑止在榜眼的位置。這篇文章的語氣和態度分明表現了李伯元和《游戲報》的一種不自信,這種不自信來自于自身立足未穩。
但是到了61期《閱本報名妓牢騷一則再申論之》一文中卻語氣大變,直陳自己是經過調查并非單純依靠來函評選,認為張四寶(花榜狀元)和金小寶的位置無可置疑,無疑是與之前文章給出的解釋相矛盾的。這一篇文章將之前文章中隱隱約約對金小寶過于高調惹人非議的批評明顯化了,開始明確地表達自身的看法。這無疑是作為《游戲報》主人的自信心得到提升的緣故。其實一開始李伯元沒有按照來函數量將金小寶放在狀元的位置,就已經說明他其實抱有自己堅定的價值判斷,而且從他后來的評價來看這一判斷很大程度上仍然植根于士大夫的審美標準。但是一開始李伯元并沒有這樣的底氣理直氣壯地說出自己的價值偏向。然而花榜選舉以后,《游戲報》銷量一路飆升,李伯元的底氣也越來越足。繼61期大膽堅持自己的主張之后,63期李伯元就登出了《論〈游戲報〉之本意》這篇文章,而這篇文章本身基本上又重申了其辦《指南報》的本意,試圖在這個小報上灌輸自己的大義,這也是他自覺已經有了相當的影響力的表現。
在91期的《游戲主人告白》里,重申了花榜的排名,卻又鼓勵讀者來函表達自己的意見,為那些榜外或者未能到達理想位置的妓女爭取一席之地。同第一篇文章相比,這篇文章的態度顯然大不一樣,與第二篇也有所不同。第一篇回應文章,雖然小心翼翼,卻對反對意見持一種保守的排斥態度,之所以排斥是因為自身信服力不夠。而第二篇文章十分強硬,強硬既是一種自身權力的體現又是一種排他的表現。到了第三篇,我們忽然發現李伯元開始歡迎讀者的反對意見,他希望越多越好。這種態度一方面是其地位已經十分穩固,另一方面無疑是其發現了爭議帶來的好處,爭議才能帶來關注和利益。有趣的是這一篇文章旁邊正好登載著《游戲報》“告白增價”的啟示(廣告版面漲價),顯示了兩者之間微妙的利益關系。如果說前兩篇回應以及《論〈游戲報〉之本意》中表達的意思,還證明李伯元并未完全意識到都市媒體運作的精髓,那么最后這一篇回應卻證明李伯元雖然仍然堅持自己士大夫的審美和價值觀,卻已經和都市娛樂文化握手言和。因為他發現在花榜評選的爭議之中,一個新的討論空間被建立起來了。透過對名妓的討論、報道和爭議,各種對都市時尚繁華的文化權威消息也不斷被發布在這里。自己已經悄然成為這一文化產品領域中權力的代理人。
這一場曠日持久的對上海都市狹邪文化空間話語權的吞噬,得益于李伯元上海都市娛樂經濟文化鏈條的微妙操作,最終使得李伯元一時之間獲得了“花界提調”的稱呼,象征著他在這一領域的確獲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有趣的是“花界提調”這個名稱恰恰是《花月痕》中韓荷生無意中扮演的角色,即對名妓的排名抱有絕對的權力。只是李伯元并沒有也無法獲得完全掌控“四大金剛”的權力,他只是微妙地充當了上海名妓這一娛樂景觀和她們的觀眾之間的橋梁,通過報紙這一新興媒體悄無聲息地在狹邪景觀上搭建一面巨大棱鏡。如同他的后來者們一樣,他給自己定義成為都市娛樂生活的指南者。《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海上繁花夢》《九尾龜》等等這些被胡適魯迅稱為嫖界指南的不甚高明的作品,在形式上恰恰是通過“指南”這一性質來獲得市場和地位的。“指南”針對的是都市全新的生活文化和景觀,而被“指南”的是不斷源源而來都市后來者。對這一權力縫隙的運作,使得他們重新獲得了都市文化場域的話語權。
其實此時,李伯元們已經通過對都市日常娛樂空間的“再發現”,參與到了公共空間中來了。狹邪文學對都市娛樂空間和日常生活的展現的意義其實遠遠超越了“嫖界指南”這一道德批評。其在文學史上的影響,在新感覺派、周天籟、張愛玲等等一眾上海作家那里都能或多或少尋其脈絡,對整個中國文學的發展也提供另一個視角。但值得一提的是,李伯元們畢竟是剛剛從舉業脫身的士大夫。若以職業文人來看,這時李伯元已經取得了成功。如同他的同期的那些狹邪小說作者一樣,他以文養家生活無虞。但是他們在那一時期并不想當沒有靈魂的賣文者。相反通過最初的立足之后,李伯元迅速的重新調整了計劃。幾年后他放棄了《游戲報》,在庚子事變后一年辦了《世界繁華報》,雖然仍然是小報。但是新聞范圍逐漸從娛樂空間中解脫出來,慢慢靠近最初的《指南報》的定位,以時事為核心對中國當時的政治生活重新投以關注。在這份報紙上他刊登了吳趼人的《糊涂世界》和他自己創作的《庚子國變彈詞》,后又開始創作小說《官場現形記》。他似乎以一種曲折的方式重新實現了士大夫的人生價值,然而由于脫離了原有的士大夫的人生規劃,從期待“知遇”的政治理想中無意識解脫出來,他所能參與的公共空間的深度、廣度以及自身的獨立程度遠遠超過了朝堂政治所能達到的層面。這個意義上,他似乎可以算作正在轉型中的近代知識分子了。也許是體會到這種新型的“東山再起”背后的人生新的價值,當他創辦《世界繁華報》的當年,清政府舉辦經濟特科的人才選拔,李伯元被人保薦,卻最終沒有參加,主動的告別了他曾經汲汲以求的士大夫的人生。
注:
①⑦ 王學鈞《李伯元年譜》,薛正興主編《李伯元全集》第5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0、38頁。
②⑥ 孫國群《舊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1、72頁。
③④⑤⑧⑨ 魏秀仁《花月痕》,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9、44、43頁。
⑩ 李伯元《謹獻報忱》,《指南報》1896年6月6日第1版。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責任編輯:魏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