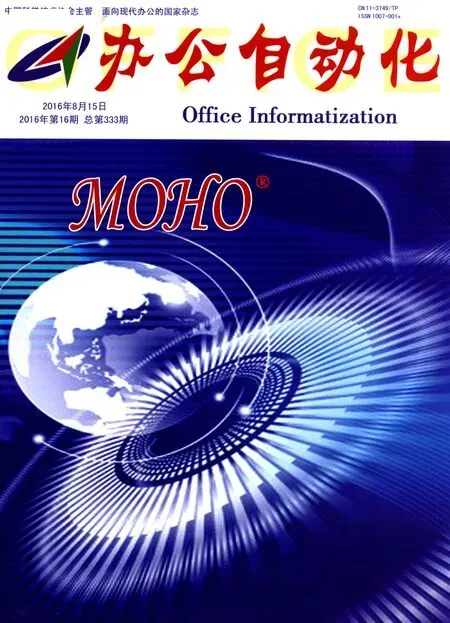科技創新的關鍵是制度創新
陳光
科技創新的關鍵是制度創新
陳光
專題報告
編者按:
創新2.0是科學2.0、技術2.0和管理與制度2.0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的結果,是知識社會環境下創新民主化的生動體現。知識社會的創新2.0需要開放協同、草根涌現,也需要頂層設計和制度建設推動。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和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科技三會”在北京隆重召開,推動制度創新也是大會的重要內容,這是科技界的盛事,也是新中國科技創新發展史上的大事。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陳光教授認為,世界已經進入大眾創新、用戶創新、協同創新、開放創新的“創新2.0”時代,迎接又一個“科學的春天”,建設創新型國家、世界科技強國,需要解決好科技供給與發展需求、政府推動與市場拉動、科技創新與體制創新的關系,科技創新的關鍵是制度創新。
陳光,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博導,成都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理事,中國創新方法研究會理事。
2016年仲夏之際,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和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三會合一”在北京隆重召開,這是科技界的盛事,即使放到改革開放38年乃至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發展歷程看,也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人們常常把這次盛會與1978年的科學大會相提并論,預示著又一個“科學的春天”的到來。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到“創新驅動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從“向科學進軍”到在主要科技領域和方向上中國“占有世界一席之地”;從經濟發展“三步走”戰略到2050年世界科技強國宏偉目標的確立,都足以說明這次會議厚重與份量。
當然,我們已經貼近21世紀的前20年,世界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經濟下行中正在孕育重大科技創新與突破,若干頃刻間足以讓現有科技、產業、規則、投資和價值“歸零”的顛覆性技術正悄然興起。真是“不創新不行,創新慢了也不行,如果我們不識變、不應變、不求變,就可能陷入戰略被動,錯失發展機遇,甚至錯過整整一個時代”。改革開放已經38年了,但是人們心中仍然保有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盼,人們仍然在期待“科學春天”的到來,某種意義上說明,現實中還有一些需要研究、探索和逐漸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科技供給與發展需求
在經歷了要素驅動、投資驅動之后,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意味著技術、品牌、組織、管理等人力資本作為高級生產要素替代投資或技術因素與投資組合正在成為經濟增加的主要動力,意味著科技供給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凸顯,科技供給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和動力。科技供給的主要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傳統經濟增長動力乏力或衰竭時,科技創新成為經濟增長動力源;
二是在“三去一降一補”工作中,通過創新在發展動力和活力上實現根本性轉變;
三是搶占先機,在物質結構、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識本質等一些重大科學領域開辟原創性工作方向。
與需求匹配的供給才是有效供給。科技創新要成為有效供給,必須充分考慮“廣義發展需求”。
一是科技產出與供給不僅要有利于緩解當前經濟下行、產能過剩的壓力,還有助于中國產業的轉型升級。互聯網經濟、VR(Virtual Reality,即虛擬現實)、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5G國際標準化、新能源技術等是科技供給的重要方向;
二是科技產出與供給不僅要有利于牽引經濟持續增長,還要體現綠色、包容、人文發展理念。不能因為確實有大量科技成果轉化不力,就喪失了對科技發展二重性的理性思考,更要摒棄GDP主義對提升科技供給的影響。到2030年,如果我們國家部分地區、特別華北地區的PM2.5濃度仍然居于世界“領先”水平,即使全國科技進步率從今天的55.1%提高到65~70%,我們居于世界創新型國家前列的地位也會大打折扣;
三是科技產出與供給不僅要“頂天”,要有利于突破核心關鍵技術,攀登世界科技高峰,提升國家整體創新能力,同時更要“立地”,要通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通過發展分享經濟和民生科技,為普通青年、廣大民眾提供創新、創業、創富的機會。
2006年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中國首次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目標,至今已經10年,世界已經進入大眾創新、用戶創新、協同創新、開放創新的“創新2.0”時代,一個藏富于民、民富國強的國家才是受人尊敬的創新型國家。
二、政府推動與市場拉動
公開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全社會研發支出達14220億元,其中企業支出超過77%。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科技進步貢獻率達55.1%,國家創新能力世界排名提升至第18位,經濟增長的科技含量不斷提升。我國在人類基因組測序等基礎科學領域、在高性能計算機、載人航天、載人深潛、北斗導航、高速鐵路等工程技術領域取得重要突破。現代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是既有基于民意基礎上的科學決策機制,又具有節約社會成本的資源集成能力。中國政府的社會動員能力和資源配置能力在世界上絕無僅有,具有集中資源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繼續發揮政府推動科技創新發展的優勢。
一是做好創新型國家建設“三步走”戰略規劃,制定實施“中國創新發展2050長遠規劃”;
二是政府主導、充分論證,選準并實施面向2030年的重大工程項目;
三是在國家宏觀層面制定國家科技安全、基礎科學發展、軍民深度融合等方面的方針政策和實施辦法。
系統集成時代,政府在大科學、大工程、大項目中的推動作用不可或缺。但是科學自由探索的本性和相關多元主體的利益博弈,同樣也是科學技術得以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科技資源配置方式已經發生重大變化,通過政府計劃管理的方式已經不適合創新要素迸發的生動的局面和要求。2015年9月國家啟動部分地區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建設,要解決的問題依然市場和政府作用的有效作用機制和科技與經濟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徑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是讓市場發揮科技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一是科學研究的選題機制要進一步優化,基礎研究課題要從世界前沿研究中遴選,技術開發項目要從工程實踐和新產品或新產品功能的用戶需求變化中遴選;
二是要強化企業在R&D活動中的主體作用,企業真正成為科技創新的研究主體、投資主體、利益主體、風險承擔主體和政府科技公共產品和服務購買的主要對象;
三是建立科技發展市場牽引和公益指導的互補機制,透過產權激勵、優化科技資源配置、高效率產出創新成果,同時擴大國家主導大科學、大工程的溢出效應,讓創新資源實現市場和社會的最優配置。
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目標,就是建立起來兼具效率與公平的科技發展政府推動和市場拉動的雙重作用機制
三、科技創新與體制創新
歷史不斷告訴人們,科技革命總是能夠深刻的改變世界發展格局、改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一些國家抓住科技革命的難得機遇,實現了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國防實力迅速增強,綜合國力快速提升。近代以來,我們屢次與世界科技革命失之交臂,有從世界強國變為積貧積弱的“東亞病夫”的恥辱與苦難,有著強烈振興發展的歷史情節。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和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三會合一”,透出的強烈信號是要把科技創新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推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科技是國之利器”的認識成為國家意志。這是科技之幸,也是國家之幸。
但是,現實的情況是,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研發投入總量、研發人員總量、國際科技論文數、國內專利授予量均位居世界前列,與此同時,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競爭力上升緩慢,經濟增速持續下滑、高增加積累的風險與矛盾日益凸顯,社會發展的結構性問題難以釋懷,科技與經濟發展深度融合機制尚未形成,部門分割、地區分割、軍民分
割現狀沒有根本改變。科技成果轉化的制度性瓶頸依然存在。科技人員依然疲憊于繁瑣、粗暴的行政束縛與窠臼之中。前不久有人抱怨說,科技人員在財務報銷人員面前像“孫子”。嚴格說,不是在財務報銷人員面前像“孫子”,而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傲慢和“行政主導”謬誤對科技事業的無情戕害。事實上,除了財務管理之外,在科技成果、研究設備、技術信息、學術出國、人事管理等方面對科技人員束縛已經讓科技界苦不堪言。
當李克強總理語出驚人,斷言“一流的科研不是靠政府管出來的”,當科技創新大會上科學家們感覺又一次解放了,其實心里并不踏實的時候,便可知科學研究的環境是怎樣的糟糕;當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題研究“科研預算、人員經費、旅差費”這些細目的時候,便可知我們日常的科研行政管理與教育行政管理已經到了怎樣“昏庸”的程度;當科技界呼吁政策松綁、期盼“科學春天”的時候,便可知科技創新的問題在于制度創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要協同發揮作用”,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要雙輪驅動。
一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更加全面地理解科技創新的社會功能。科技不僅僅是國之利器,科技還是民族的精神與文化,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杠桿,科學所秉承的求真務實、批評與懷疑的精神,將洗滌歷史的塵埃,突破現實的桎梏,引領社會不斷前行;
二是要進一步向世界開放,讓世界真正了解中國的自信,科學沒有國界,世界各國的文明成果都應該吸收和學習,要逐漸剔除信息樊籬,開放與共享是科技創新緊貼世界前沿、永葆創新活力的基本保障;
三是要深刻認識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的關系,“科技創新”是生產力,“制度創新”是生產關系。就目前中國發展階段講,科技生產力依然被不合理的生產關系所束縛,這是主要矛盾,影響創新驅動戰略實施的關鍵因素,不是科技創新,而是制度創新。制度創新能走多遠,科技創新就能走多遠。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指標不僅是科技貢獻率、R&D投入強度、對外技術依存度等“技術性”要件,還包括開放、高效、合理、創新的制度設計。在科技創新大會之后,我們真的期待一個以制度創新為核心、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雙輪驅動”的全面創新時代的到來!
The Ke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Chen G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