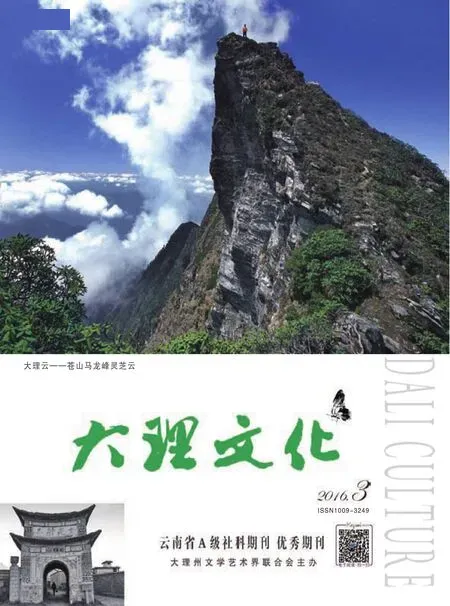普洱,那淡淡的甘苦
●疏 雨
?
普洱,那淡淡的甘苦
●疏雨
與普洱有著綿密的牽記,是因為兄長的緣故,最初的時候,普洱還不叫普洱,叫思茅。都說有親人的地方就是故鄉,那普洱也應是我的故鄉。我的兄長在那,父親的孤墳在那。
當普洱還叫思茅的時候,我不曾去過,那時候父親還在,可我和父兄還未曾相認。我一直住在距他們很遠的巍山古城。兄長來信相認時,我剛剛成年,父親剛剛故去,在我不知道的遙遠的異鄉故去,帶走的是他兜兜轉轉的滄桑和牽念,還有我的難言的傷痛。
如今說來,父親已離世多年,住在異鄉的一抷黃土里,其實對于我來說,他只是一個模糊的意象,只是“父親”這兩個似乎還存留著些許陌生體溫的漢字。父親尚在人世的時候,我沒有依靠過他寬厚的肩,沒有機會聽他對我說過一句話,從未聽過他慈愛的聲音,更未曾與他的容顏相見相親。
我不知道,父母間究竟有什么深入骨髓的芥蒂,致使我們血脈相連卻形同陌路,只知道小伙伴們在父親懷里撒嬌時我那空蕩蕩的失落,無助時對著一個模糊的名詞——父親陷入臆想和絕望……
孩提時代,父親住在我的心里,他的容顏形象隨著別人的父親不停地變換著:趕廟會時,脖子上駕著小孩踮著腳的男人;放學路上,用雨衣裹住孩子的那個偉岸的身影;出差回來,身后藏著玩具讓孩子猜的笑臉;朱自清筆下緩緩爬過月臺的背影……我在周遭的小伙伴的父親臉上尋覓猜測著父親的容顏,走在路上我會不時地張望,朝我凝神的到底是不是我自己的父親——他一定是知道我的,他可能常在我上學放學的路上偷偷看著我,我不知道為什么小伙伴唾手可得的一切于我是如此地遙不可及,這樣的缺失開始是疏疏落落的,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交織得愈加深切而綿長,在別人異樣的目光里,我窺到了不同于他們的點點滴滴——父愛如山,而我沒有這座讓身心倚靠的山,很多時候我只能自己面對突如其來的風雨。
身邊的親友偶爾會問我:“知道你爸爸嗎?”我茫然地搖搖頭,“可我們不敢指給你……”不知當時的他們出于怎樣的心理,只記得目光中有疑惑,有好奇,有真正的關切和無奈。我不再多問,小小的我已能揣摩或簡單或復雜的表情和心態。如今想來,明知而不設法讓我知道的他們犯的是一個怎樣大的錯誤——他們讓我失去了見父親一面的機會,當然,對于他們來說這是礙于母親的聲明,信守一個只適用于成人游戲規則中的,卻讓我抱憾終身的秘密。是的,這一切也原本與他們沒有半點關系。

最后一次機會錯過于我十四歲的一天,那天早上,正上初二的我,依舊靜靜地回到家里,家里也依舊地平靜,而過后我才知道,我的父親將隨我的哥哥定居異地,回來將他們住的房子賣了,恐怕以后再不能見到我,他們特意來央求母親讓我們見上一面,以提前彌補這徹骨的遺憾,然而,話音未落,便被母親驅逐了出來,還追出去數十米。待我回來,一切都已風平浪靜,我就在這樣無聲的不得而知中錯過了和父親訣別的機會——這一走,父親就永遠沒再回來……
從異鄉傳來父親去世的消息,是在我二十歲那年。我曾有過的種種和父親見面場景的想象頃刻化為泡影。在母親波瀾不驚的表情里,我只能默默地承受著這徹入骨髓的絞傷……對于父親的期待戛然而止。從此,父親已從我的心里移居到異鄉的一座孤墳里……
父親走后,我收到兄長的來信,父親曾經的容顏定格于那張小小的兩寸的照片之上,那樣薄而輕,而這照片、信封的兩端是一對二十多年從未謀面的兄妹的心,那樣厚實而沉重,也許,這份情感已根植于彼此的心中,只是在各自的人生奔走的無意中暫時淡化了,但父親的故去,一下子使這份感情更厚重和沉痛了。我和父親已錯過了一生,我們兄妹也已錯過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二十五年。畢竟,人生沒有幾個這樣的二十五年。
兄長的來信中開始有了自己,有了嫂子,有了小侄女的點點滴滴,我從照片的神態和信的字里行間猜想著兄嫂的生活,感受著他們的幸福和不易。從那時起,那個叫做思茅的遠方有了我日益綿長的牽記。
直到2001年的一天,身在思茅的兄長悄然返鄉和我以地下黨接頭的方式在賓館相見。他開門的一瞬間我就知道是他了,這一天我們等了二十五年。但我們沒有相擁而泣,和所有的兄妹一樣自然和親近,彼此都在心間眼底。年近不惑的兄長眼角已漾起了滄桑,而我也不再是那個不諳世事的小姑娘,眉梢眼角間也有了歲月流轉的痕跡。我默默地在他臉上尋找父親的影子,父親走了,長兄為父……從那一刻起,父親的音容在我的心中開始具象化,他應該很像我的兄長,如他一樣慈愛,溫良。
后來,我也結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小家,享受著悲欣交集的尋常的幸福,也為只屬于自己周遭的哀樂糾結,掙扎。哥哥仍從那個叫做思茅的遠方回來看我,后來帶上了嫂子和侄女。和兄長的牽記就這樣日益綿密而清晰。
待我第一次去看望哥哥的時候,心心念念的思茅已不叫思茅,被改名為普洱,“普洱”兩字或許是因為茶的關系,仿佛有了蒼綠的味道,從口中念出便生出了唇齒留香的意味。到了普洱,確實是一個蒼綠的城市,周邊的公路兩旁都是郁郁蔥蔥的林木,隨處可見藤纏樹樹纏藤的悱惻纏綿,連街道中間的隔離帶種的都是青茶。普通的飯館,店鋪都有茶桌,讓人感覺品茶于普洱人而言和呼吸一樣尋常自然。想起哥哥畫的山水,總是重重疊疊山,密密層層樹,頗有黃賓虹神韻,想是被這普洱的風物同化了罷,或許那關山萬重外是他長大的故鄉,這層林葳蕤處便是他的普洱。
我們的到來,讓哥哥很是欣喜,他和嫂子帶著我們去了位于城東南的梅子湖,邂逅周渝民、劉詩詩的《回到愛開始的地方》;去東部的洗馬河,據說諸葛亮率軍南征時,曾在這條河里洗刷過戰馬;去寧洱的同心,走古驛道,看大水車,在同心橋上鎖同心鎖。去景洪吃傣味,菠蘿飯、舂干巴讓孩子大快朵頤;去鄉下吃菌子宴,嘗遍各種時鮮美味菌子;還帶我們去吃海鮮,給孩子剝蝦子,看著孩子吃完滿意地笑。就像要把他周邊所有好玩好吃的都讓我們玩個遍,吃個遍。看著他饒有興致,神采奕奕的樣子,我心里是莫名的愉悅,對能干的嫂子甚是感激。哥嫂是大學同窗,校園內青澀的戀情修成正果。嫂子是思茅本地人,爽朗不失周到,大氣不乏柔情,里里外外打理得妥貼而周全,對哥哥更是悉心照顧。
知道我喜歡茶,哥哥帶著我們在微雨中登上萬畝茶山,淡淡的霧薄薄地縈繞著,清風中,嫩綠的芽尖上星星點點的雨珠微微搖曳。空氣里浸潤著泥土和新茶的清新,濾盡心頭的紛繁和鉛華。在茶山,我們還親自感受了采摘、揉捻、烘干的樂趣。走過了從普洱到寧洱的茶馬古道,如今已人跡罕至,光滑的石頭,深深的蹄印,是曾經輝煌的馬幫,留給我們的無盡的、極富張力的遐想。行在其間的我們成了一個小小的盜版的“考茶隊”。
晚上,一家人圍坐在茶桌旁,哥哥將“咕嘟咕嘟”燒沸的水倒入紫砂壺中,輕搖片刻,用這洗茶的水涮了涮杯子,讓茶杯也變得溫熱起來,再將沸水倒入壺中,一會兒,裊裊的茶香便蕩漾起來。倒入杯中,握在手里,握著剛剛好的暖和妥帖,看著杯中的茶葉如世事沉浮,起起落落,心中不禁感慨:原來,再山長水遠的人生,不過是手中的一盞普洱,亦濃,亦淡,亦起,亦落。哥哥的儒雅、清朗便是這經年的普洱濡養的罷。然哥哥沒有了先前的煥發,眼里心上是無限的擔憂:“你這樣的身體,如何扛得住?這些年來,我都沒怎么照顧過你。”喝著茶,這樣講著,我們自然而平和,沒有傷感,如茶,溫熱的,緩緩的從喉間輕輕涌動。其實,這些綿密于心底的愛一次次抵御了徹骨的傷痛,一天天走過來,也是綿邈清寧,靜落燈花了。只是氤氳了那清灰的人生底色,再怎樣也去不掉了。
哥哥畫作里的行云流水,喝普洱時的云淡風輕,讓我釋然而安心。而哥哥對我身體的擔憂卻讓他無法釋懷。在他又一次返鄉看望我時,我明顯的感覺到閑話家常輕松自若的他,把這份牽掛和愛放在了心底。而也就是那時,我發現了他頭上竟然生了許多白發,那樣駭然地在我眼前晃動。
平日我們在自己的生活里輾轉奔波,而心中的牽念卻沒有消解,有時我感覺血緣真是奇妙的東西,它會讓失散多年的親人的心又根脈相連的在一起,且沒有絲毫的突兀和局促。因了心里的這份惦念,我們一家又赴普洱去看望哥嫂。路途遙遠且不好走,加之修路,讓哥哥很是牽掛,叮囑路上慢慢開,多晚都等著我們。沿路我打電話過去,哥哥總是響了一聲就馬上來接,聽到我說已到哪里了,他總就釋然道:“不急,不急,慢慢開。”溫暖從電話那端悠悠傳過來。到了家里,嫂子忙著炒菜,哥哥端出煲了一天的當歸羊肉湯,讓我們喝,他惦記著讓我補補,他不知道,這幾年孩子大了些,我的身體比原來好多了,顛簸了一天,在哥嫂的等候和慈愛里狼吞虎咽著,格外地溫馨。
哥哥的白發更多了,原先的黑發和煥發的英姿漸漸褪去,我心里有些難過,但依舊淺笑著敘著家常。而我的精神狀態、氣色卻讓哥哥很開心。心就這樣輾轉跌宕著,而說出的話都是平常兄妹的閑聊,記掛在心里,不讓彼此有任何的負擔。我們那沒有彼此的,缺乏飽滿的愛的童年顯得艱難而漫長,但因為性情的緣故,并沒有讓我們變得凜冽地與生活對抗,可心底那份微苦和薄涼卻是入髓的,與我們如影隨形。多年來,得益于嫂子的爽朗真摯、老公的寬厚溫情,這種感覺雖得以包容和消解,卻是不能完全抽離的,這一點,我們兄妹都彼此感覺得到。只是在這份微苦和薄涼中,我們更愿意去享受、珍惜這失而復得的遲來的靜好。
正如接過哥哥手中的茶,喝著那琥珀一樣澄澈的漾著暖香的茶水,聽他說:“慢慢喝,那淡淡的苦味過后,就有了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