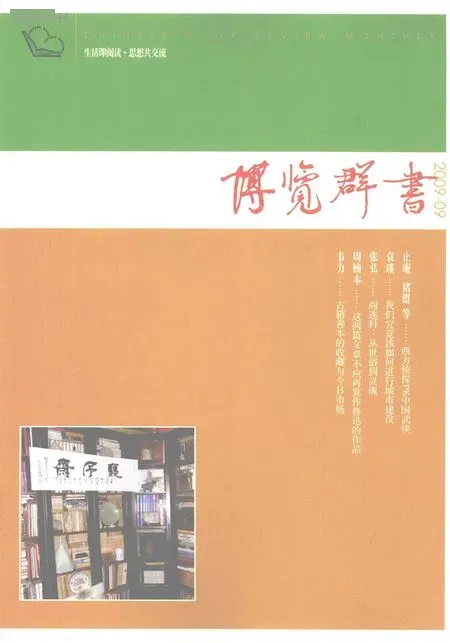談安徒生研究
(一)
一個從事于童話研究的人,如果沒有研究過安徒生,他的童話研究,不可能做出成果。因為要寫《童話學》,自然,我也對安徒生做過一番研究。
不過,我不能說我是一位安徒生的研究家,因為我只能躲在我的小書房里,讀過他的全部168篇童話作品,以及我能夠找來讀的他的傳記和對于他的作品的評論,自然都是翻譯過來的文字。我的研究,沒有什么新進展,更沒有什么新價值。
不過,我認為“安徒生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童話作家,是世界上最有影響的童話作家。他是童話的一面大旗,一說童話就要提到他。我國現代童話的開拓和發展,受他和他作品的影響最大”。(《童話學》)這完全是事實。
我在寫《童話學》,梳理童話發展歷史的時候,我有一個新發現。即,每遇童話處于低落,在度過一段艱難時日后,總有人把安徒生抬出來,發表一系列的關于安徒生的論介文字,出版社開始出版安徒生的作品,這種先兆后,接踵而來,是一批批創作童話出世了,童話一步步走向繁榮。好像這現象,是一種規律,因為在我們這兒已重復多次。
目前,臺灣對于安徒生的研究“熱”起來了,我似乎預感到臺灣的童話創作,必然將會出現一個新的飛躍,新的局面。
(二)
安徒生是位偉大的作家,他的作品也是偉大的。他為世界做出了卓著的貢獻。這是大家所公認的。
但是,在我們安徒生的研究中,也有種種不好的傾向,即是把安徒生“神”化,說成是童話的“頂峰”。有人認為安徒生以后沒有再出現安徒生童話那樣的好作品。世界上童話并沒有進步,而是倒退。自然,今天的許多童話作品,還沒有能和安徒生的童話那樣產生世界性的轟動效應,其實安徒生童話的轟動效應,除了作品本身的成功因素外,還有許多其他的種種客觀條件。絕不能說,世界上童話創作不是在發展,沒有出現優秀的成功的作品,恐怕也不是事實,這說法也是不科學的。有的人,把安徒生的全部作品說成是典范作品,都得繼承,這似乎也是偏頗了。安徒生的許多作品,是成功的,但也有一些作品,例如他后期的作品,我想至少不能說是兒童所適合閱讀的作品吧!我們的研究工作,必須做科學的分析,不能是盲目的迷信。我看過有的童話理論研究著作,連篇累牘的是安徒生的童話如何如何,而不提當前當地的童話創作如何如何,這就不好了。安徒生的精華,我們應該繼承,但不是沒有應該揚棄的部分。我們的童話理論研究文字,可以和應該從安徒生那里接受遺產,但也不能言必稱安徒生,一篇論文中盡是安徒生如何如何說,而沒有自己如何如何說,這是不能算好論文的。
(三)
前不久,我在報上見到一篇文章,說丹麥歷史學家揚·約更森最近提出:安徒生的身世,并非像眾所周知的是一位鞋匠和女傭所生的孩子。揚·約更森是安徒生就學過的學校的現任校長。他認為安徒生是后來成為丹麥國王的庫利斯八世和一位叫埃利賽貴族小姐所生。他提供了許多證實的材料。還有著名的安徒生傳記的作者埃利阿斯·布萊茲多夫也曾說過:“安徒生所談的家庭背景,純屬虛構。”
這篇文章,對童話研究者來說,是震動的,因為我們一直都認為安徒生出生于貧苦的鞋匠家族。但是震動盡管震動,卻無法證實,因為我們只能看到第二手,甚至第三、第四、第五手的材料。我只是將這則短文剪下,又發在我主編的《童話選刊》上,提供給廣大讀者參考。
臺灣的兒童文學界,不知是不是知道安徒生身世的這一新說?前些日子,在臺灣《國語日報》上刊載了我們《童話選刊》編輯小啦小姐寫的那篇通訊:《丹麥行——訪安徒生中心約翰·迪米留斯教授》。在這篇文章中,這位研究安徒生的教授說:“事實上,在安徒生的童話和故事中,有相當的數量是專門為成人寫作的;一部分童話是為兒童的,但至少同時也是為成人的。”這又是一個新發現。
這個發現,如果成立,那會牽扯許多關于兒童文學童話、兒童文學作家等的一系列問題。過去的許多傳統論點和觀念,將受到沖擊和修正。
(四)
談起安徒生,自然會想到那個以安徒生命名的世界性的兒童文學獎。但是這個獎,對于我們華文兒童文學并沒有放在恰當的位置上。首先,他們沒有我們華文兒童文學作家參加獎的評審委員會,他們那些評審委員沒有一位懂得華文,他們更不了解華文兒童文學實際。而用華文寫作的兒童文學,必須要譯成英文才能接受評審;用已經翻譯過的作品,來評審華文作品,有多少準確性就值得懷疑。我想,以安徒生命名的這個兒童文學獎,這樣在華文兒童文學世界,也會失去它應有的聲望和作用。安徒生是丹麥的,也是世界的。安徒生兒童文學獎應該是一個真正世界的兒童文學獎。
(洪汛濤,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理論家,“神筆馬良”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