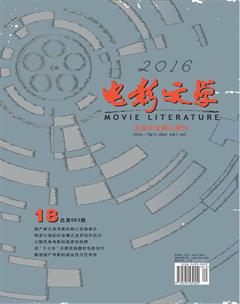《這時對那時錯》的平行敘事分析
周穎 李娟
[摘 要] 《這時對那時錯》是韓國導演洪尚秀2015年的最新作品,這部生活小品延續了洪尚秀的一貫風格,通過極簡的人物、場景和情節展示了對日常生活的深入觀察與思考,體現了一種獨特的生活哲學與日常美學。影片采取了一種別致的敘事結構,即通過平行世界的構建來進行重復敘事,大膽地在一部電影中把同一個故事講述了兩遍,并在二者的細微差別中力圖揭示生活中不被人注意的空隙與隱而不發的另一面,帶給人無限的思索與想象空間,并最終呈現出生活本身的偶然性與無限可能性。
[關鍵詞] 《這時對那時錯》;洪尚秀;敘事;生活;哲學
無論在韓國還是世界影壇,洪尚秀都是一位極具個人風格的導演,他的電影既沒有好萊塢的華麗敘事與宏大場景,也沒有主流韓國電影對熱點社會事件的反映與批判,而是采用極簡的敘事風格、人物關系模式與日常化的場景構建來展現平凡生活的細節,流露出對生活的細致觀察與哲學思考。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洪尚秀導演創作了近20部電影長片,這些電影始終體現著導演的獨特風格,從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視角出發,講述普通男女之間的情感故事,成為逆精英化敘事的一種獨特嘗試。
洪尚秀在他的處女作《豬墮井的那天》之中就已經將自己的實驗精神呈現了出來,他的鏡頭語言和敘事風格都極具個人色彩,而在此后的電影創作之中,洪尚秀也不斷嘗試對自己的敘事形式進行突破與創新。《這時對那時錯》是洪尚秀2015年的新作,這部電影獲得了洛迦諾電影節的金豹獎,獲得評論界和媒體的一致贊譽,它一方面延續了導演的創作風格,一方面又有所創新,豐富了自身電影創作序列的多樣性。
一、平行宇宙:生活的無限可能
《這時對那時錯》這部電影的片長恰好是兩個小時,但是導演用兩個小時的時間把同一個故事講了兩遍,在影片接近一個小時的時候,故事從開頭的地方重新開始講述,片頭也重復出現了一次,無論是人物、場景還是情節的基本發展脈絡都沒有改變。但饒有趣味的一點是,故事雖然有著相同的開端,卻因一些偶然事件和人物情緒的細微波動而引起了不同的結局。前后兩段的差別就仿似同一個故事的不同結局,導演所展現的是兩個相互平行卻又存在某些內在關聯的世界。
這種利用平行世界所帶來的多種可能性而完成敘事的電影已有不少,其中更不乏經典之作,如波蘭大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機遇之歌》、德國導演湯姆·提克威的《羅拉快跑》等,但這些電影都是從某個關鍵的結點開始分出平行世界的,在《機遇之歌》中,影片的主人公威特克在車站追趕火車,導演給出了三種命運的可能:威特克追上了火車;他沒追上火車并被警察抓住;他沒追上火車但遇上了曾經的女同學,三種命運依次呈現,并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局。在《羅拉快跑》中,羅拉為了救自己的戀人曼尼需要在20分鐘內籌到10萬馬克,導演同樣給出了三種不同的可能,三種結局依然是截然不同的。在平行空間的假設之下所完成的電影敘事不僅擴大了影片的內容含量,而且揭示了生活的可能性與偶然性,使影片具備更豐富的內涵與外延,為觀眾提供了廣闊的想象空間。
《這時對那時錯》雖然在平行空間的敘事方式上與上述影片有著相似之處,但這部電影在內容上沒有二者的政治隱喻與未來想象,剪輯節奏也明顯更加緩慢,更重要的是,《這時對那時錯》呈現出的差別是十分細致的,與《機遇之歌》和《羅拉快跑》中的毫厘之差產生千里之別的結果完全不同。
同樣是利用平行世界的可能性來進行重復的敘事,《這時對那時錯》做得更為徹底,干脆從頭開始重新把故事講述一遍,而不是從某個關鍵的結點生出不同的可能性。因此,洪尚秀在電影中試圖通過重復來“窺探生活的空隙”,發現生活原本隱藏起來的一面,貼近生活本真的樣貌,而并非想要窮盡生活的所有可能去探索未知。
在這部影片中,男主人公咸春洙是一位小有名氣的導演,他到外地開講座宣傳自己的影片之時偶遇畫家尹希靜,二人因同是藝術家而相互吸引。在第一個故事中,咸春洙表現得像是一個情場老手,時機恰當的邀約、看似真心的夸贊和風趣幽默的言談都吸引著希靜,但在希靜姐姐的聚會上他不得已吐露了自己已婚的事實,更令希靜難以接受的是春洙在評價自己的畫作時使用的語言幾乎完全一致,這說明他根本不是發自內心地贊賞希靜的畫作。因此,第一段故事中的兩個主人公不歡而散,希靜從放映廳起身離開,為這段感情畫上了句號。但在第二段故事中情況則有所不同,兩個人相遇的時間、地點和方式都與上一段故事中完全一致,咸春洙這次卻表現得笨拙而直率,沒有了適時的邀約,在畫室中對希靜的畫作更是坦白地說出了自己的意見,惹得希靜不快。誤會消除之后二人同去吃飯,在酒館中春洙首先向希靜說明了自己的婚姻狀況,然后再向希靜表達自己的愛意,希靜也對此感到十分可惜,這段感情雖仍將面臨無疾而終的結局,但兩位主人公因這段感情收獲的東西卻變得不再一樣。
洪尚秀利用這種平行之中的重復敘事為我們揭示出生活的復雜樣態和曲折幽微的奇妙之所,其中更是隱含著導演的生活態度與生活哲學。
二、“對”與“錯”之間的生活哲學
影片在平行世界的架構下完成的重復性敘事所講述的兩個故事被導演區分為“對”和“錯”,但他在片名中所謂的“這時對”與“那時錯”,到底哪個是“這時”,哪個是“那時”呢?實際上這些問題不僅導演沒有給出答案,每個觀眾在觀影之后也都會產生不同的意見,甚至同樣無從判斷。歸根結底,所謂的“對”與“錯”之間并不存在價值判斷,導演所呈現的只是生活的微妙和偶然。
無論是前一個故事還是后一個故事,其中的主人公都僅展現了部分的自我,從兩個故事中我們才大致可以知道,咸春洙雖然事業小有成就,但也有自己的苦悶和困境。尹希靜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生活和藝術追求,但同時也是孤獨、渴望認同、希望被愛的。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不完美去生活,渴望擁有更好的生活,他們遇到彼此只是生活中的一個插曲,但如何處理這突如其來的相遇不僅取決于他們展示自己的方式,也將對他們未來的生活產生重要的影響。無論二人選擇何種方式,都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在第一個故事中咸春洙掩蓋了自己苦悶和失敗的一面,在第二個故事中他卻沒有回避自己的無力,笨拙地坦白自己,這兩種態度都是咸春洙自身所隱含的可能,選擇采用哪種態度或許是出于很多因素的影響,而洪尚秀則沒有試圖告訴觀眾對錯,而僅僅是將這種細微的差別顯露出來,留給觀眾自己去判斷與思考。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對錯向來沒有那么分明,洪尚秀借此想要表達的與其說是“對”與“錯”,不如說是“這時”與“那時”,他更加注重在相同的條件與背景之下,人物自發的情感態度與生活選擇,過程顯然比結果更為重要。借用海德格爾的哲學來表述,即人被拋入這個世界之后盡管無法選擇自己的生存處境,但也并不是完全被動的,而是可以主動地承擔起自己的存在,進行決斷、選擇與籌劃。咸春洙與尹希靜就像是被導演洪尚秀在特定的時間拋入到寺廟的情境中相遇,這是無法更改的必然,但二人如何相互結識并相互影響卻在某種程度上不再由導演決定,他們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走向,在細微的差別之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質。
因此,在洪尚秀所構建的“這時”和“那時”之間不是截然二分的,兩個平行的世界之間既有各自的獨立性,又有著某種說不清的關聯,在平行的敘事完成之后,不僅能揭示出上述的生活哲思,還能夠令人產生無限遐想。在平行的關系之中完成的重復性敘事具有十足的奇妙之感與開拓能力。導演洪尚秀曾在這部影片的新聞發布會上說第一部分拍完之后就先給演員看過了,演員在知曉第一段故事的情節結構和主人公的情感基調之后再進行第二段的拍攝,因此在第二段之中兩人已有一種無法言明的似曾相識之感,他們帶著已有的某些情緒進入第二段故事之中,能夠生發出原本所不具備的一些感情。在接受Cinema Scope雜志的訪談時,洪尚秀談到了這兩個平行世界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兩個世界是同時存在的,一旦它們之間的關聯被明確道出,兩個世界就會消失。或許正是因為關聯之間的模糊性讓兩個世界的兩種可能得以并置,從而將由這種模糊所帶來的疑問留給觀眾去深思。
洪尚秀通過獨特的敘事方式所呈現的生活態度和哲思完全被放置在一種平穩緩慢的氛圍與基調之中,對于他來說,對于生活的領悟從來都在生活的過程之中,對于日常生活的關注也是他一貫的主題,在這一主題之下的探討也往往是通過略顯瑣碎的日常生活本身來加以呈現的,但人物之間的行為和言談又讓這一過程充滿了趣味。
三、平行、重復與日常生活的復雜性
洪尚秀的生活小品往往是不著一絲痕跡的,觀眾看不到導演的用力之處,卻能夠感受到導演想要傳達的內容,這種舉重若輕的能力來源于導演對日常生活的仔細觀察與思考。實際上,洪尚秀每部電影的成本只有幾十萬美元,電影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海外藝術機構提供的基金。因此,他的影片中不僅人物比較少,場景也基本取自日常生活中的幾個固定場所:咖啡館、酒館、賓館、街道等,因此吃飯、飲酒、旅行、聊天基本構成了洪尚秀影片中的大部分內容。從形式上看,洪尚秀的鏡頭語言也并不復雜,他善于使用長鏡頭,并在場景之中和人物保持一定的距離,產生有距離的觀照,有時一個場景中的故事在一個長鏡頭中皆可以完成,使故事本身能夠保持一種完整性和連續性,減少導演主觀情緒的介入。
至于影片的敘事結構,自然也與洪尚秀對于日常生活的態度有著密切的關聯。洪尚秀導演對自己影片的敘事結構進行了有意的構建,他善于使用非線性敘事結構,如本片的平行重復敘事,《處女心經》《生活的發現》等片中的對比與反復敘事,還有以《劇場前》為代表的套層結構敘事等,都是通過獨特的敘事方式對生活進行重新發現。洪尚秀試圖借助別出心裁的敘事方式來重新觀照已經被熟悉的日常生活,正是因為我們每天都處在日常之中,實際上我們對于生活的感受已經鈍化了,洪尚秀在影片中能夠通過平行并置與重復來提醒我們生活被隱藏的另一種面貌,于是在重復之中觀眾非但沒有感到煩瑣與冗長,反而還獲得了關于生活的新鮮感受。在并置與重復之中,洪尚秀重新激活了被遮蔽的感情,讓人物的生命體驗更加復雜。
在《這時對那時錯》之中,洪尚秀進一步將這種由重復所揭示的生活美學顯露給觀眾。舉例說來,在第二段故事中,春洙在酒館中與希靜喝了很多酒,二人也逐漸開始袒露自己的心聲。正是因為之前春洙說出了自己對希靜的畫作的真實看法,希靜才會坦白自己很孤獨,交不到朋友。而由于希靜的坦白,春洙也說出了自己對希靜的矛盾的愛慕情感,他為自己還擁有愛上一個人的能力而哭泣,為這份感情的無法延續而傷心不已,希靜也因他的誠實而感動。二人的這番真情流露是第一段故事中所沒有的,但實際上在第一段故事中春洙未必是虛情假意的,導演通過同一個故事的不同講法告訴我們有時溝通本身也充滿了謬誤與偏差,一個小小的細節也許會導致事件完全不同的走向。
由于我們的生活是線性的、不可重復的,因此我們對事件與人物的判斷往往只能依靠它實際發生過的情形。但洪尚秀借助影像實現了平行的構建與重復的敘事,打開了全新的理解之門。通過這種重返事件現場的方式,觀眾的視角不再是平面的、線性的,而是立體的、多維的,畢竟生活本身并不因日常的局限而變得簡單,它總是復雜而難解。洪尚秀正是用自己的影像來對生活本身的復雜性加以展示,這不僅是他所選擇的對待電影的態度,也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參考文獻]
[1] 洪啟龍.“生活的發現”:從現實走向“極簡”的銀幕哲思[D].重慶:西南大學,2015.
[2] 任丘.《這時對那時錯》本是虛無,何分對錯[J].中國企業家,2015(23).
[3] Francisco Ferreira,Julien Gester采訪,Roger Koza撰文,帕拉多克斯譯.重復與區別:洪尚秀自評《這時對那時錯》[J].Cinema Scope,2015(64).
[作者簡介] 周穎(1979— ),女,河北承德人,碩士,承德醫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教育學、中華傳統文化。李娟(1979— ),女,河北承德人,碩士,承德醫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醫學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