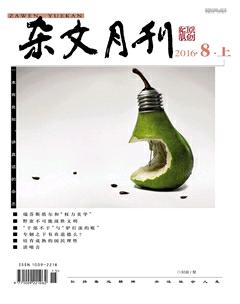瑞芬斯塔爾和“權力美學”
周拓
近讀一篇題為《“功德無量”抑或“遺患無窮”?》的文章(《雜文月刊》2016年第6期原創版),方知毛志成先生曾極力倡導編寫一部“《權力美學》讀本”,“使權力顯示出應有的美感,并為此而構建一個專門性的‘權力美學”。毛先生的高論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不過,倡導編寫“《權力美學》讀本”是一回事,談論“權力美學”則是另一回事。盡管將權力與美學聯姻,不啻是在“拉郎配”,可“權力美學”這一概念畢竟使用并熱議了若干年,具有特定的所指,即指稱一種崇拜權力的審美觀念。記得筆者初識“權力美學”這一概念時,首先聯想到的就是德國女導演、對希特勒一往情深的萊妮·瑞芬斯塔爾,她無疑是實踐“權力美學”最杰出的藝術家。她制作的兩部紀錄片《意志的勝利》(1934)和《奧林匹亞》(1938),堪稱體現“權力美學”的典范。前者宣揚的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即“納粹主義”),將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推向了極致。后者記錄的是1936年柏林奧運會——將納粹德國從一戰廢墟上重新崛起和其稱霸世界的野心表現得淋漓盡致。瑞芬斯塔爾自稱不關心政治,不是為了宣傳;可她的每一個鏡頭幾乎都凸現出強權的威力,表現了她對極權的極度癡迷與無限崇拜。“權力”一詞的拉丁文詞源為“fascer”,音譯即“法西斯”,說“權力美學”就是“法西斯美學”,應算是恰如其分吧。蘇珊·桑塔格在評論瑞芬斯塔爾時,就深刻闡述了這種美學觀念的來龍去脈:“法西斯主義美學產生于對控制、屈服的行為、非凡努力以及忍受痛苦的著迷(并為之辯護);它們贊同兩種看似相反的狀態,即自大狂和屈服”。在蘇珊看來,“法西斯主義的戲劇表演集中在強權與其傀儡之間的狂歡交易,它們身穿統一制服,人數呈現出不斷膨脹的勢頭”,將“人群/物群集中在一個具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具有無限個人魅力的領袖人物或力量周圍”,“歌頌服從,贊揚盲目,美化死亡”。
“權力美學”進入中國學界的話語系統也有些年頭了,但多是作為批判對象論及的,像毛先生這樣公然推崇、極力提倡編寫“《權力美學》讀本”的實為鮮見。與其相反的是朱大可先生,始終對權力美學保持著足夠的警惕和清醒的認知。他曾追溯“中山裝”的淵源,指出當年孫中山拿來做樣品的乃是日本的士官服,而日本士官服參照的又是德國士官服。因此,“中山裝的姓氏,本該名叫德意志”。而之后曾有那么幾十年,中山裝竟“成為全國民眾的單一服裝”,這還不足以顯示出權力美學的強大征服力?希特勒上臺之后的德國青年,為能穿上威嚴的納粹軍服而紛紛參加黨衛軍;“文革”時期的中國青年,不分男女,無不以戴上一頂準軍帽為榮;直到去年年末上映的影片《老炮兒》,主人公還把一件“將校呢”大衣當作圣物珍藏——這莫非就是毛先生所稱贊的權力的“美感”和“魅力”?近年來,朱先生更多的是批評一些象征權力的建筑,并將這種權力美學一直追溯到秦始皇嬴政。對此,我們讀一下杜牧的《阿房宮賦》即可明了:“覆蓋三百余里,隔離天日”,“不知其幾千萬落”。如此皇家威儀能不令蕓蕓眾生臣服么?這恐怕也是今人大肆鼓吹并發揚光大的原因吧?我們不妨看看全國各地的政府大樓,哪一座不是蓋得富麗堂皇,高大、豪華而又氣派十足?恰如兩千年前蕭何對劉邦所言,“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令后世有以加也”。可見,府衙之高大府院之開闊,無非是想顯示權力的威風與威嚴,讓平民百姓望而生畏。動輒“以大為美”,大手筆、大場面、大制作,可這種整齊劃一、思想趨同的大一統觀念,勢必會泯滅人的個性與自由,無情地扼殺人的自主性和創造力。權力美學的肆虐,恐怕也正是國民奴性延續兩千多年的原因所在。將權力“魅力化”,編寫什么“《權力美學》讀本”,難道還想繼續普及奴化教育,讓廣大民眾永遠心誠悅服地當一個好奴隸、好奴才?
毛先生還煞有介事地質問,“真正的罪惡是權力本身造成的么?”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權力一旦失去制約和監督,它隨時都會作惡。正因為如此,美國憲法才在修正案的前十條鄭重地提出“權利法案”,其目的就是為了“限制聯邦政府權力的無限擴張,防止聯邦政府干涉和剝奪美國人民的自由”。不知瑞芬斯塔爾生前是否想過,倘若美、英、法三國也像她所心儀的國家權力至上而個人權利闕如的話,她會被“無罪釋放”,并安然活到101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