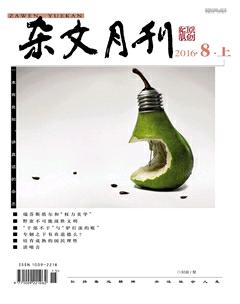他從來都不合時宜
周實
沒想到在這時候,在很多人都“告別革命”走向另外的方向的時候,他不但寫出了而且竟然出版了這樣一本書——《革命尋思錄》(林賢治著,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他在給我的信中說:“號稱‘革命起家的已經怕聽革命了,而我這個坐享‘革命成果的人居然還要說革命!這個話題,當今知識界大約已經厭說,兄當哂笑我太不識時務了罷?” 也許吧。也許我真這樣認為。識時務者為俊杰。但同時我也認為:不識時務者也許更俊杰。 編《書屋》時我曾經發過他的一些文字,其中大的有兩篇,都超過了十萬字。一篇題為《五四之魂》,針對的是當時文壇眾說“五四”不是的情勢,他偏要為“五四”招魂。一篇是《五十年:散文與自由的一種觀察》,我在那期的《編輯絮語》曾經這樣向讀者介紹:“此文從‘自由——這一獨特的視角切入,對近五十年來,中國散文的演變,作了全方位描述,并涉及當代文學的有關方面。在文中,自由是一個綜合性概念,既是人類學的也是社會學的,既是哲學的也是美學的。全文視野開闊,縱意評說,可謂一種‘文學史別裁。文章的頭兩章可看作導論部分。作者深入論述了文化生態環境、文學傳統、作家的生存狀態等問題及其相互關系,重點引向作品的生成。中間部分是作家論,是工細的文本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聲名煊赫的大家多有貶抑之詞,甚或略而不論,相反,對寂寂無名者則給予相當高的評價。究竟文學批評的標準何在?在結論部分,作者標舉自由感、個人性和悲劇性三者,試圖自行立法。作者這種把文學史納入人類精神史、講求通觀的做法,應該說是頗有見地的。多年前,學術界即有‘重寫文學史之說。在此,本刊不拘一格,發此長文,意在鼓勵探索。文學史寫作同文學一樣,唯在自由的探索和討論之中,才能走向真正的繁榮。其他學科也一樣。”其時,我想說卻又沒寫的更多的是私人著史。相對于國家項目而言,相對于集體項目而言,私人著史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一個傳統。只可惜在“解放以后”,由于意識形態的禁錮,被生硬地一刀斬斷。能夠承傳這一薪火,開啟當代的私人著史,在我看來是了不得的。 他從來都不合時宜,激情四溢的不合時宜,理性十足的不合時宜,極其現實的不合時宜。不但有激情而且很理性就是他的文字的特點。讀者只要讀他的文字就能通過他的文字看到他那火樣的激情究竟是為什么燃燒并且是怎樣的熊熊燃燒。《革命尋思錄》自然也一樣。讀時,我總感覺到他和羅伯斯庇爾(1758-1794,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領袖人物),血是一樣的,心是相通的。他是這樣寫他的:“作為法國大革命的一位象征性人物,羅伯斯庇爾的出現,打破了歷史家的單一的黑白構圖:一、從演說到行為,這是一個具有‘美德的人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卻要為大革命的恐怖殺人負責;二、他把他的同志送上斷頭臺,然后自己也步了他們的后塵;三、他如同革命一樣被人詛咒,但也始終不乏贊美之辭。他是圣徒,還是魔鬼?他是參加革命之后,具體說來是在掌權之后才變成魔鬼的?抑或本來就是圣徒,只是人們把他涂抹成了魔鬼?不同的歷史評價反映了人們諸多觀念的沖突。” 我曾囫圇吞棗地讀過羅伯斯庇爾。我腦子里記得的是他的模樣之英挺、步伐之輕盈、姿態之優雅,可媲美于貓。他天生敏銳的感受性激起了大眾的熱情,但在短暫的人生中,卻只戀愛過一次。從1789年春天起,他就告訴他自己:縱使冒著生命危險,也要捍衛人民的權利,除此之外,別無所求。他說:“對于正義、人性和自由而言,愛是一種與戀愛相等的熱情,受其支配的人,把一切獻給那種愛。”他的這種堅忍的自我犧牲精神,把他導入了一個悲壯的命運。他雖有預感卻不愿違拗。他說:“人既然來到人世,誰都不免一死。如果我的命運是為自由而死于非命,那么我不想逃避,寧愿勇赴那種命運。”不料竟然一語成讖,他真的在兩年之后在斷頭臺上與死神相遇。他最大的貢獻就是讓我們看到了民主的可貴,也看到了它的可怕。我最記得的他的話是:“平等是一切善的根源。極度的不平等是一切惡的根源。”我想我這一輩子都忘不了這句話。 關于《革命尋思錄》,這本書的前勒口上有段話寫得很準確:“這是一本隨筆式論著,革命構成它的主題。近代以來,革命以它特有的震撼改寫了世界歷史,它不但改變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版圖,也改變了廣大人們對社會前途和自身價值的看法。二百多年來,革命家、政治學者和歷史學家對革命作過各種不同的敘述與闡釋。作者涵泳其中,結合英國、美國、法國和俄國四大革命個案,介紹了相關的理論觀點,并根據某種內在邏輯進行整合;對革命的實質及一般性特征、革命與知識分子、精英與大眾、組織與權力、意識形態、社會動員、暴力、社會運動與改革、主權與憲政等諸多問題作出有意義的探討。全書采用尼采、本雅明式的斷片化形式,旁征博引,隨機生發,鋒芒閃耀,是敘事性、論辯性和詩性的結合。”人生難得一知己。這段話可謂是作者難得的知己了。 讀這本《革命尋思錄》,我還強烈地感覺到:革命是你想告別就能告別得了的嗎?回答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們該做的而且能做的應是大力地減少落后應是進一步消滅貧窮,讓人民的工作生活更加自由更加民主更加富裕更加和諧。何況就是再好的社會也要發展也要進步,自然也就會有革命,雖然革命的內容形式會因時代的不同改變。 最后,我還想引兩句話,也是這本書中引的。一句是美國的亨廷頓說的:“真正無望的社會不是受革命威脅的社會,而是無法進行革命的社會。”一句是南斯拉夫的伊沃·安德里奇說的:“沒有任何人的蠟燭可以一直亮到天明。” 革命最難的就是你有時非要革你自己的命。【童 玲/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