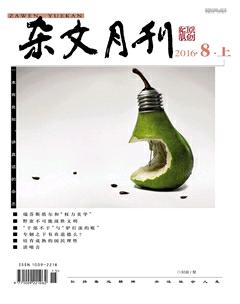雜文的歷久如新
符號先生在《我心儀的雜文》中說到雜文的“‘耐壓性(壓在編輯案頭數月上年仍歷久如新)”,這是雜文和時評的一大區別。其中的“歷久如新”也可進一步推繹為經得住時間(歷史)考驗。“時間”雖是最權威的文學批評家,但從激濁揚清、革故鼎新的社會功效來說,雜文和經得起時間考驗,別有關系存焉。
魯迅自述“愿我的文章速朽”,但大半個世紀過去了,先生之文有不少如今仍有強烈的針對性,就像是在指陳時弊。其文“歷久如新”,證明了魯迅揭露和針砭的種種國民性積弊,根系之發達、蔓延之深廣、歷時之久遠。其實,“如果被魯迅批判的中國文化中的弊端確實被魯迅的消毒劑消除了,那么,魯迅確實可以不再重要。但是看來這過于樂觀,所以,魯迅是不朽的魯迅”(張遠山語)。
以“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為己任的雜文,如在社會效用上“歷久如新”,那就說明所批評的不良事物“青春常在”,丑惡現象“駐顏有術”,而這有悖于雜文寫作之初衷。魯迅一語中的:“我以為凡對于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球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存留時,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熱風〉·題記》)試想中國的反腐敗斗爭如取得了全局性、決定性勝利,那么,眼下如過江之鯽的反腐雜文,自然也就與腐敗現象“同時滅亡”,而不再“歷久如新”。
有資深雜文家將歷年寫的雜文結集,其中不乏在1980年代為牛仔褲鳴不平、為個體戶正名之類。這些作品可謂“歷久則舊”,“時間”只是證明了作者當初說的沒錯。相反的情況如趙健雄為《醬香雜文集》作序時說:“二十年前針砭的問題與現象,往往二十年后仍大行其道甚至有過之無不及。”這樣的“歷久如新”,其實是雜文家不愿看到的。
賈士祥在《雜文的“與時俱進”》中說:“雜文與其他文藝品種相比,應該是‘易碎的。雜文直接而迅速反映社會現實、針砭時弊,社會生活發展變化了,這一階段雜文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如果一個時期雜文的生命是長生不老的,這不是什么好事,說明這個社會凝固了,沒有發展,沒有進步。”在具體的社會功效上,雜文最好不要“歷久如新”,而在藝術形式上當追求經得起時間檢驗。經典雜文不僅針砭對象具有根深蒂固的“歷時性”和舉一反三的普適性,而且藝術表現也堪以傳世。如今,因受“雜文時評化”的影響,在藝術性上“歷久如新”的雜文寥若晨星。不少人寫雜文就像參加知識競賽的選手那樣,比“搶答”時誰按鈴快。時效性是有了,但可讀性、耐讀性卻多有損折。而魯迅雜文的“歷久如新”,既在于所針砭之對象代有傳襲,也在于其文筆回味無窮。
符號先生為“野馬雜文漫畫叢書”寫的總序中說:“時弊不斷,積弊頑劣,雜文長存。”雜文因“時弊”的“不斷”和“積弊”的“頑劣”而“長存”,但雜文所針砭的假丑惡現象倘“歷久如新”,則是雜文的悲哀。【王 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