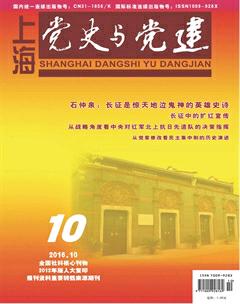從戰略角度看中央對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決策指揮
唐龍堯++駱小峰++俞曉嫻
[摘 要]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作為紅軍長征的序曲,無論其對第五次反圍剿的作用,還是在閩浙皖等省的影響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一些認為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悲劇是中革軍委的“錯誤決定”造成的觀點,本文從中央戰略的角度作分析,認為:一是中央決策紅軍攻打福州,不僅能夠造成更大的聲勢,更能吸引國民黨軍去守衛福州,從而減輕中央紅軍的壓力。二是繼續要求紅軍北上反映了當時中央決策者的意圖,即北上抗日先遣隊的重要任務是吸引和破壞,以減輕中央紅軍的壓力。三是前后矛盾電報的重要原因是,中央根據形勢變化,考慮部隊的不利的局面,才作出了這樣的決定。四是紅十軍團成立后第十九師為什么還要繼續北上,是因為當時中央紅軍處于不利的局面,需要外圍紅軍部隊采取行動,予以配合。五是紅軍湯口會師,是為了擺脫困境,化被動為主動。從而更為全面地看待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這段歷史,弘揚革命精神,還歷史以真實。
[關鍵詞]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央;戰略;決策
[中圖分類號] D2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928X(2016)10-0009-04
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決定由紅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率先北上,史稱“北上抗日先遣隊”。這支由6000多名指戰員組成、擔負著特殊任務的部隊,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孤軍深入,橫跨閩浙皖贛四省幾十個縣,行程達5600余里。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將士們,以不足一萬人的兵力,與十幾萬敵軍展開殊死搏斗,最后大部分壯烈犧牲,其中包括方志敏、尋淮洲、劉疇西、王如癡等一批紅軍高級將領。對北上抗日先遣隊失敗原因的研究,目前影響最大的是劉志青的《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悲劇》,文章中講到造成北上抗日先遣隊悲劇的重要原因是中革軍委的5個“錯誤決定”。此后,該文演變成為網上盛傳的《中共北上抗日先遣隊覆亡內情:中央做5個“錯誤決定”》等。其基本觀點是:在客觀上,是敵人力量的暫時強大,主觀上是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博古為首的中央組建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戰略決策不合時宜;在作戰指導上實行絕對集中的指揮,以致容易脫離實際,使部隊作戰行動陷于被動;加上先遣隊領導層意見分歧大,鬧不團結等等。
上述研究觀點,基本切合歷史事實,也有一定道理。但是,這些研究沒有從一個更大的視角,更寬廣的范圍,從整體的去看這一歷史,而是簡單的以結果來反推原因,總結歷史。本文試以《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悲劇》和《中共北上抗日先遣隊覆亡內情:中央做5個錯誤決定》(以下簡稱“兩文”)文中所提的中央5個“錯誤決定”展開,從中央戰略的角度作分析,以期更全面地看待這段歷史,還歷史以真實。
一、為什么要進攻福州,
兼評中革軍委的第一個“錯誤決定”
進攻福州,是“兩文”認為中革軍委所做出的第一個“錯誤決定”。為什么要進攻福州呢?1934年7月6日晚,紅七軍團從江西瑞金縣出發。31日,紅七軍團渡過閩江,占領古田縣黃田。遵照中革軍委原定計劃,紅七軍團接下去應該經浙江慶元縣、遂昌縣北上,直趨皖南。可是,紅七軍團先頭部隊剛到達古田縣谷口,就接到中革軍委電令:由谷口東進,占領水口,紀念“八一”建軍節,威脅并相機襲取閩侯縣(今屬福州市)。“兩文”認為紅七軍團改變進軍方向,不僅要轉一個大圈子,而且會暴露實力。因而認為,這是北上抗日先遣隊進軍途中,中革軍委做出的第一個“錯誤決定”。
1934年4月廣昌失守后,中央紅軍在蘇區內粉碎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已極少可能。中央蘇區的形勢極為惡劣,中央也因此開始實施戰略轉移的準備。而福州不僅是福建的省會,也是國民黨當時在福建的主要支點。與此同時,當時中央考慮日本有可能在此沿海登陸,中央政治書記處、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中革軍委會《關于組織北上抗日先遣隊給七軍團作戰任務的訓令》中就提到:日本帝國主義正加強著對福建、浙江沿海一帶的侵略。[1]
1934年6月1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明確提出:“在福鼎地區發展廣泛的游擊運動可能引起同日本海軍陸戰隊的直接沖突,在我們巧妙利用這種沖突的情況下,可以促使白軍士兵群眾轉移到我們方面來。”[2]所以,紅軍攻下福州,不僅能夠造成更大的聲勢,更能吸引國民黨軍去守衛福州,從而減輕中央紅軍的壓力。如果,日本侵略者如中央估計的一樣侵略福建沿海,那樣紅軍就可以直接與之作戰,直接體現黨的抗日主張,贏得全國人民的支援,從而有力推進抗日活動。事實也表明,中央的這一決策,引起國民黨當局震驚。福建省主席陳儀命令部署在閩東寧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剿匪”的第八十七師王敬久部集中到福州。蔣介石急調在湖北整訓的第四十九師伍誠仁部由長江水路和海運馳援福建。8月1日凌晨,紅七軍團占領水口鎮后。“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急忙趕到福州視察,并派部隊加強福州的防衛。日、英、法、美等以保護僑民和領事為藉口,先后派出軍艦進入馬江港。
結果卻是,中央過高的估計了紅七軍團的實力,也低估了福州國民黨軍的實力和所采取的措施,暴露了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實力。進攻福州受阻失利后,紅軍部隊只能繼續北上。
二、繼續北上的必要性,
兼評中革軍委的第二個“錯誤決定”
福州戰役后,紅七軍團先后攻占羅源縣城、穆陽鎮以及浙江的慶元縣城等地。由于一路行軍作戰,一直未得到休整。軍團長尋淮洲建議:紅七軍團就地進行短暫休整,總結經驗教訓,補充一些戰士。依托閩北蘇區打一兩個大勝仗,更大規模地發動群眾,發展游擊戰爭,創造更大的局面,然后跳躍式地向贛東北、浙西、皖南發展。但中革軍委指出:“擬于閩北蘇區休息,這恰合敵人的企圖,因敵人企圖阻止你們北進。”“兩文”也由此認為,這是中革軍委做出的第二個“錯誤決定”。
但看一下當時的總形勢,國民黨軍正向中央蘇區中心地區發起全面進攻:以北路軍直接指揮的六個師向江西興國縣推進;第六路軍四個師向興國縣古龍岡推進;第三路軍先以四個師進占江西廣昌縣頭陂,又集中九個師向江西寧都縣、廣昌縣驛前、石城縣推進;以東路軍為主的六個師由福建連城縣向長汀縣推進;南路軍三個師由江西尋鄔(今尋烏)縣筠門嶺向會昌縣推進。1934年9月初至10月上旬,中央紅軍在興國、石城方向,與國民黨軍展開了突圍轉移前夕艱苦的阻擊戰。可以說,很需要外圍紅軍的行動來化解中央蘇區的壓力。
1934年9月9日,紅七軍團遵照中革軍委的命令,離開閩北蘇區,北上浙西。在行軍途中,中革軍委來電要求:“不須以急行軍增加病員與疲勞,每日行二三十里。”[3]這一明顯不按常理的要求,反映了決策者的意圖,即北上抗日先遣隊的重要任務是吸引國民黨軍的注意力,破壞鐵路等設施,以減輕中央紅軍的壓力。此后,中央和中革軍委多次電令,要求“立即開始執行別動隊及游擊隊的任務”。[4]并強調:“在廣大地段上破壞杭(州)江(山)鐵路、調動敵人不是次等任務……對汽車、鐵路、電話線,應派隊盡量破壞,不應視為畏途。”[5]
對于七軍團未能完成破壞杭江鐵路,更是嚴電:“在未執行軍委給你們破壞杭江鐵道及其附近公路的任務前,軍委禁止你們繼續北進……”并要求“應派出兩個別動隊,每隊兵力一營,一個于常山衢州間破壞公路,一個于江山衢州間破壞鐵路”。在飛機在天上轟炸,地面遭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的情況下,先遣隊還是取得了較好的戰果,“焚毀賀村鐵橋及火車汽車各站”,“航頭大鐵橋被毀,割斷電報電話線斷絕我交通……”[6]北上抗日先遣隊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中央的要求和目的。
三、前后不一致電文的主要原因,
兼評中革軍委的第三個“錯誤決定”
9月17日,中革軍委電令:紅七軍團在未執行已賦予的破壞浙贛鐵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務,禁止繼續北進。18日,中革軍委卻電令:“應即向遂安前進,以襲擊方法占領該城,并確保于我軍手中。”[7]“兩文”認為,時隔一天,中革軍委的指示前后矛盾,使紅七軍團無所適從。
不過紅七軍團堅持執行中央命令繼續北上進入皖南,經過幾次戰斗,大體摸清了敵人的企圖和部署。此后,紅七軍團在皖贛邊地區打退追擊和堵截之敵,并補充了500名新戰士。尋淮洲、粟裕、劉英向中革軍委建議:紅七軍團留在皖贛邊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爭取在安徽休寧縣、祁門縣和江西婺源縣一帶消滅尾追之敵,擴大皖贛蘇區,尋機進入浙江。但是,中革軍委卻不斷指責紅七軍團,要求紅七軍團立即前往閩浙贛蘇區整頓補充。“兩文”認為,這是中革軍委做出的第三個“錯誤決定”。
其時,中央紅軍在興國、石城方向,正與國民黨軍展開艱苦的阻擊戰。情況瞬息萬變,考慮到破壞工作不能起到有效解決中央的壓力,不如讓紅七軍團繼續北上,發展新蘇區,特別是到離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較近的浙皖邊區建立蘇區,在保存紅軍力量的同時,更好地調動國民黨軍隊。這一戰略,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也強調:“當‘圍剿已經證明無法在內線解決時,應該使用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轉入我之外線敵之內線去解決這個問題。堡壘主義發達的今日,這種手段將要成為經常的作戰手段。”如10月8日,朱德關于七軍團發展蘇區與游擊運動問題致尋淮洲、樂少華電報中,就明確指出:“你們的行動不在無目的亂竄,而應有決心地在到達之地發展蘇區與游擊運動,以利紅軍主力活動。”[8]
這些前后矛盾電報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國民黨部隊已從幾個方面加速撲來,企圖堵死紅七軍團前進道路,實施多路合擊。部隊再不及時移動將更陷于不利的局面,弄不好會全軍覆沒。所以,才有了這些看似前后矛盾的電報。
四、紅十軍團成立后第十九師為什么還要繼續北上,兼評中革軍委的第四個“錯誤決定”
1934年10月下旬,紅七軍團進至閩浙贛蘇區,在江西德興縣(今德興市)重溪與紅十軍合編組成紅十軍團。根據中革軍委的指示,紅七軍團與閩浙贛蘇區紅十軍合編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團,紅七軍團改編為第十九師,紅十軍主力改編為第二十師。中革軍委要求“十九師于整理后應仍出動于浙皖贛邊新蘇區,擔任打擊‘追剿的敵人與發展新蘇區的任務”;“第二十師則仍留老蘇區執行打擊‘圍剿敵人與保衛蘇區的任務”。[9]紅七軍團從皖贛邊地區到達閩浙贛蘇區,通過敵人層層封鎖,付出了很大代價。此時,從閩浙贛蘇區返回原地區,則更加困難。“兩文”認為這是第四個“錯誤決定”。
從當時中央紅軍的整體情況來看,1934年10月7日,主力紅軍第一、三、五、八、九軍團先后向興國、于都、會昌地區集中,準備突圍轉移。9日紅軍總政治部發布政治指令,提出“準備突破敵人的封鎖線,進行長途行軍與戰斗”。10日開始,中央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等踏上戰略轉移的征途,開始了著名的長征。11月13日,鑒于中央紅軍西進甚急,深恐中央紅軍渡過湘江,進至桂、黔邊境,蔣介石在南昌發布了“追剿計劃”,以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同時又電令貴州軍閥王家烈,廣西軍閥白崇禧各派得力部隊分至湘黔、湘桂邊境堵擊,妄圖“殲滅”紅軍于湘江以東地區。
為減輕閩浙贛蘇區的壓力和策應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18日,紅十九師突破封鎖線,向浙皖邊出擊,繼續承擔北上抗日先遣隊的重任,“爭取運動戰中消滅敵人以創造皖浙邊蘇區”。[10]此后,尋淮洲率十九師通過靈活機動指揮,抓住戰機殲敵,渡新安江,逼近昌化、於潛(今於潛鎮,屬臨安市)、臨安,震動了杭州;又從浙江入皖南,克旌德縣城,一路北上,威脅蕪湖、南京。第十九師突然出動,讓國民黨軍始料不及,慌忙調兵遣將前堵后追。1934年冬,蔣介石集中正規部隊和各省保安團20多萬人,封鎖閩浙贛蘇區和“圍剿”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
在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的同時,10月28日,中央還命令紅二、六軍團從南腰界出發,挺進湖南,開展湘西攻勢。
為什么中央要如此命令,因為11月25日至30日,紅軍在湘江邊與國民黨軍浴血奮戰。為此,迫切需要外圍紅軍部隊開展行動,在減輕壓力的同時讓中央紅軍擺脫不利的局面。如11月25日,中革軍委電示紅二、六軍團:堅決深入湖南中部及西部活動,積極協助西方軍(即中央紅軍),紅二軍團主力及紅六軍團全部應集中一起,以突擊遭遇的國民黨軍正規部隊。這些就是當時中央會如此決策指揮的主要原因所在,而且這些決策行動也基本達到了中央的目的。
五、紅軍湯口會師是否必要,
兼評中革軍委的第五個“錯誤決定”
1934年12月7日,紅軍第十九師離開旌德縣城北上,威脅蕪湖縣,震懾南京市。就在此時,紅十軍團突然電令第十九師回師黃山,與第二十師、第二十一師會合。原來,在第十九師從閩浙贛蘇區出發后不久,中央軍區就電令紅十軍團:根據敵人對閩浙贛蘇區“圍剿”日益嚴重的形勢,紅十軍團立即率領第二十師、第二十一師轉到外線,同第十九師會合,在浙江開化縣、遂安縣、衢縣、常山縣之間集結兵力,爭取以運動戰消滅敵人,創建浙皖贛邊新蘇區。紅十軍團放棄根據地,全部出動到外線作戰。“兩文”認為這是第五個“錯誤決定”,使閩浙贛蘇區反“圍剿”幾乎沒有勝利的可能。
這一決策從戰略看,中央是以外線作戰的思想開展閩浙贛蘇區的反“圍剿”,在保證閩浙贛蘇區的同時,發展新的蘇區。所以,中央軍區關于十軍團行動任務及軍政委員會組成的決定致方曾劉樂尋聶電稱:“完全是為了調動敵人,保衛閩浙贛蘇區及創建新蘇區。”[11]
12月10日,第十九師到達安徽太平縣(今屬黃山市黃山區)湯口地區,與軍團部、第二十師、第二十一師會合。蔣介石得知紅十軍團全部脫離閩浙贛蘇區后,為避免出現中央紅軍的情況,立即電令“圍剿”,并調集20萬兵力,按“駐剿”“堵截”“追剿”的部署展開。“駐剿”部隊的任務,主要對付閩浙贛蘇區,重點對付紅十軍團。
紅軍湯口會師后,部隊士氣高漲,加上國民黨軍重兵“圍剿”,方志敏等領導人決定打一仗,以擺脫困境,化被動為主動,這就是譚家橋之戰。這一仗關系重大,是紅軍能不能在皖南站腳,完成戰斗任務的關鍵。遺憾的是,譚家橋一戰紅軍失利,損失慘重,尋淮洲因重傷不治身亡,軍團政委樂少華、政治部主任劉英等重要干部負傷。至此,北上抗日先遣隊開始陷于被動,直至懷玉山失敗。成為唯一一支中途失敗、犧牲慘重、未能最后到達陜北的紅軍部隊。
通過上述分析,中央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指揮從戰略意圖的角度進行審視,保障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實現安全戰略轉移,是中央派遣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出征的根本原因。在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長途跋涉、孤軍奮戰的6個多月時間里,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中央紅軍主力撤離上,對先遣隊沿途作戰的指導方針是預先制訂,簡單而明確,即“規定這次行動的最后到達地域為皖南”,并“要求七軍團在一個半月內趕到,支援和發展那里的革命局面”。在行動過程中,對于先遣隊提出的調整作戰路線等建議,中央都是再三強調北上戰略行動的重要性和特別意義,即不論在什么情況下“都不改變北上任務”[12],也“不要希望紅十軍及閩北分區的幫助”[13],“在部隊中應防止與堅決反對想縮回贛東北的情緒與企圖”[14],就是要求盡可能多的吸引和牽制國民黨“圍剿”軍隊,掩護中央紅軍主力實現從西南方向進行戰略轉移。中革軍委下達的作戰命令也都是圍繞這一戰略指導思路來部署的。
對于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行動,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寄予很大希望,做了大量準備工作,還讓紅九軍團專程護送紅七軍團渡過閩江。為了宣傳抗日救國主張,公開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等文件,并提出了“紅軍是工農自己的軍隊”“擁護紅軍北上抗日運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致對外,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福建”等口號。中革軍委下令紅九軍團在東線行動,專程護送紅七軍團渡過閩江。
“戰爭中一切行動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結果,而不是肯定的結果。”毛澤東所提外線作戰的思想,他實際是把運動戰的思路放到全國這樣一個大的棋盤上作出重新的定位,這可以說是深得運動戰之精髓,當時中央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指揮雖堅持運動戰的原則,但已難以發揮其曾經有過的威力。與此同時,國民黨軍也在不斷總結經驗,調整進攻部署。由此,中央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決策從戰略來講是一種必要和客觀形勢的需要,絕不能簡單的歸之于失誤,更不能說是錯誤。所以,方志敏、樂少華等領導人在反思材料之中都沒有責怪中央決策指揮的失誤,而是承認自身和軍團工作的不到位。當然,如果北上抗日先遣隊能夠如粟裕等人事后所總結的那樣,歷史或許可以重寫。
雖然北上抗日先遣隊失敗了,但是他們播下的紅色種子,卻在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崇山峻嶺生根發芽,不斷成長。指戰員們用血和肉凝聚成偉大精神,永遠值得繼承和弘揚。就如粟裕所說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斗爭歷史,首先是一部驚天動地的無產階級革命戰爭的英雄史”[15]。
參考文獻
[1][4][5][6][7][8][9][10][11][12][13][14][15]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21.89.94-95.429.102.125.139-140.453.145.92.85.95.260.
[2]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147.
[3]粟裕戰爭回憶錄[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119.
作者唐龍堯系中共杭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駱小峰系中共杭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宣教處副處長;俞曉嫻系中共杭州市委黨史研究室綜合處主任科員
■ 責任編輯:周奕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