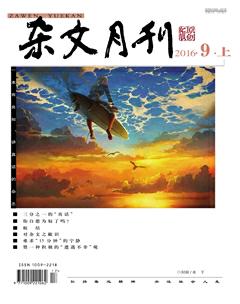人人是演員也是觀眾
夢麟
哈米先生在《生活中是沒有觀眾的》(《雜文月刊》2016年5月上)中,對于李銀河先生的《回歸生活的原始狀態》(《雜文月刊》2016年1月下)給予了批評。我有不同意見,不揣冒昧與先生商榷。
首先需要厘清三個概念。
“作壁上觀”(乃至幸災樂禍地“城隍山上看火燒”)。可李銀河說的是“回歸觀察”呀。這是否偷換了概念?
“明哲保身”。在李銀河《回歸生活的原始狀態》中看不出有“明哲保身”的意思,她在幾十年的生活實踐和學術實踐中也從沒有流露過這個意思,反倒是一直在與各方爭議對著干。“明哲保身”,是無中生有的概念。
“單純地‘看戲”。看戲是什么時候分“單純”和“復雜”兩種的?李銀河“單純地看戲”不能被容忍,她如果“復雜地看戲”就能被“包容”嗎?匪夷所思。哈米先生顯然是把“看戲”這個“單純”的概念復雜化了。
下面進入正題。
哈米先生對于李銀河突發奇想要當觀眾反應如此激烈,多余了。人生大舞臺,有戲臺就得有看臺,有演員就得有觀眾,沒有誰規定當演員就“對”當觀眾就“錯”,或者相反。一個人在社會上扮演什么角色,不存在是非判斷。
所有人都可以同時身兼演員與觀眾二職。即如哈米先生寫這篇文章時扮演的角色是演員,如蒙先生賞光讀我的這篇商榷文章,先生的角色就轉換成了觀眾。我們這些雜文作者既是觀眾也是演員,不當觀眾就掌握不了寫作素材;“胸有成竹”后在鍵盤上敲擊文章就成了演員。李銀河當觀眾了,她也還是一位演員,她社會學家的身份沒有變,她“觀察”,她“靜思”,也都是一種“表演”,只是橋段有所不同而已。
任何人都無法逃避一些特定的演員角色,如女兒或兒子、妻子或丈夫、母親或父親等。至于扮演其他社會角色,由于社會的進步,不再強求人人“只準”做“螺絲釘”,人人都有選擇角色的自由了。“適宜”扮演什么角色,只有自己知道,就是說,任何人包括李銀河,只能做自己。別說絕大多數人不“適宜”做哈米先生所列舉的孫中山、汪精衛、張志新、遇羅克、魯迅、聞一多、張治中、戴安瀾、趙一曼、楊靖宇、蔡元培、陳寅恪、顧準(按哈米先生的思路,這個名單可以無限排列下去),就連我“責令”我的兒孫做個雜文寫作者也不“適宜”,就像魯迅先生也無法讓他的兒子海嬰做他那樣的文學家。哈米先生又何必難為李銀河做孫中山……顧準們呢?實屬不經之談的是,因為李銀河舉了錢鍾書的例子,哈米先生即反詰曰“錢鍾書‘智慧了一次,他能‘智慧地逃過‘文革之災嗎!”天哪,就算是“超人”也沒有這種預測未來災禍的“智慧”呀。
李銀河更做不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妓女。以此責于李銀河,有不恭之嫌。如果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責于如今的“失足婦女”,她們肯定會歡呼雀躍趨之若鶩地捐款,因為那樣的話她們的“性工作者”身份就“合法”了,還可能因為反襯出了唯利是圖而沒有民族尊嚴的貌似尊貴者的寡廉鮮恥而成為受人尊重的羊脂球式的人物呢。這是哪跟哪喲!這幾近于魯迅不齒的“小說作法”了。
以馬丁·尼莫拉關于“沒有說話”的那段話責于李銀河,不對路。李銀河“沒有說話”嗎?她說過的話太多了,白紙黑字,微博微信,有目共睹,且不會速朽,是會記入歷史檔案的。
至于將李銀河的“看戲不入戲”上升到了“與政治密切相關”的高度,也夠令人驚悚的!
李銀河倒也是活該挨批。你想當一回觀眾,就本本分分安安靜靜地當唄,可她當慣了演員不甘當觀眾的寂寞,非得寫一篇勞什子《回歸生活的原始狀態》來“向蕓蕓眾生廣而告之”不可,這分明犯了“真話全說”的毛病。
《雜文月刊》發表的李銀河的文章是薦稿。薦稿人評說:“人生大舞臺,臺上臺下都是角色,不亂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將來,不念過往。如此,安好。”薦稿者讀懂了李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