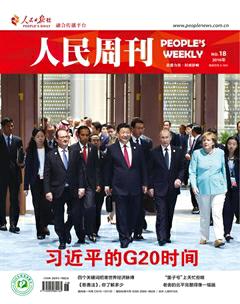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朝圣之路”
劉春雷
不論是專業人士,還是非專業人士,在互聯網的“桃花源”里,有太多的人被海量信息淹沒,可能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亟待博大精深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滋養。
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朝圣之路”上,有的人因路邊風景而駐足流連,有的人因道路崎嶇而畏葸不前。近十余年來,教育學比較知名的大學幾乎都不再開設“馬列教育論著”課程了。莫非真的“流風困暴豪”?不,“志之所趨,無遠勿屆,窮山距海,不能限也”。馬克思主義教育學并不因某些名校、某些名家的冷落而絲毫減少其科學性與生命力!
作為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教育學更強調以整體論、系統論研究人的全面發展,比如馬克思曾對教育與所有制關系的交互作用有精辟地論述:“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可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教育思想,有著更廣闊的歷史人文視野,而非局限于某一“專業”。遺憾的是,近年來無以復加的專業細分,不僅沒有帶來對教育實踐中一系列具體問題的創新研究,反而弱化馬克思主義教育學在學科建設、教育實踐的指導地位。用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指導教育理論與實踐,不是機械地從經典作家的論述中尋找與現實問題一一對應的答案,而是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教育智慧的群眾化。用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指導教育理論與實踐,不是空洞的原則,而是系統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從學科建設到學術研究,從宏觀教育政策到微觀教育技術等等,讓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的科學性在教育實踐中得以檢驗和發展。事實上,當前有關泛在學習、E-learning、“互聯網+教育”、教育游戲化、智慧教育等概念,并不都是有價值的東西,有的屬于概念翻新、有的科學性存疑。信息技術背景下的教育理論與實踐更需要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的指導,更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武器。馬克思主義從來不缺少科學的批判和批判的科學,而當前教育理論界缺乏的正是這一點。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貼近并明確回答這些具體的現實問題,才能彰顯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的生命力。當然,馬克思主義學說是發展的,而不是靜態的,教育學也不例外。馬克思主義教育學從來不拒絕吸收人類一切教育的成果,也不拒絕先進教育技術理念。只不過一些擁有西方話語權的教育權威人士不愿意承認這一點。
馬克思在其博士論文序言中寫道:“這篇論文如果當初不是預定作為博士論文,那么它一方面可能會具有更加嚴格的科學形式,另一方面在某些敘述上也許少一點學究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0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何其振聾發聵!一段時期以來,我國教育學術界在所謂的“學究氣”“科學范式”上過于追求形式主義的東西,忽略了經典作家科學思想的挖掘、運用與創新。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科學研究范式如此清晰,邏輯結構如此精美。教育理論界一些人卻陶醉于人為制造繁復而沒有技術含量的話語體系,搞什么本土范式、蘇聯范式、西方范式之類的界定,對西方流行的教育技術或者技術層面的教育頂禮膜拜,似乎以為披著技術的外衣就真的“高大上”了。濫用模型、怪異生澀,云里霧里,以形成專業壁壘,拒絕思想性的東西,汗牛充棟的教育文獻,高質量的實在太少,論文發表后,或束之高閣,或化為紙漿,身在文死,連“爾曹身與名俱滅”都做不到!一些研究馬克思主義教育學的人也不自信,捧著“金飯碗”要飯,轉而尋求更“時髦”的、更有“科學范兒”的教育理論。不客氣地說,有的教育理論工作者已經跌到了庸俗教育學的境地,實踐中自覺不自覺地回避、排斥馬克思主義教育學,甚至走向反面,這也是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的原因之一。
學習經典是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教育學的最好方式。學習經典,非下苦功夫、笨功夫不可。沒有吃透經典,就談不上繼承馬克思主義,遑論發展!讀經典相當于書法家臨帖基本功,當今一些頭銜顯赫的所謂“書法大家”,其作品之所以速朽,就是因為沒有臨帖的硬功夫,缺乏對傳統數十年如一日的忠實繼承。讀馬克思經典要比臨帖艱難得多,遠非所謂的“一萬小時定律”可衡量。讀經典,除了應作為教育學基礎理論的本科生、研究生重要學業,還應是專家的“必修課”。那些活躍在各種論壇、著述等身的名家、名師,在經典作家面前老老實實當一回小學生,會少些浮躁,多些沉思,他們名不副實的程度也許會不那么嚴重!比如,有知名學者公開發表的大作竟然將經濟基礎理解為硬的基礎設施,甚至以為馬克思主義沒有講什么是經濟基礎的基礎。可見,不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才會有如此無知無畏的言論;再如,馬克思相互教育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早就解決了的教學主體問題,但時至今日仍有大量文獻在重復性研究,甚至將尊重的教育看作是創新;還有,如果研究素質教育的人以為自己有什么創新,那么請看看恩格斯的原話:“大學都辦成這個樣:它最多只能造就在種種專門知識部門可能獲得比較高深造詣的專家,但無論如何不能給予在別的大學里可望受到的那種更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3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如果不是對馬恩經典視而不見的話,一定是對經典沒有讀透,就匆忙提出自己所謂的獨創。對待學術研究與創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一點也不為過。
沒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學家不是從學習經典走上學術之路的,離開經典作家的巨人肩膀,他們瞬間就成為理論的矮子!發展馬克思主義教育學所面臨的困境,固然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教育領域矛盾錯綜復雜方面的因素,但也有教育基礎理論界自身的問題。如果不那么在意自己頭上在名師、名家桂冠,不那么急功近利在影響力期刊上發文章,多花費一些精力從經典作家那里汲取更多的智慧,完整準確把握經典作家思想精髓,教育學的理論自信就會更富有穿透力、富有感染力!
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高峰不是孤立的,它矗立于教育基礎理論高原之上。教育理論界之所以沒有出現劃時代的大家,正是因為缺乏構造理論高原的一大批馬克思主義教育學家。如果能夠多一些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家(不一定局限于教授和研究員,還應該包括政策制定者、教育管理者),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就不會僅僅停留在政策文件的指導原則上,而是知行合一,也體現在政策條款和實施細節中,教育領域中長期困擾人民群眾的一些難題就會迎刃而解。教育改革完全可以少走許多彎路。比如大學合并、擴招,教育產業化、擇校等方面的教訓告誡我們,教育改革須臾不能偏離馬克思主義教育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
有的人因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生活、研究的時代背景已遠離我們,而懷疑其現實指導作用,那么請看馬克思有關教育公平的論述:“惟一還有的普遍的、表面的、形式的差別只是城市和鄉村的差別。在社會本身內部,這種差別則發展成各種以任意為原則的流動的不固定的集團。金錢和教育是這里的主要標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100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不知那些罔顧城鄉差別、收入差別而一味倡導所謂機會均等、程序正義的“教育家”們,看到了這段文字是否臉紅?那些從現象到現象研究教育公平的學者是不是因此有所反思呢?當然,今天的社會不同于當時經典作家筆下的市民社會,但其中蘊含的教育公平思想值得借鑒。
散見于馬恩全集的教育方面的論述浩如煙海,讀經典,對專業人士而言,可以從經典作家那里獲得新的感悟,增加馬克思主義科學素養,進一步提供理論自信;對非專業人士而言,可以跨越時空拜經典作家為師,沐浴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思想光輝。不論是專業人士,還是非專業人士,在互聯網的“桃花源”里,有太多的人被海量信息淹沒,可能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亟待博大精深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滋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