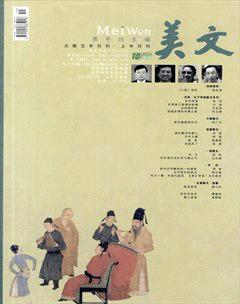他的城
祝正陽
對(duì)所有住在西安的人來說,西安,就是他們的城。或許有人從未發(fā)覺已經(jīng)錯(cuò)過了長安古意,就像夏蟬失約了洛陽花期,卻渾然不知。
他記憶開始的地方在那片田里,那個(gè)距西安84公里的小鎮(zhèn)。
與西安最初的牽絆源于他的母親。母親身上的頑疾每個(gè)冬天都會(huì)發(fā)作,就像是上好了發(fā)條的鐘。母親暗啞的聲音又開始嘶鳴,仿佛拼盡全力要把帶著血絲的腥臭液體干嘔出來。父親開動(dòng)著拖拉機(jī),但母親的咳聲仍清晰可辨。拖拉機(jī)一路顛簸來到西安,停在最繁華的街上,占了半個(gè)街道。
每當(dāng)父親扶著母親走進(jìn)醫(yī)院,他就在那里等待,盼著太陽快些垂到遠(yuǎn)處那片灰白的屋檐下。
當(dāng)黑徹底填滿這座城的時(shí)候,父親扶著母親出來了,一家人去醫(yī)院對(duì)面的老鴨粉絲館里吃飯。
他終于等來了自己想要的東西:破瓷碗里盛著老鴨粉絲,氤氳的水汽沖擊著干冷的空氣,香氣在日落月升間彌漫開,帶著無與倫比的暖意裹在他身上,落在門前的一大一小兩棵刺棗樹上。他認(rèn)為,這就是西安的味道。
那碗老鴨粉絲的余味能在他嘴角殘留好久,溫暖他一冬,或陪他看一樹花開,一樹花落。
他記憶中的冬天永遠(yuǎn)是暖的,因?yàn)槟亲形靼驳某恰?/p>
直到有一次只有父親一人出來,他才領(lǐng)悟到,原來悲傷也是一種無期徒刑。那天,他額角上落了一滴淚,是他這個(gè)年紀(jì)遠(yuǎn)不能承受的淚——那是從父親層層皺紋中流出的清淚。
那個(gè)沒有西安味的冬天冷了好久。
西安如同磁石般死死吸住他的命運(yùn),從前是,將來也是。他在西安念書時(shí),恰遇房?jī)r(jià)大跌,于是他入手了一間老屋,而且在一場(chǎng)細(xì)雨中邂逅了一個(gè)年輕美麗的姑娘……
他找到了他的城。他在西安。
一場(chǎng)雨季帶來一波人流,如織的人流變成一個(gè)個(gè)小黑點(diǎn)散落在這座城里,車站邊的垂柳又在一個(gè)個(gè)月夜靜默地看著這些黑點(diǎn)背著行囊,踏上一列列單程列車。
他仍在這座城里,點(diǎn)著煙,看火光點(diǎn)點(diǎn)燃盡時(shí)間。身邊的女人已不是那個(gè)年輕美麗的姑娘。他猛然想到自己那次去尋找老鴨粉絲館,誰知曾經(jīng)的舊城老巷成了如今的東大街,曾經(jīng)的刺棗樹成了如今的玻璃幕墻。他看著玻璃發(fā)呆,心中空空,只看到灰色的玻璃映著灰色的街,灰色的天和人們灰色的眼。
這座城人來人往,車水馬龍,身邊熟悉的臉龐不覺間消逝,陌生的臉又再一次次的遇然邂逅中變得熟悉,城也在一次次邂逅中有了自己的味:閑適,蒼涼,繁華……味道濃郁得卻無人品味,只留下了一座無味的城。
城是空的,里面盛滿了人釀的酒。酒是淡的,鐫刻著世間的影。
最后,還是有人不曾知道,這座城最有古意的時(shí)候,叫長安。
一扇城門隔開繁華與蒼涼,人們?cè)陂L安月下,一壺清酒,一束桃花。
甜美的夢(mèng)托起沉睡中的人們,浮在煙云叆叇的天上,整個(gè)長安也浮在天上,一夜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