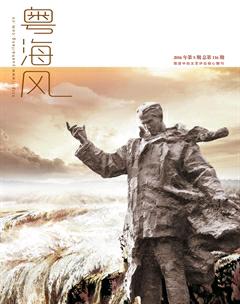領袖態度與刊物“仕途”
1957年1月,《詩刊》創刊,創刊號發表了毛澤東舊體詩詞十八首,并刊發了毛澤東給《詩刊》的信,引起很大轟動。此后,《詩刊》在其發展過程中,多次轉發毛澤東詩詞,其主編臧克家與毛澤東多有往來。但是,在看似“平穩”的表象后面,《詩刊》在路向選擇、編輯人員變更、領導標準等方面卻充滿曲折。毛澤東對文藝界的第二個“批示”下發后,1964年年底,它就首先遭到“清理”,成為“文革”開始前最早停刊的中國作協刊物。1976年元旦,《詩刊》復刊,是“文革”后第一家復刊的國家級刊物,復刊號再次發表毛澤東《詞兩首》,引起很大反響。《詩刊》在創刊和復刊兩個重要“節點”上都發表了毛澤東的詩詞,并獲得了很好的效果,其“文革”前的停刊也與毛澤東對文藝界的態度有很大關系。但實際上毛澤東除在創刊時給臧克家等人的信中說“祝它成長發展”以外,并沒有在任何場合表達過對《詩刊》的支持,也沒有表示過對《詩刊》的不滿。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雖然被《詩刊》編者成功地拉入其“作者隊伍”,他本人對于《詩刊》的態度還是隱晦、曖昧的。毛澤東與《詩刊》之間,可以說保持著的“若即若離”關系。《詩刊》的創刊、停刊、復刊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毛澤東的態度并非直接原因,但從毛澤東對它的態度中,可見《詩刊》生命歷程的復雜性,也可見政治領袖即文化領袖的特殊年代里文學發展的特殊生態。
一 、創刊時期毛澤東的支持
1956年秋天,隨著“雙百方針”在文藝界的執行,詩歌界感覺到有必要創辦一份詩歌專門刊物,為詩歌創作和評論提供陣地,于是,在徐遲的提議下,臧克家向中國作家協會黨組負責人劉白羽報告,竟“出乎意料”地得到批準,于是籌辦者徐遲、呂劍、臧克家等人通過走訪艾青、馮至、冰心、馮雪峰、魯藜、穆旦等詩人,獲得了認可和支持。同時,由于民間流傳著不少毛澤東詩詞,所以徐遲等籌辦者試圖將毛澤東詩詞的發表當作他們的刊物“打響第一炮”的籌碼,并“費盡心思”“日思也忖”,想要獲得毛澤東詩詞的發表權。經過馮至的建議,徐遲等人將搜集到的八首毛澤東詩詞認真抄寫后,于1956年11月21日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給毛澤東,請求毛澤東支持他們,幫助他們“辦好這個詩人們自己的刊物”,并請求毛澤東定正傳抄的八首詩詞后允許他們發表出來,同時也大膽地向毛澤東約求其他詩稿作品[1]。信發出后,由于籌辦者們均與毛澤東沒有密切交集,他們只能熱切地企盼著毛澤東能夠給他們回信。50天以后,當徐遲等人都已開始不抱希望時,竟意外地收到了毛澤東的回信。毛澤東在回信中不僅定正了徐遲、臧克家等人抄錄的八首舊詩詞,還額外地給了他們十首,同意他們發表,還寫一封信祝福《詩刊》成長,并說明他對詩歌的態度:詩應該以新詩為主,舊體詩可以有一些,但不適合在青年中流傳[2]。
毛澤東給《詩刊》編者回信并允許發表自己定正并增加了數量的詩作,被《詩刊》編者看作是對刊物的“一個最強有力的支持,一個最大的鼓舞”,他們表示“無比的興奮和感動”[3]。1956年到1957年這段時間無疑是共和國成立后文藝刊物的一個辦刊高潮期,陜西的《延河》、河南的《奔流》、天津的《新港》、浙江的《東海》、云南的《邊疆文藝》等一大批地方性文學期刊紛紛創刊,這首先得益于“雙百方針”的執行,也與1956年年底召開的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對刊物的重視有很大關系。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全國性的詩歌刊物”[4],《詩刊》歸屬中國作家協會所管,再加上主編臧克家、副主編徐遲以及編委中的艾青、田間、袁水拍等人,都是新中國成立前就有影響的詩人。因此,《詩刊》的創辦不僅要為詩人們打造一個陣地,還需要塑造其權威性,發揮其全國性影響,這樣,作為新中國成立前就有著辦刊經驗的臧克家、徐遲來說,能夠借助國家領袖的影響,讓剛起步的刊物為更多人所關注,必然成為他們為刊物“打廣告”的一個“殺手锏”;同時,在建國初期就開始的一系列文藝運動中,作為不是黨員也沒有身居要職的臧克家和徐遲來說,獲得國家體制的認可得以負責一份刊物,既是他們的榮耀,同時對他們來說也是一次考驗,之所以臧克家得知作協黨組織同意他們辦刊物時覺得“出乎意料”、徐遲被確定為副主編時的反應是“起初不愿意編刊物”[5],或許他們也是猶豫過的。而他們費盡心思力圖有點“巧思”地寫信懇請毛澤東允許發表其詩詞,就包含著借助國家領袖的光環保護刊物,以獲得合法性的意圖,同時,讓自己的刊物發表國家領導人的詩作,也間接地向國家領導人以及社會公布了刊物遵循國家領袖所規約的文學路線的編刊取向。
毛澤東同意并增加詩歌讓《詩刊》發表,還寫信表明自己的詩歌主張,祝它“成長發展”,說明毛澤東不僅支持這個全國性的專業刊物,也將自己看作一個詩人,將自己納入“詩人們”隊伍。既然如此,有這樣一個陣地,有這樣一個可以發表自己作品、表現自己詩歌主張的地方,毛澤東應該是會支持的。毛澤東同意發表自己作品,也是作為詩人的毛澤東,與發起創辦刊物的徐遲、臧克家等詩人們的“會合”,就如劉白羽在《詩刊》編輯部收到毛澤東的信時所說的那樣,這是“詩人和詩人之間有共同語言”[6]。毛澤東雖然沒有及時回復《詩刊》編者,但就其定正民間流傳的詩作并主動增加數量給《詩刊》發表來看,毛澤東對于自己的詩作的公開發表和傳播的態度是積極的,詩作的發表不僅能夠將他的創作才能告知天下,還連同他的信一起傳播了毛澤東的詩歌理念和主張,它們“使詩人們在創作上受到了巨大的啟示;解決了新舊詩的關系問題”[7],這也使得其后舊體詩詞存在的合法性得到確立,從而使得建國六七年來很稀見的舊體詩詞創作逐漸地浮現出來。寫信給臧克家等人后沒過幾天,還召見了臧克家和袁水拍,和他們談詩歌問題,他對臧克家的態度和藹,對臧克家提出的他的詩詞中的“臘”字的修改,以及對《詩刊》紙張要求,都欣然同意,還與臧克家等人談及自己的詩歌主張和觀點[8]。從這也可以看出,毛澤東不僅支持《詩刊》的發展,對當時的詩歌發展也是積極關注的。毛澤東是一個詩人,同時他對文學事業也有著自己的理想和觀念,支持《詩刊》創刊是他第一次公開展示自己的創作才能,也是他第一次作為文學活動的實踐者公開出現,他對詩歌的參與和關注,一定程度上活躍了詩歌氛圍,還為其后他發動新民歌運動做了鋪墊。
《詩刊》創刊時的毛澤東對它的態度,是《詩刊》得以順利“生產”并產生廣泛影響的重要因素。《詩刊》因此首先獲得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保障。據說,刊物創辦不久后的“反右”中,主編臧克家是有“右派”嫌疑的,但因為毛澤東接見過他、與他談過詩而免遭一劫[9];同時,對刊物銷量的擴大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當事者臧克家、徐遲、白婉清等后來仍津津樂道于民眾大冬天排隊購買《詩刊》創刊號的情形,足見當時的需求量之大,需求量大必然使得刊物銷量增大,后來因為讀者需求量大,《詩刊》編者還重印了創刊號。這樣,加上前述的對詩歌發展方向的影響,毛澤東對《詩刊》的支持,實際上起到了政治、文化和商業等方面的多重效果。
二、毛澤東與《詩刊》的“若即若離”
臧克家在建國以前就編過刊物,他深知發表重要人物的作品對刊物的重要性,此時他作為《詩刊》的主編,又曾及時講解、闡釋過毛澤東詩詞,在毛澤東發表十八首詩詞后不久即出版了《毛主席詩詞十八首講解》,毛澤東又召見過他談論詩歌,因此他借助能接觸毛澤東的“便利”,有機會就向毛澤東約稿。收入《臧克家全集》里的兩封書信,也能看出當時臧克家積極向毛澤東約稿的情況。1958年6月份給毛澤東的信中,臧克家首先就向毛澤東約稿,他說“您到全國各地視察工作,許多新鮮事物,一定會引起詩興,如有新作,希望給《詩刊》發表”。1961年12月27日給毛澤東的信中,也說“您手頭如有寫定的詩,順便寄幾首來,沒有,將來再說”[10]。從他與毛澤東的交往來看,他的信件不止這兩封,且其他信中也常向毛澤東約稿。
1958年臧克家給毛澤東的信,現有資料無法知道毛澤東有沒有回復,但是,就當時的情況來看,沒有回復的可能性比較大。臧的信是6月份寫的,當年7月1日,毛澤東就寫了兩首詩,即《七律兩首·送瘟神》,當日,毛澤東寫信給胡喬木,說明寫作原因,并“請你同《人民日報》文藝組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請告訴我。如可用,請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不使冷卻”[11]。按理,當時臧克家寫信給他不久,臧克家約稿態度誠懇,他此前與毛澤東也有往來,《詩刊》又是專門性詩歌刊物,而且從1958年1月號開始,開辦了“舊體詩”欄目,毛澤東有詩詞作品問世,應該首先照顧《詩刊》才對,可他卻先想到“投稿”《人民日報》,這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這當然可以有多種可能性,如他或許沒收到或者沒看到臧克家的信;或者他覺得他的“宣傳詩”不適宜在文藝刊物《詩刊》上發表,而適合在黨報《人民日報》上發表等。具體原因,已無法得知。毛澤東的這兩首詩,整整三個月后,才于10月3日的《人民日報》上刊載出來,據當事者說,這是因為毛澤東后來又將詩歌索回去進行修改了[12]。但為何不給《詩刊》發表,仍令人奇怪。
將近一年后,1959年6月底7月初,毛澤東又作了兩首詩,即《七律·過到韶山》和《七律·登廬山》,在詩作寫了兩個月后的9月1日,他寫信給臧克家和徐遲,信開始時說“信收到。近日寫了兩首七律,錄上呈政。如以為可,可上詩刊。”第二段以不短的篇幅分析“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的情況,最后表明“我這兩首詩,也是答復那些王八蛋的。”[13]從信的內容來看,這是一封回信,但是沒有毛澤東大部分回信中的“遲復為歉”,說明不是對去年6月份臧克家信的回信,也不可能是對好幾個月以前的信的回信。因此可以推斷在他寫完詩到寫這封信期間,臧克家或者徐遲曾以《詩刊》的名義給他寫過信約過稿,這封信是對約稿者的回應。同時,從毛澤東能夠花兩三百字的段落在信中“推心置腹”地談論他眼中的政治形勢,也可以看出他對收信人的信任。可以看出,他給自己的作品征求意見并同意發表,態度是誠懇的。奇怪的是,這兩首詩始終未在《詩刊》上發表,而直到四年后出版的《毛主席詩詞》才首次面世,其中原因,也耐人尋味。從臧克家、徐遲的角度來說,毛澤東同意發表自己的作品,對于《詩刊》來說,是求之不得的,而且它在1959年6、8、9、10、11月號都發表了舊體詩詞,看來他們也正需要稿源,所以最終沒能發表的原因,應是毛澤東又改變了主意。究竟如何改變的,也不得而知。
1961年毛澤東曾三次回信臧克家,4月24日的信開始表示“來信及附文收到”,并表示“頗有一些事想同你談一談”;11月30日的信說“惠書收到(兩次),因未能如愿面談”,“明年一月內”如找得出時間,要找臧克家和郭沫若一起談一談;12月26日的信又表示“幾次惠書,均已收到,甚為感謝。所談之事,很想談談”,并表明“我對于詩的問題,需要加以研究,才有發言權”[14]。由幾次回信可以看出,其間臧克家多次寫信給毛澤東,臧所寫的信以及附文內容究竟是什么,暫無資料可查證,但從毛澤東的第三封回信中可知是有關詩的問題,而且就毛澤東與臧克家、郭沫若之間的往來看,可能是關于舊體詩詞的;另外,1961年臧克家寫過《精煉·大體整齊·押韻》闡釋毛澤東的詩歌觀念,也寫過《毛主席親題魯迅詩》《再談毛主席親題魯迅詩》《毛主席詩詞欣賞——讀〈沁園春·雪〉、〈長征〉》等幾篇關于毛澤東詩詞的文章,他寫的信也有可能就相關問題請教毛澤東。毛澤東的三封回信,表明臧克家所請教的問題毛澤東是很重視的,對此,臧克家反倒誠惶誠恐,他在12月27日及時回信毛澤東,并表示了讓毛澤東“為了會面談詩分神”的不安,但他仍不忘記向毛澤東約稿[15]。可惜的是,這幾次信件中所談到的會面計劃,最終也沒能實現。
《詩刊》創刊號發表毛澤東詩詞獲得很好的反響之后,“文學國刊”《人民文學》也積極爭取毛澤東詩詞的首發權,其編者仿照《詩刊》創刊時的“請批”模式,將從鄧拓那兒搜集到的毛澤東詩詞抄送并請求毛澤東改定后允許發表。1962年,毛澤東對陳白塵等人的請求有了回應。他在定稿之前,請人提供修改意見,臧克家就是其中之一。臧克家在提供了自己的修改意見之后,可能給毛澤東寫過幾封信,順便請求毛澤東的詩詞也能同時在《詩刊》上發表。毛澤東在4月24給臧克家的信中說“數信收到”,然后答復臧克家說“同時在兩個刊物發表,不甚相宜,因為是《人民文學》搜集來的”,并告訴臧克家“另有幾首,可以考慮在《詩刊》上發表”,還詢問了《詩刊》5月號的出版時間。然后才回到臧克家的修改意見上,他大力稱贊臧克家的修改“改得好,完全贊同”,并繼續詢問臧克家是否還有可以改動的地方。臧克家大概后來又“遵命”繼續作了修改后上呈,并再次詢問毛澤東“考慮”在《詩刊》上發表的作品,4月27日,毛澤東又回信臧克家,說詩詞“應當修改的地方,都照尊意改了”,然后答復臧克家“唯此次只擬在《人民文學》發表那六首舊詞,不在《詩刊》再發表東西了。在《詩刊》發表的,待將來再說。”[16]關于《人民文學》編輯部搜集“請批”發表的詩詞作品數目,周明和涂光群說是十幾首,陳白塵說將近二十首;但宋壘和黎之說只是詞六首,他們還在文章中提供了傳抄稿。幾個人各執一詞,難以定論[17]。如果按照周、涂、陳的說法,那么毛澤東說的“另有幾首”,有可能是其他幾首《人民文學》搜集了他不愿意在其上發表的作品;如果按照宋、黎之說,又有可能是此前答應發表的《七律》等作品。讓人疑惑的是,毛澤東在短短三天之內“反悔”,將答應過臧克家在他們刊物上發表作品的“允諾”自我否定掉,究竟是出于什么考慮。若說臧克家請求毛將《人民文學》搜集到的詞作在他們的刊物同時首發,確實不太合理,那么答應發表“另外幾首”,應無不妥之處,畢竟《詩刊》是專門發表詩歌的刊物,發表詩詞作品是理所當然的。
毛澤東雖然拒絕了《詩刊》對《詞六首》的首發權,也推延了答應發表其他作品的時間,但是,《詩刊》轉載《詞六首》的權力并沒有受到限制。《詩刊》在1962年第3期上,以刊頭位置赫然刊載了毛澤東的《詞六首》,并在文末用小字備注說這幾首詞最先發表于《人民文學》第5期。但是,這時候的《詩刊》是雙月刊,每單月10日出版,此期出版時間標示為“5月10日”,而《人民文學》此時是每月12日出版,發表《詞六首》的第5期是按時出版的,標示時間是“5月12日”。也就是說,單純按照刊物標示時間來看,毛澤東的六首詞是首先面世于《詩刊》的,只是它標明了其“首發權”歸于《人民文學》。就當時臧克家幫助毛澤東修改作品來看,他拿到作品定稿的時間跟《人民文學》獲得毛澤東詞的定稿的時間應該差不多,因此在刊發毛澤東作品同時,《詩刊》發表了臧克家的《讀毛主席〈詞六首〉》,《人民文學》發表了郭沫若的《喜讀毛主席的〈詞六首〉》,贊美并賞析毛澤東的詞作,但臧克家文章的署名時間是4月30日,郭沫若的署名時間為5月1日,臧克家如此迅速地寫就文章,可能與刊物出版的時間、對國家領袖詞作的喜愛等有關,但也難免給人搶占話語先機之嫌,說明刊物對國家領袖所帶來的影響和效應是十分期待的。
臧克家這次的積極爭取,得到了毛澤東的一個空頭支票。就像此前毛澤東多次答應約他見面談詩始終未能如愿一樣,這次毛澤東的“將來再說”,直到毛澤東逝世,也沒能實踐。1963年1月,毛澤東寫過一首和郭沫若的詞《滿江紅·和郭沫若》,大概是要踐行1962年信中對臧克家的承諾,他于3月囑咐林克寫信給臧克家,讓將這首詞發表于《詩刊》。林克在信中說“主席囑將他這首《滿江紅》詞送詩刊發表。詞內用了三個典故:‘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請詩刊作注后,再送主席閱。主席詞發表時請附郭老原詞。”[18]然而,這首《滿江紅》的命運與1959年的兩首律詩一樣,最終也未能在《詩刊》露面,等到年底出版的《毛主席詩詞》面世之后,它才首次公開。
這些本來有望在《詩刊》發表的詩詞作品,《詩刊》最終都失去了首發權,只能以“轉載權”在《毛主席詩詞》出版后,第一時間于1964年1月號予以轉載。毛澤東幾次允諾將自己的作品給《詩刊》發表,最后又“反悔”,有可能正如袁鷹、陳白塵、宋壘等人說的那樣,是因為他對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的修改態度有關,但是從屢次對《詩刊》“放鴿子”的行為中,也可見他對《詩刊》的態度的“曖昧”,一方面他積極支持刊物的發展,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也防止《詩刊》對他的作品發表權的壟斷。
三、毛澤東關于文藝的“指示”
與《詩刊》的停刊
在毛澤東與《詩刊》的“曖昧”過程中,《詩刊》本身的另外一些改變也在悄悄進行。先是1959年臧克家病重,住院“八九個月之久”[19];然后是1960年,副主編徐遲被調到湖北;4月號開始,調阮章競當副主編;11、12月號開始,因“需要加強黨的力量”,調是黨員的葛洛當副主編,徐遲不再擔任副主編;1962年第1期起,阮章競又被調走,副主編只剩葛洛,從此以后,主要負責刊物的,實際上是葛洛,直到停刊。1960年年底調來葛洛后,《詩刊》已經有了三個黨員,即葛洛、吳家瑾和丁力,組成了黨小組,后來還改建成支部。根據臧克家女兒鄭蘇伊的說法,臧克家1959年以后“一直受壓制”,對于刊物,他“只是業務上把把關,政治上是沒有發言權的”,到以后“有黨員就基本撒手了,有時出版前看看”。無論鄭的說法是否真切,但可以肯定的是,《詩刊》內部的人員變動,對刊物的發展變化,是有很大影響的。1963年12月,也就是《毛主席詩詞》出版前后,毛澤東對文藝界的第一個批示下發,他雖然在批示中說“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但整體上還是批判的。此后,文藝界開始整風。1964年6月,毛澤東的第二個批示下發,對文藝界的批評更加猛烈。在作協的幾大刊物中,最重要的是《文藝報》,其次是《人民文學》,當然要設法保住,為此,文藝界領導采取“舍車保帥”,《詩刊》“地位不如人家”,為了“有所表示”,便被停刊整頓,以“向上面交代”[20]。
《詩刊》雖然貴為“詩歌國刊”,但在作協的報刊體系中,它只是一個次要刊物而已。由于它一直較為“聽話”,在越來越復雜的政治運動中已無多少自主權;而這個時候的毛澤東,作為創刊時幫助《詩刊》打響第一炮的重要作者,已經完全游離于其作者群體之外。毛澤東的以上幾個“放鴿子”行為,已經表明毛澤東對《詩刊》“不離不棄”實際上是“保持沉默”。創刊時候《詩刊》因為毛澤東的關系獲得合法性,如今既然“支撐”者已經遠離,它的命運也可想而知。更有甚者,毛澤東從其作者群游離后,《詩刊》發表或爭取毛澤東詩詞,也由創刊時候的榮耀和“保護傘”,變成了現在的“罪證”。據說,當時作協黨組書記劉白羽向中宣部報告,《詩刊》“近年來更發展到妄圖壟斷主席詩詞發表權,招搖撞騙,極其惡劣。編輯部成分復雜,黨員力量薄弱,實際上整個編輯部已被資產階級所溶化,我們建議停刊或暫時停辦,以后看情況,再決定辦不辦。”[21]這里的“妄圖壟斷毛主席詩詞發表權”,也許更多的是針對主編臧克家三番五次向毛澤東約稿而言的,但實際上臧克家的約稿均以失敗告終,《詩刊》很長一段時間只有毛澤東詩詞的“轉發權”,因此這實際上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另外,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從1962年以后,文藝界所討論的文藝內容,已更多地偏向于小說、戲劇、電影,尤其是戲劇,詩歌受重視小可能是《詩刊》被邊緣化和停刊的原因之一;而在當時的文藝活動中,《詩刊》對國家層面的政策,一直扮演的是“順從者”角色,如及時響應和踐行“反右”“新民歌運動”“大躍進”等,它被停刊卻沒有任何抵抗,還有它再一次發揮“順從者”作用的嫌疑。在當時的整風中,編者多被下放“四清”,當時夾在停刊號里宣告自己停刊的“停刊通知”中說:“目前,我國各個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群眾運動正在蓬勃開展。為使本刊編輯部工作人員有較長的時間深入農村、工廠,參加火熱斗爭,加強思想鍛煉,本刊決定從1965年元月暫時休刊。這一積極措施,一定會得到您的支持。”這與此前《詩刊》積極響應各種政治運動的做法是一致的。
四、權力博弈中的“奉命”復刊
《詩刊》停刊后,毛澤東與臧克家等人的交往也基本終止了。20世界70年代初開始,出版界開始復蘇,因“文革”爆發停刊的期刊也蠢蠢欲動,各地方刊物紛紛復刊或者創刊,但國家級別的文藝刊物卻很長時間都沒能復刊。1975年7月的一次與鄧小平談話中,毛澤東開始表示對當時的文藝政策不滿,說“百花齊放都沒有了”,“沒有小說,沒有詩歌”,此后不久,在與江青的談話中他又表示“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22]。這樣,國家級別的文藝刊物的復刊也提上日程。9月19日,毛澤東批準了山東省教師謝革光7月份寫給《紅旗》雜志建議復刊《詩刊》的信。11月15日,《詩刊》編輯部采用創刊時的策略,搜集兩首毛澤東寫于1965年的詞作傳抄本,寫信請求毛澤東改定后,“連同主席新寫的其他詩詞,給重新出版的《詩刊》第一期發表”。毛澤東改定之后,沒有增加篇目,批示“送詩刊編輯部”[23],表明同意《詩刊》復刊并發表自己的詩詞。由此,《詩刊》編輯部欣喜萬分,將本來打算于1975年1月10日出版的《詩刊》,提前到元旦出版[24]。
此時籌備出版的全國性刊物,除了《詩刊》,還有《人民文學》,被命名為《詩刊》主編的李季,在“文革”前本來是《人民文學》負責人,“文革”中也被下放,1972年被調回北京,準備復刊《人民文學》,卻在當時的政治權力博弈下遭遇失敗,最終不了了之。《詩刊》籌備復刊時,他卻突然被“任命”為《詩刊》主編,這是很有意味的。李季在“文革”中表現較好,受到的沖擊比大部分其他作家小,1972年他任干校5連支部書記,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不久就被調回北京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并在此期間籌備《人民文學》復刊;他本身是黨員,政治上有“老到之處”[25],僅從1972年年底后《人民日報》屢次提及他公開參與文化活動,就知道他已被當時文化界主流所認可了,選擇他負責復刊后的《詩刊》,應是領導人慎重考慮的結果。停刊前的《詩刊》,主編臧克家不是黨員,后來長時間負責工作的葛洛,原本是《人民文學》的副主編,因為《詩刊》缺少黨員,同時在《人民文學》“犯錯誤”,才被調到《詩刊》任副主編,他主持的《詩刊》,比較謹慎,沒顯露出多少特色,以致最后毛澤東從其“作者群”疏離,《詩刊》也被停刊。復刊后的葛洛因為有黨員身份,仍為副主編,非黨員的臧克家則只是顧問。《詩刊》復刊,據說“是主席同意的。主編、編委名單是鄧副主席帶頭圈定的”[26];據臧克家所言,則毛澤東也參與“圈”定復刊后《詩刊》負責人:在1977年11月28日給馮牧的一封信中,臧克家說“主席又圈了李季同志‘主編,我‘顧問”[27],參與《詩刊》復刊工作的王春回憶當時的情形時也說,“在‘文化大革命初被迫停刊的《詩刊》經毛澤東批準復刊,并指定李季同志為該刊主編。”[28]此時毛澤東對于《詩刊》的這些積極主動的態度,比起《詩刊》創刊時和停刊之前,是有很大不同的。
在70年代復雜的政治形勢下,文藝完全為政治所控制,《詩刊》要復刊,必須得到政治允許。1972年李季等人試圖復刊《人民文學》的嘗試,說明知識分子,尤其是重新獲得認可的知識分子,試圖恢復他們的文化權利,但當時的文化控制權,很明顯的是在極力支持和鼓吹“工農兵”是一切領域的主人的派別的手中,因此李季等人的活動得不到國家最高權力擁有者的知曉與支持,必然導致失敗。1975年后,由于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發話”,《詩刊》《人民文學》的復刊才有了新機,而領導人的同意和“圈定”負責人,使得知識分子爭取權利一定意義上取得成功;但當時的文化權力博弈仍十分激烈,據說在國家領導人圈定李季為《詩刊》負責人時,還有“拍馬文人”奉“四人幫”的“旨意”來游說他讓他出馬當主編,李季最終選擇了“黨中央”;而即便是復刊以后,《詩刊》仍需要面臨文化權力博弈和選擇:編者選擇延續1957—1964年的《詩刊》而延續了其期號,以“復刊”的名義重新出版,因此受到“四人幫”的責難;而《人民文學》則似乎以“洗心革面”的姿態出現,它選擇了重新排期號并以“創刊”的名義出現,就沒有受到為難[29]。據此也可以管窺到當時政治、文化權力博弈的復雜性。
毛澤東的“同意”《詩刊》復刊,并同意發表自己的作品,在重新出版的《詩刊》獲得合法性上,是起到巨大的作用的,由刊物得到允許就籌劃提前出版即可知,它不僅是響應國家領導人的結果,也是國家領導人關注文學發展的體現。從毛澤東主動、親自參與“圈定”《詩刊》負責人,以及突然讓李季負責該刊,也可以看出,《詩刊》的復刊,更多的是最高領導人意志的體現。因此,據說當所謂“四人幫”責難李季時,他能夠義正詞嚴地以毛澤東的支持作為“擋箭牌”[30]。從毛澤東“呼吁”,到“同意”,再到“命定”負責人,《詩刊》的復刊已經失去了1957年創辦時候由詩人們自動發起的“自由”文化品格,而變成了被國家政治所操控、為國家政治服務的刊物。因此,復刊后的《詩刊》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僅繼續扮演著作為黨和國家的文藝政策的“注腳”的角色,更充當著國家政治運動的注釋者和擁護者角色,其所刊載的內容,如一系列批判運動、國家領導人的變更等,幾乎將刊物變成了政治新聞場域與政治斗爭陣地。直到1978年開始,經過它自身漫長的自我覺醒和斗爭的過程,它才逐漸變回比較純粹的“文藝刊物”。
結語
誠然,毛澤東的身份的多重性決定了他不可能一心一意關注詩歌的發展,但是,作為詩人的毛澤東,尤其是主要創作舊體詩詞的毛澤東來說,怎樣將自己的詩歌(文學)主張表達出來,將自己的作品公之于眾,本身就是一個難以把握的問題,因為自從新文學產生以來,舊體詩詞的生存空間已受到很大的擠壓,所以他的個人愛好與詩歌發展形勢之間必然有不一致的地方。50年代末毛澤東提倡“新民歌”運動時,就主張發展舊體詩詞與民歌“結婚”的新民歌,以踐行廣大民眾參與文學建構的全民文藝理想。《詩刊》畢竟是一份新文學語境中產生的文學刊物,但是作為國家機關所主辦的刊物,它一方面需要擔負促進詩歌發展的任務,另一方面又必須承擔文藝的國家性指導功能、起到模范性作用。毛澤東與《詩刊》之間的復雜關系充分說明,作為作者和國家領導人的毛澤東和作為國家級文學刊物的《詩刊》,也不能時時刻刻保持文學方向的一致性。更多的時候,《詩刊》積極向毛澤東約稿,或許只是為了增加自己影響力、確立自身合法性的砝碼;而毛澤東對《詩刊》態度與行為的矛盾,或許也是尋求自己的詩性表達與怎樣中和文藝界文學力量的矛盾的結果。無論如何,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在詩歌領域所發揮的作用是極其強大的,《詩刊》在其發展歷程中也始終沒有背離毛澤東的文藝路線,因此兩者之間的微妙關系,就更多地體現出在政治標準第一的年代里,文學刊物怎樣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以及它怎樣得到政治認可的復雜性。
參考資料:
[1] 該信全文見《〈詩刊〉編輯部給毛主席的信》,《詩刊》1997年第2期。
[2] 該信全文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頁。
[3] 《詩刊》1957年創刊號《編后記》。
[4] 臧克家:《我與〈詩刊〉》,《臧克家全集》第六卷,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頁。
[5] 二人的心態見臧克家《我與〈詩刊〉》(《臧克家全集》第六卷,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頁)、徐遲《慶祝〈詩刊〉二十五周年》(《詩刊》1982年第1期)。
[6] 徐遲:《慶祝<詩刊>二十五周年》,《詩刊》1982年第1期。
[7] 《詩刊》1957年第12期《編后記》。
[8] 臧克家:《人去詩情在——紀念毛澤東同志百歲誕辰》,見《臧克家回憶錄》,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420頁。
[9] 《世紀老人的話——臧克家訪談錄》,見《臧克家全集》第十二卷,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614-615頁。
[10] 以上兩封信,見《臧克家全集》第十一卷,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360頁,其中1958年那封信具體日期不詳。
[11] 此信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頁。
[12] 袁鷹:《風云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123頁。
[13] 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489頁。
[1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611、614頁。
[15] 見《臧克家全集》第十一卷,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頁。
[16] 以上兩封信均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3、84頁。
[17] 以上各種說法,分別見涂光群《毛澤東詞六首發表內幕》(《五十年文壇親歷記(1949—1999)(上)》,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頁)、陳白塵《回憶〈詞六首〉的發表》(《新華日報》1978年12月24日)、宋壘《千錘百煉 滿眼輝煌——毛主席對〈詞六首〉的改定》(《中流》1993年7月號)、黎之《毛澤東詩詞的傳抄、發表和出版》(《文壇風云錄續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322頁)、周明《毛澤東與〈人民文學〉》(《文壇記憶》,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頁)。
[18] 此信見《毛澤東關于幾首詩詞寫作、發表的幾封信(1963—1965)》,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1期。
[19] 臧克家《我與〈詩刊〉》,見《臧克家回憶錄》,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頁。
[20] 以上《詩刊》的停刊過程,根據連敏對吳家瑾、白婉清、鄭蘇伊、尹一之等人的采訪綜合而成。連敏的采訪文章于2007年以《重返歷史現場——關于〈詩刊〉(1957—1964)的訪談》發表于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編的《新詩評論 2007年第一輯》,2010年以《重返歷史現場——吳家瑾、白婉清、鄭蘇伊、尹一之、聞山、王恩宇訪談》發表于吳思敬主編的《詩探索 2010年第二輯 理論卷》。兩文內容略有差異。
[21] 劉欽賢提供的丁力回憶錄內容,轉引自連敏的博士論文《〈詩刊〉(1957—1964)研究》,首都師范大學2007年,第91頁。
[22] 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446頁。
[23] 以上關于《詩刊》復刊經過,總結于《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8、609、623、624、627、628頁。
[24] 張光年:《向陽日記》,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頁。
[25] 關于李季的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表現,可參見涂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歷記》(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230、231、416、417頁相關敘述。
[26] 郭小川1975年11月6日致曉雪信,見《郭小川全集》第7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36頁。
[27] 見《臧克家全集》第十一卷,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頁。
[28] 王春:《我在詩刊社的日子》,《詩刊》2006年第5期。
[29] 對此的相關考察和論述,可參見張自春:《從同人刊物到詩歌“國刊”——〈詩刊〉1980年前的轉變歷程》,《文藝爭鳴》2015年第3期。
[30] 袁鷹:《直到最后一息——哭李季》,《人民文學》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