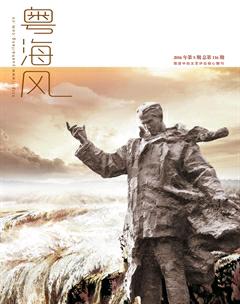乞巧拜仙,金針度人
近十年來,每年的七夕期間,廣州地區的天河、黃埔、番禺等地婦女的乞巧傳統,經媒體宣傳,其影響越來越大。期間雖然多有政府主導的各種宣傳展示活動,但與七夕有關的習俗卻一直在民間鮮活地傳承,該傳統其來有自。舊時,農歷七月初七日,廣州地區未婚女子為七娘會,陳花果作供,于庭中拜仙,對月穿針乞巧。是夜,雞初鳴時分,擔江水或井水儲存起來,此為天孫水,亦謂之圣水,沐浴可治療熱病。
一
早在宋代,廣東即已盛行七夕乞巧,宋代詩人劉克莊即有“粵人重巧夕,燈火到天明”[1]詩句。明清時期,嶺南地區七夕拜會乞巧習俗依然繁盛。地方志及文人筆記多有記載。
七月初七為七娘會,乞巧。沐浴天孫圣水,以素馨、茉莉結高尾艇,翠羽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屈大均《廣東新語》[2]
七夕,汲華水貯之,以備酒漿,曰圣水。兒女陳瓜果乞巧,有喜蛛網則為得巧。 ——(乾隆)《番禺縣志》[3]
七夕,女兒乞巧。名媛劉蘭雪詩云:堪笑東鄰各女兒,聲喧檐外斗蛛絲。經年未識回文錦,試問天孫巧與誰?又名媛孫蕙蘭詩曰:乞巧樓前雨乍晴,彎彎新月伴雙星。鄰家有女都相學,鬧取金盤看五生。七夕遇雨,余五娘詩曰:乞巧傳杯不暫停,人間天上兩關情。西風吹斷牛郎淚,灑落檐前作雨聲。是夕雞初鳴,汲江水或井水,凈器貯之,味久不變,且益甘香,謂之圣水,專療百般熱病。此夕水獨重于他夕,若雞二唱汲之,即不然矣。——(清)范端昂《粵中見聞》[4]
明清時期的文人詩歌也多有描述。
銀河鵲尚未成橋,花果陳筵迓碧霄。兒女心忙先乞巧,分明七夕是來宵。七月初六夜,為七娘會,兒女以花果作供乞巧。(《乞巧》)
七日良宵鵲駕成,空庭拜罷夜三更。勸君欲汲天孫水,莫待雞啼第二聲。(《天河水》)——(清)陳坤:《嶺南雜事詩鈔》[5]
清代學者汪瑔(1828—1891)更以十首《羊城七夕竹枝詞》,詳盡描述清中晚期廣州地區的七夕盛況,設長筵陳設瓜果,香奩器具俱備;直徑數尺的梳妝盤,盛滿女兒們梳妝打扮的各色衣服、鏡子之類;在翠綠的稻苗、豆莢掩映中的玻璃燈,翠色冷光相照,澄明透徹;各種巧藝制作,精巧絕倫;新嫁娘們則忙著“謝仙”,從此告別乞巧;是夜姑娘們盛水于盆,第二日早上起來,觀看浮在水面的落葉等所成影像,占驗所得之巧。
越王臺畔雨初停,幾處秋光到畫屏。好是羅云弦月夜,家家兒女說雙星。
繡闥瑤扉取次開,花為屏障玉為臺。青谿小妹藍橋姊,有約今宵乞巧來。
十丈長筵五色光,香奩金翠競鋪張。可應天上神仙侶,也學人間時世妝。
乞巧設長筵,用方幾數十。其所陳設,自瓜果燈燭而外,香奩縷箱中器具,幾于無一不備。又有織女梳妝盤,圓徑數尺,中盛鏡匣衣扇之屬,皆用雜彩及砑金五色等箋制成。或出自閨中,或購諸市上,雖巨費不吝也。廣州諸邑皆有此風,而會城為最。
稻苗豆莢綠成叢,費盡滋培一月功。嫩綠幾層紅一點,羊鐙光在翠秧中。
一月前,以水浸谷豆之屬,俟其發芽,約高數寸,即移置磁盎,至七夕陳于筵際。中燃玻璃鐙,空明四照。宋人詞所謂“翠色冷光相射”者,庶幾近之。
小品華蕤制最精,胡麻膠液巧經營。不知翠袖紅窗下,幾許功夫作得成。
用胡麻小粒及碎剪鐙心草黏砌盤盞鐙檠之屬,又或作小隊儀仗,如旗傘牌扇之類,大僅數寸,精巧絕倫。曩皆制自閨中。近年市肆亦有制就出售者矣。
排當真成錦一窩,妙偷鴦杼勝鸞梭。何須更向天孫乞,只覺閨中巧更多。
約伴燒香歷五更,褰裙幾度下階行。相看莫訝腰支倦,街鼓遙傳第四聲。
姊妹追隨上下肩,個儂新試嫁衣鮮。嬌癡小妹工嘲謔,明歲何人又謝仙。
乞巧皆女郎。其新嫁者預于會,則謂之“謝仙”。
幾盞清泉汲深夜,銅盤承取置庭心。今年得巧知多少,水影明朝驗繡針。
是夜以盤水置庭中,俾受風露。次日浮小花針或豆葉于水面,觀水中影所成物象。為得巧之驗。
升平舊事記從前,動費豪家百萬錢。昔日繁華今日夢,有人閑說道光年。
道光中乞巧之風最盛,豪門盛族一夕之費或數百金。往往重門洞開,外人入而縱觀,無呵止者。咸豐甲寅以后,此風頓衰。近十余年,乃漸復舊觀。然多閉門以拒游人,非相識者,無由闌入矣。[6]
汪瑔記述乞巧之盛,尤以道光年間的廣州城區為最,豪門巨族有些竟然為家中女兒“擺七夕”花費百萬錢,也許是夸大之詞。那些平日重門關鎖的高墻大院,此時皆重門洞開,任由外人入內品鑒家中女兒的巧藝。只可惜咸豐甲寅年間(1854年)廣東天地會“洪兵”之亂后,此風頓時衰落。此后雖舊觀漸有恢復,但豪門巨族皆閉門謝客,不再供外人欣賞了。
1934年8月15日《越華報》發表作者蒲劍的文章,回憶光緒年間廣州乞巧之盛況,大戶人家,爭相競奇斗麗。
七夕節巧瑣談
蒲 劍
吾粵女郎,每年七月初六七兩夕聯合諸姐妹在廳堂之上。陳列紙通芝麻制成之各種故事扎作,刺繡絲織手工品及燈色瓜果等類。各出心裁,爭奇斗巧。或唱女伶八音以助慶。名曰拜仙。到夜諸女郎傅粉涂脂,列座廳前。惹得一般狂蜂浪蝶,鑄立門外,評頭品足。在富有之家,每次所耗之金錢,多則數千,少亦數百。其貧乏者則瓜果香燭,雖少亦花費一元數角。……曩昔乞巧,不過陳設瓜果針線之類而已,乃后則有諸種女兒制品出焉。向憶光緒年間,周某以庫書起家,給數千元與其女拜仙。其時物價甚平,布置得窮奢極侈。一般人街談巷議周家拜仙如何奢華,如何聲勢。聞者皆以得一睹為快。故初六、七兩晚,把一條寶華坊擠擁得水泄不通。是時富豪之家,與官宦小姐們,不甘落后。效尤競奮斗富。投機者每屆七月初一日,即賃鋪擢列乞巧品物,供人采買。有用紙通芝麻等砌成各種戲本故事一座。內藏機器,上錬即能行動者,每座價值百數十元。其余砌成各種器皿用具,五光十色,奇形怪狀,美不勝收。業此者多獲厚利。其市以上下九甫,寶華路,高第路,河南洪德路等處為最繁盛。因其地點適中,且多殷戶,其余則零星小販,不足與論。近年因世界不景氣所影響,已不若爾時熱鬧矣。
二
此俗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1923年,上海廣益書局出版的胡樸安所輯《中華全國風俗志》,其中有《廣州歲時紀》《廣州之七夕》,皆詳細描寫民國初期廣州地區七夕習俗,為今天的七夕民俗傳承留下了寶貴的參考資料。
七月初七日,俗傳為牛女相會期,一般待字女郎,聯集為乞巧會。先期備辦種種奇巧玩品,并用通草、色紙、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種花果、仕女、器物、宮室等等,極鉤心斗角之妙,初六日陳之庭內,雜以針黹、脂粉、古董、珍玩及生花時果等,羅列滿桌,甚有羅列至數十方桌者。邀集親友,喚招瞽姬(俗稱盲妹),作終夜之樂。貧家小戶亦必勉力為之,以應時節。初六夜初更時,焚香燃燭,向空禮叩,曰迎仙。自三鼓以至五鼓,凡禮拜七次,因仙女凡七也,曰拜仙。禮拜后,于暗陬中持綢絲穿針孔,多有能渡過者,蓋取“金針度人”之意。并焚一紙制之圓盆,盆內有紙制衣服、巾履、脂粉、鏡臺、梳篦等物,每物凡七份,名梳裝盆。初七日,陳設之物仍然不移動,至夜仍禮神如昨夕,曰拜牛郎。此則童子為主祭,而女子不與焉。禮神后,食品玩具饋贈親友。拜仙之舉,已嫁之女子不與會,唯新嫁之初年或明年必行辭仙禮一次,即于初六夜間,禮神時加具牲醴、紅蛋、酸姜等,取得子之兆,又具沙梨、雪梨汁果品,取離別之義。惟此為辭仙者所具。他女子禮神時,則必撤去。又初七日午間,人家只有幼小子女者,咸禮神于檐前。禮畢,燃一小梳妝盆,曰拜檐前,祈其子女不生瘡疥。俗以檐前之神為齷蹉神也。復有一事,即于是日汲清水貯于壇內密封之,嘗久貯不變臭味,曰七月七水調藥,治熱性瘡疥,極有特效。
廣州風俗,綦重七夕,實則初六夜也。諸女士每逢是夕,于廣庭設鵲橋,陳瓜果,焚檀楠,爇巨燭,錦屏繡椅,靚妝列座,任人入觀不禁,至三更而罷,極一時之盛。其陳設之品,又能聚米粘成龍眼、荔枝、蓮藕之屬,極精致,然皆藝事,巧者能之。惟家家皆具有秧針一盂,陳于幾,植以薄土,蓄以清泉,青蔥可愛,乃女伴兼旬浸谷,昕夕量水,屏炎熱天時醞釀而成者。睹此覺中土“谷雨浸種,芒種蒔秧”之說,猶滯古諺,拘于地、囿于時也。廣州盛暑時,晝皆衣單稀衣,夜較涼,可衣復稀衣。其天時如此。粵稻歲兩熟,七月蒔秧,十一月刈稻,以為常。[7]
從上述描述可知,民國期間廣州一帶七夕會,實際上初六日即在庭中陳設各種用通草、米粒、芝麻等日常用品制作的奇巧玩品,以及女兒縫紉用的針線工具、化妝用品等,初六夜初更迎仙,三更、五更時分,拜七仙,然后“金針度人”,并焚梳妝盆,是夜,新嫁女辭仙。初七日童子拜牛郎,家中有幼小子女者焚小梳妝盤,祈求小孩不生瘡疥。另外,貯清水,密封,以備調藥之用。綜合宋至民國的文獻記載,可知七夕是廣州一帶非常重要的節日。
1929年3月,時任廣州特別市黨部委員的蒲良柱發起組織成立“廣州市風俗改革委員會”,當年7月11日正式成立,翌年2月份倉促結束。該委員會以“改良風俗,破除迷信”為宗旨,成立之時適逢臨近一年一度的七夕拜仙燒衣習俗時日,連日在《廣州民國日報》以記者名義,刊發文章痛陳婦女之“傷風敗俗”。足見民國時期某些官員對于民俗的態度,其觀念還是非常陳腐。文中對于當時七夕拜仙舉市若狂的描述,雖不乏種種貶義,倒可一窺民國時期廣州一帶七夕的盛況。
改革風聲中舉市若狂之婦女拜仙運動
民眾視法令如牟髦丑態百出恬不為怪
滿坑滿谷都是凡夫牛郎織女并未光臨
登徒子大顯神通婦女們揚眉吐氣
這才是傷風敗俗此之謂冶容誨淫
夏歷七月七日即八月十日。俗傳雙星渡河佳節,一般婦女多陳列鮮果、餅餌、生花暨各種刺繡小工裝作品,到壇迎仙,藉以邀□。千百年之習慣,牢不可破。本市風俗改革委員會□□此怪誕不經之事,特規定消極積極兩種禁止辦法。消極的,則派員勸導。積極的,則請公安局嚴禁售賣拜仙用品。惟記者昨晚細視十二甫等富戶聚居之街道,但覺禁者自禁,迎者自迎。婦女之迎仙興趣,不減昔年,在將所見情形,略述于后。
粉市。是晚十一甫暨十二甫之三鳳、美麗、丹鳳、金玉、泰生各粉莊,婦女之往購粉者,絡繹不絕,門限為穿,各粉莊大有應接不暇之勢。而各粉莊亦善于營業,更于是晚預以香水嗔地,香沁心脾,一般登徒狂且之流,徘徊于粉莊之間,藉以飽其眼福,其至上下其手,丑態百出。婦女因購粉拜仙之事,被狂且所奪者,大不乏人。故呼哀之聲,時隨香氣送入耳鼓。
花果。市內花王以此日為發財機會,盡力搜羅各種生花發售。凡花俗卉,亦細大不捐,陳列于觀音大巷等處,高聲眩售。一般迎仙婦女趨之若驚。是晚七時,各生花攤均有售罄,大有求過于供之勢。十八甫及十五甫馬路之生果攤,亦將價格抬高數倍,各婦女之購生果者,攜籃挽袋,取價爭益,聲振遐邇。種種怪狀,非記者之禿筆所能形容。
細工。十一甫、十二甫、十八甫、高第街、務洋貨店以及紙料紙扎店,均預仙橋暨巧小器具售賣。投機小販,更待興顧,婦女之往購者,摩肩擦背,馬路上婦女手挽肩托此種仙橋紙扎物品者,觸目皆是。尤可怪者,身穿漂亮西裝,胸懸襟章之少年,拖其愛人往購迎仙用品,代其愛人雙手捧著仙橋,高視闊步,一路軟語溫聲,回家迎仙者,為數不少。此中情形,又非記者禿筆能形容也。
迎仙。西關之富戶,仍于是晚,于大廳內以臺數張或十余張八仙木,陳列迎仙物品,應有盡有。姨太太、小姐、少奶輩,髻辮光滑,面涂粉脂,坐于廳事,以候牛郎織女之降臨。一般浪子闊少,則逡巡門前,評頭品足,冀以一親香澤。而粉白黛綠之少奶、小姐、太太等一早預備以色相示人,不以為忤,且有得意色。她如小家碧玉,平日結其同心若干人,每月預蓄金若干,盡行購置生果餅餌等物,更制備新衣,靚裝艷服,集合一堂,以迎仙子者,情形亦與往年無異云。[8]
1934年七夕節,番禺鹿步司茅崗鄉(今廣州黃埔區茅崗社區)循例備辦慕仙會,村中自梳女帶領小家碧玉、富家小姐置辦各種七夕手工,除千篇一律、陳陳相因的七夕故事之外,還有中山紀念堂、1932年淞滬抗戰等反映社會現實的手工作品。
茅崗慕仙會之盛況
老 骨
番禺縣茅崗鄉,乃范黃董李四姓聚族而居。人丁約三千余以范姓為最多,已占全村十分之六。其男子多數出外謀生,年中寄歸之欸極多。族中女子又能勤于紡織,日中所醵亦不菲。故其族之殷富,殊非別姓所可及也。該族婦女習于勤儉,因其愚守舊道德,頭腦未免陳腐,迷信色彩因而頗深。舉凡一切神誕莫不作熱烈之慶祝。猶以每年二月十九日之觀音誕,及七月七夕之女兒節,為最高慶。乞巧節時,婦女向有慕仙會之設。會之組織,每份基金壹元,按月各供兩角,會份無限制,多多益善。入會者不拘何姓,亦無鄉界之別也。惟男性與已嫁者不許參加。會務由一二富有積蓄自梳不嫁之老姑婆主持,辦理頗臻完善。附近各鄉之小家碧玉及富戶之小姐多有加入,每年會份多至數百。份金既多,則其開銷,當可盡情揮霍矣。各家女兒,每于紡織之余,必獨運匠心,以紙通芝藤等物,砌成各種器具,或砌出劇本故事。近年能利用干電池及各色小電泡。所制成之洋樓大廈,其中電炬齊明,模型賤小,能與真者無異。所砌之人物,暗配鐘練于內,使其自能行動。惟妙惟肖,栩栩若生。其手藝之織巧,見者無不稱贊。
該會之陳設,向在祠中,公開展覽,任人參觀,愿得與眾共樂之旨趣。是屆余承友約得一飽眼福。今年所擺之方桌共一百十二張,陳列之品,除各眾所藏之古董外,手工品占十之七八。即供仙之齋菜鮮果,亦皆染紙制成。驟然觀之,多不虞其為贗品。所列之紙制建筑物,以廣州市之中山紀念堂為最出色。其外觀既酷肖,而內部亦完備。即一磚一木之微,其間格與髹色亦無異于真者。其所制之人物故事,則以淞滬抗敵一座為最脫俗套。所制成之我國官兵,皆奕奕精神,殺敵致果,且有機簧暗藏其中,各能揮刀向敵。見者之心,多為興奮。于娛樂中不忘救國,制此者其亦庶幾乎。余外所列者多七夕故事,手工雖巧,惟陳陳相因,千篇一律,殊不覺其精彩也。是夕觀者人多如鯽,紅男綠女,白叟黃童,擠逼祠中,肩摩臀并。幸各人皆能謹守秩序,尚無攬竊非禮之事發生。會友數百人,或招待戚友,或歡迎來賓,或監視品物,或指揮香燭,各司其職,忙個不了。而觀眾之贊許聲,談論聲,泯成一片。亦足與祠外唱八音之弦歌聲,互相響應也。時至三鼓,更在祠外曠地,大放煙花,金蛇吐焰,光耀數里。熱烈情形,堪稱一時之盛。聞是屆所耗之資,數在三千金以上。在此世界不寧,農村破產之當中,得此點綴,殊足稍破吾人愁悶。然以有用之資,作無為之舉,余固不敢贊同也。[9]
1934年8月19日廣州《越華報》曾記當年禺南石壁(今廣州市番禺區鐘村鎮轄區)鄉民環請鄉長準予籌備七夕并請梨園演戲一事,鄉長因怕擔責而不愿呈準告官,不料有人卻曲徑通幽,獲得當局批準。鄉人遂以鄉長不具擔當之名而罷其職,七夕之日鄉民極盡狂歡之能事,盡情釋放。
石壁鄉乞巧節之易長潮
番禺石壁鄉,交通四達,人煙稠密。鄉中富戶,尤以區姓為一鄉大族,平日鄉事,多歸其主持。歷屆鄉長多能護慎從公,故鄉中甚少風潮發生。近日鄉人以七夕已屆,鄉中不演戲已久,際此乘平時候,欲趁茲機會大演梨園,鋪陳七夕物品,以與鄉人共樂。當此消息傳出后,鄉中婦女尤為興高采烈,一致贊成。事先即聯會姐妹輩就本姓祠堂砌作乞巧品物,以備屆時陳列。好事之徒,又議蓋搭戲棚,出省雇請梨園,以備回鄉開演。惟近日鄉村演劇須有負責者出而擔負責任,呈準官聽,始能開演。于是眾乃環請鄉長區柏江出面辦理,區以此種有抄家無封誥之事,意殊不欲。乃向眾諸多留難,使將此舉打消。眾人于是當堂鼓噪,謂鄉長自私太重,弗顧輿情,一時議論紛起。然卒以無人負責,勢將中輟矣。其中有一部分人,以各專已整備,事如不成,未免掃興。乃轉而之省,丐得留省之有面子者,向當局呈準人情。遂不動聲色,雇妥演壽年戲班,并聯合留省鄉人之有勢力者,水陸浩浩蕩蕩,回去開演。當戲班未抵步之前,鄉人中尚有故意向該鄉長再三求情,愿允其所示條件,不意議商既竣。而紅船已揚帆入口,留省之有面子者亦盡歸來,一時鄉人歡呼震天,婦孺亦雀躍而出。該鄉長登即愕然,知自己弄糟其事,不敢見人,乃伏匿不出。惟時鄉人見其身為鄉長,而不能負責守法為鄉人造事,乃一唱百和,要將其撤換。立即聚祠堂集議,卒議決以區天任暫代其職,蓋代期尚有一月,區以眾怒難犯,亦愿早日卸事得身輕矣。鄉人見目的已達成,為增加熱鬧起見,更發起賽龍船之舉,又有某坊將其祖遺古玩古畫等古物盡數檢出陳列,任人參觀,而婦女之筵戚接友以盡此一夕以歡,尤為忙個不了,是興七夕節鄉村中少有之鬧熱矣。[10]
以上三則民國時期報紙所記七夕拜仙之消息,今天讀來頗為有趣。由此可知,民俗的慣性并非一紙行政命令即可禁止,與其壓制禁行,不如疏導放行,尊重其傳承規律。
三
七月初七“擺七夕”民俗活動,在番禺的石碁、石樓、化龍一帶,久有流傳。特別在石碁的凌邊村,只在“文革”期間有短暫中斷,民間一直保有“擺七夕”傳統。20世紀80年代,化龍鎮潭山村的自梳女們也開始自發組織,恢復“擺七夕”。至今,隨著當地政府的重視,以及民間的自發組織參與,兩地“擺七夕”傳統均得到較好傳承,并有新的發展。
凌邊村的“擺七夕”,在番禺地區頗負盛名。舊時凌邊村的乞巧多由各家各戶自辦,姐妹們多互訪品評觀摩,看誰做的“七夕公仔”手藝高。“文革”期間,凌邊村乞巧中斷。據謝權治介紹,1973年,凌邊村即恢復擺七夕活動,以女性為主,采用分散自由組合的方式。[11]1978年之后,凌邊村的“擺七夕”,即由家庭轉到了小集體,“人多好做作”,容易發揮集體智慧,擺七夕的地點也從家庭轉變到祠堂。
以前呢,擺的范圍比較小,沒現在規模這么大,現在都好大陣仗。以前就幾張臺,就在天井頭擺三幾張。1978年的時候,就已經是以生產隊為單位。之前更早的時候,我們村都有拜七姐,整手工。[12]
到1978年,我們十五六歲那個時候,就撩起隊長說,不如重新擺七夕啰。隊長說,你們擺啊!我們就開始擺啰。第二日隊長就派我和田妹、洪叔去佛山買東西,買石灣公仔返來擺,那個時候沒誰知道擺啊!其實都好簡單,也就是簡單擺擺,又沒錢,只好自己整點手工,主要目的是拜拜神。后來才慢慢整大,個個都擺十幾二十圍(餐)。[13]
到1992年,凌邊村的乞巧活動,從原來在祠堂靜態展示,在祠堂靜態觀賞,借用舊時神誕出會巡游的形式,轉向動靜結合,即既有祠堂的展示,也有動態的巡游,由各生產隊精選一板新作的七夕公仔、裝上色柜,用人抬著游行,更有真人扮相的牛郎、織女以及六個仙女,一頭真人舞動行走的道具仙牛,還有幾十只真人頭戴鳥飾的喜鵲,隨隊游行,每到開闊處就停下來表演《銀河會》歌舞。參加巡游的有學生鼓樂隊、儀仗隊、生花果擔隊、百足旗、八音鑼鼓、彩旗隊、醒獅等。整個巡游隊伍有500多人,浩浩蕩蕩沿全村大街主路巡游一周,歷時兩個鐘頭,行經四公里,盛況空前。每年凌邊村七夕期間,外村到凌邊看七夕的人特別多,加上本村的親戚、外嫁女拖男帶女回來,村內大街人潮涌動,川流不息。家家戶戶當刂雞殺鴨,喜氣洋洋。[14]
1992年那次游村,那時候還沒有環村路,就沿村游行,后來鎮政府知道我們有這么大規模的巡游,就要求我們去長隆、去英東體育館、去石碁鎮巡游。“非典”前我們村的擺七夕都好隆重,七月七那天,來我們村參觀的人多到人山人海,家家戶戶都擺幾十圍,二三十圍,請親朋好友食飯。那個時候小孩還沒結婚,他們的同學啊,到了這個時候就來了。人多到有一年我崩(缺)3圍,有一年崩(缺)5圍,慘啰!我只好隨街揾餸(去街上到處找菜式)。以前三月份,這里周邊的小食店全部訂完,間間都滿座。
“非典”那年,雖然有拜神,但是沒有請人食飯,以后就再沒有請飯了。不再請飯,不是錢的問題,主要是太辛苦啦,要搞家里那份,又要搞生產隊那份,好辛苦![15]
凌邊村的七夕從初六下午開始,初六晚起一連三夜演大戲,初七各家請客吃飯,初八繼續擺一天,初九全部拆除,保存放好,留待下一年添新去舊再擺。
凌邊村的乞巧多取材于古典戲曲故事,舊時多紙通公仔,人物高尺許,多穿著針線刺繡服裝,做工精細,仿照舞臺造型,似無聲大戲。在每一個擺七夕的祠堂里,可欣賞到五百多個不同人物、造型各異、千姿百態的古裝公仔,其傳統供案有“薛丁山三擒三縱”“穆桂英大戰洪州”“梁紅玉擊鼓退金兵”“天姬送子”“武松打虎”“牛郎織女渡鵲橋”“六國大封相”“拜月記”“楊門女將”“郭子儀拜壽”等。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
我們做的公仔都是大戲當中的人物。我們都中意睇戲,睇古裝戲,買碟返來睇,去會堂睇,去到市橋睇,還去廣州睇,以前我們到處去睇戲,走路都去。看了之后不就記住了嘛,記住之后想想,不就接著做啰,做一場戲,不是做整出戲。以前我們村有私伙局,那個掌板的去世后就散了,沒人玩了。“文革”的時候村里有個劇團,自己會做大戲,屬于文娛組。[16]
此外,還有花燈、蠟制仿真花果等工藝品,其中燈飾就有菱角燈、蓮花燈、走馬燈、宮燈等。另有一種在瓷砵上以谷秧圍成圈狀的油燈最具特色,取“五谷豐登”之意。還有不少供奉牛郎織女的手工藝品,如繡花鞋、花衣裳、妝奩、笠帽等紙布制品,再加上五彩燈飾,琳瑯滿目。[17]
與舊時文獻中記載的乞巧一般由待字閨中的未婚女子參加不同,凌邊村現在的乞巧參與主體主要是60歲以上的老年婦女。從她們接觸乞巧開始,參與主體都是老年人。
我們小時候看到的都是我們這些幾十歲的人擺七夕。我家姐八十幾歲啦,現在在新橋(石碁鎮另一條村)那邊都還有參加。擺七夕的事情,一路都是老人參加得多,有稍微后生點的,都四五十歲了。[18]
2015年七夕期間,凌邊村再度巡游,有7個生產隊參加此次沿環村公路的游行,巡游的儀仗隊伍與1992年大體類似,村中各大祠堂也有擺放。盡管巡游很熱鬧,但拜七姐依然是七夕期間最重要的儀式。
擺七夕都有裝香,就是在祠堂那里,初六晚十一點開始拜,三更拜七姐,初七晚又拜一次。每年的手工主要都是做拜七姐的那些東西,其他都是次要的,主要是每年都要給七姐燒那些衣衫、鵲橋、七娘盤,其他做公仔就一套套戲。[19]
每屆七夕,外人欣賞的是巧姐們的手工,而對于她們自己而言,這些手工更是一年一度敬獻給七姐的禮物。沒有親身參與其中的人們,無法想象這些上了年紀的老人,為何如此熱衷于用一些今天看來頗為粗糙的材料,用自己的雙手制作一些簡單、質樸的衣衫妝奩、亭臺樓閣、神佛仙界、戲曲人物、農家生活、田園風光、花草生果等。如果說舊時未婚女子向七姐祈求巧藝與美好姻緣,那么,今天的老人們則更多的是在繼承傳統拜七姐信仰基礎上,出于自己的喜愛,自娛自樂,在自己的辛勞和別人的贊嘆中,獲得成就感。
村里的媳婦也不是個個都會擺七夕。誰中意,誰就去擺啰!主要看你中唔中意,有時間同精神,不就出來擺啰?有的人都說,是你們中意的,咁辛苦!我們不怕辛苦,晚晚都開夜工做的。
以前都是跟著村里的老人家一起做的。接大板的乞巧來做,是第一年參加比賽那個時候,大概是2012年、2013年,我同我老公一齊整。那個時候大隊通知說生產隊可以做,私人也可以做,我就為生產隊做一板,自己做一板。去年我做了三板,村委凌主任說做多少都可以,我就多做點。前年沒有比賽,我個人沒有做,就幫生產隊做,做了一板《春到田間》。
小的時候不就是看別人擺的嗎?讀書那時候還不知道擺,后來跟黃家珍學。現在我們隊的七娘盤都是我做的,其他人都不會做。以前看擺七夕很開心的,拿張凳就坐在那里看擺七夕,不知道有多高興![20]
與廣州天河等地的擺七夕相比較,凌邊村的乞巧更少受到外界關注,無論其內容還是表現形式,都更為原始、質樸,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是簡陋。正因其簡陋,而保持了更多質樸的表現手法,比如用材隨意,造型不事雕琢,色彩素樸自然,有一種別樣的天然拙趣。
20世紀80年代化龍鎮潭山村的姑婆們恢復“擺七夕”活動,至今已從女性為主到男性、女性共同參與,現在,潭山村的“擺七夕”也是由浩明藝社主持,每年在潭山村許氏大宗祠都有大小規模不等的展示。
1980年,恢復乞巧的時候,我們男人是不參與的,是我們村的一班姑婆搞的,現在我們村還有一兩個自梳女。為什么會在80年代恢復乞巧呢?因為“文革”十年所有民間的活動都被禁止。80年代改革開放,我們村的這些姑婆們就商議恢復乞巧,擺了一次七姐,當時在整個番禺縣引起轟動。之后一直到1988年,都沒再擺過乞巧了。1988年,由祺叔(許冠祺)發起,他說現在國泰民安,恢復這些傳統的事情,應該都沒什么問題。從這一年開始,就由浩明曲藝社出面籌備,有當時尚健在的十幾個姑婆參與,當時不是由村委會出面組織,完全都是由我們曲藝社這幫人負責。我們曲藝社的男人當時只是聽講過、見過,但都不知如何做、如何擺,就請這些姑婆親自示范、口述,這樣足足搞了兩年。1990年開始,年年都有乞巧了。乞巧的籌款、召集人手,都是由浩明曲藝社出面,村中那些比較熱心、經濟條件比較好的村民,我們就會找他多多少少贊助一點。剛開始搞的時候,村里面也不是說不支持,因為那時候村集體也沒什么經濟收入,不可能有精力關注這件事。當我們民間自己做這些事情有了成績之后,村政府發現這些傳統的文化好有價值,加上村集體經濟收入也比較好,也就開始重視起來。
我們乞巧節期間有拜七姐。我們潭山拜七姐的時候,只是自梳女們做一個簡單的祭祀儀式,焚香,向上天祈禱,向七姐乞心靈手巧、風調雨順。潭山以前有好多自梳女,當時的社會受封建禮教約束,男女接觸唔多,好多女仔怕出嫁之后老公對她不好,又吃喝嫖賭,所以唔想嫁。受當時風氣潮流影響,好多的女仔都選擇唔嫁。[21]
與潭山飄色一樣,因主持者更少受傳統約束,潭山“擺七夕”多現代題材,如2015年的“飛奪瀘定橋”“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等,用材較講究,造型用心揣摩,色彩艷麗,場景宏大,善于運用現代聲光電技術營造亦真亦幻效果,總體呈現精雕細琢的別致風格。
表面看來,潭山村的飄色和乞巧在浩明藝社的主持下紅紅火火,屢有創新,發展勢頭良好,實際上,其傳承現狀與其他民間藝術一樣,也存在著隱憂。
其實現在的傳承都出現好多問題,如果從50年代開始算起,浩明曲藝社到今年已經生存將近60年了,根本上就是一班土生土長的農民,在農閑的時候做的事情。但是到了今時今日,年輕人都在工廠做事,八小時正常上下班,根本就沒有農閑的時間安排。我估計20年之后,我們現在搞的乞巧、飄色很可能會銷聲匿跡了。現在表面上有傳承,但實際上愛好的人不多。像舞龍舞獅乞巧扒龍船這些傳統,除了扒龍船,村中細佬從小到大一路扒啊扒,應該可以傳承下去,但乞巧啊、飄色啊這些好精細的東西,都好難傳承噶。比如乞巧的一只公仔,至少要耗時三日,按照現在工廠的工時效益,一只公仔至少應該賣多少錢呢?至少也要六七百蚊吧,但是你做出來哪里有銷路呢?仲有,飄色乞巧的各種儀式,大家都沒得閑的時間來參加。現在不是農耕社會,有農忙農閑。現在一年四季都要做事,根本就沒有農忙農閑的分別。現在珠村之所以還有乞巧,因為還有城中村,如果他們的房子全拆,村民都上樓,我話俾你聽,呢樣嘢全部都冇曬啦。你走遍廣州、番禺,你能夠揾到邊個小區、邊個樓盤整一個乞巧、整一個飄色出來噶?受場地限制,沒有生存空間,沒有活動場所。[22]
不同的民俗現象,其傳承有其自身的內在邏輯。當下的民俗傳承,需要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針對不同的民俗現象,遵循其傳承規律,尊重傳承人的意愿,設計不同的傳承策略。任重道遠!
四
本文結合文獻材料和田野調查資料,發現廣州地區“七娘會”的核心習俗如乞巧拜仙、金針度人等歷經千年,一直傳承至今,但習俗的傳承主體卻由未婚女子逐漸演變為中老年婦女,究其原因,與習俗的中斷導致代際傳承斷裂有較大關系。傳統時期,廣州地區的“七娘會”為民間自發,改革開放復興之后,初期由民間自發,現逐漸演變成為政府、學者、媒體、民眾等不同力量共同參與的公共節日,功能日趨多樣復雜。基于“傳承母體”的民俗傳承,其人際關系基于血緣、地緣、業緣組成的“熟人社會”,而當今由不同力量共同參與的公共節日,卻是“熟人社會”與“陌生人社會”的奇異交織。由傳統的“熟人”“陌生人”相互觀賞品評,“看”與“被看”,“各美其美”,到當下的“熟人”“陌生人”共同參與,廣州地區的“七娘會”不是特例,而是當下中國民俗文化傳承的共同現象。當下的民俗傳承從“傳承母體”逐漸轉變成為利益多元的“異托邦”,對于當下民俗傳承的認識,亟須超越傳統的“傳承母體”幻象,從眾聲喧嘩的多元訴求中尋求利益各方的“美美與共”。
注釋:
[1]宋·劉克莊:《即事四首》,清·吳之振:《宋詩鈔》卷九十,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屈大均:《廣東新語》(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62頁。
[3](乾隆)《番禺縣志》,卷十七,風俗,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本。
[4]清·范端昂:《粵中見聞》,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刻本。
[5]清·陳坤:《嶺南雜事詩鈔箋證》,吳永章箋證,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311頁。
[6]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輯:《歷代竹枝詞》(四),陜西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3420-3421頁。
[7]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7頁,第382-383頁。
[8]《廣州民國日報》,1929年8月12日。
[9]《越華報》,1934年8月20日第1版。
[10]《越華報》,1934年8月20日。
[11]謝權治:《微型工藝“乞巧村”》,番禺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番禺文史資料》(第17輯),2004年12月。
[12]口述人:周鳳英,女,72歲,凌邊村人;調查記錄整理:劉曉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邊村委。
[13]口述人:曾秀妃,女,59歲,凌邊村人;調查記錄整理:劉曉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邊村委。
[14]石碁鎮文化站編:《岐山拾趣》,自印本,1993年10版,第95頁。
[15]口述人:周鳳英,女,72歲,凌邊村人;調查記錄整理:劉曉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邊村委。
[16]口述人:曾秀妃,女,59歲,凌邊村人;調查記錄整理:劉曉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邊村委。
[17]石碁鎮文化站編:《岐山拾趣》,自印本,1993年10版月,第95-96頁。
[18]口述人:周鳳英,女,72歲,凌邊村人;調查記錄整理:劉曉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邊村委。
[19]口述人:周鳳英,女,72歲,凌邊村人;調查記錄整理:劉曉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邊村委。
[20]口述人:曾秀妃,女,59歲,凌邊村人;調查記錄整理:劉曉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邊村委。
[21]口述人:許鋸泉,男,1968年生,潭山村人;訪談記錄整理:劉曉春;2015年5月15日,潭山村委。
[22]口述人:許鋸泉,男,1968年生,潭山村人;訪談記錄整理:劉曉春;2015年5月15日,潭山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