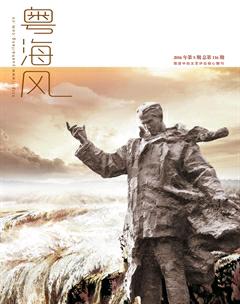左翼文化界的尷尬遭遇
張雨晴
1949年5月,由周揚主持歷時近一年完成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趕在第一屆文代會前出版了。作為貫徹《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實踐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已取得的成果,這套叢書的地位、分量和價值毋庸置疑,特別是對于那些來自國統區的左翼作家們來說,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見面禮。因此,如何總結“五四”以來的左翼文藝,以及所謂國統區的左翼作家和“廣泛的中間層”作家們在新政權和新文藝規范下如何安身立命等問題隨之被提出。于是從1951年開始由茅盾主編、開明書店出版的“新文學選集”應運而生。
這部被稱為“新文學的里程碑”[1]的選集,有針對性地選取了魯迅、瞿秋白、郁達夫、聞一多、朱自清、許地山、蔣光慈、王魯彥、柔石、胡也頻、洪靈菲、殷夫等12位“已故作家”與郭沫若、茅盾、葉圣陶、丁玲、田漢、巴金、老舍、洪深、艾青、張天翼、曹禺、趙樹理12位“健在作家”的“革命現實主義”作品,集中展現“五四”以來所謂“進步”作家在“新文學的發展的過程” [2]中的創作歷程和功績。
簡單對比兩套叢書可以很直觀地發現,與《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所體現出來的樣板、標桿、指南等特點和作用不同,開明版“新文學選集”因為作家的身份、地位以及革命文藝創作等方面的不同而呈現出另外的特點,不妨以《茅盾選集》為例。
一、檢討與批判:“序言”中蘊藏的天機
開明版“新文學選集”出版之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也已拉開帷幕,文藝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運動已經展開。在這種歷史語境下,為表明向延安主流意識形態的靠攏與歸順,出版選集的“健在作家”大都借撰寫序言的機會對自己以往的文藝思想進行了檢討與批判。例如在“廣泛的中間層作家”中,巴金就表示“我的作品中思想性和藝術性都薄弱”,“在這新的時代面前,我的過去作品顯得多么的軟弱,失色!”“我的作品沒有為這偉大的工作盡過一點力量”。[3]老舍表示自己的“溫情主義多于積極的斗爭”,“幽默沖淡了正義感”,并針對此前具有“錯誤傾向”的《貓城記》等作品愧悔說:“我很后悔,我曾寫過那樣的諷刺”。[4]曹禺檢討自己“沒有在寫作的時候追根問底,把造成這些罪惡的基本根源說清楚。”[5]在國統區左翼作家中,洪深批評自己的舊作非常“拙笨”,“和當前的生活是毫不投合的”,是“過時失效的作品”,“難于為它們安排用途”,以往的作品“并未曾為時代好好的服務”。[6]張天翼認為舊作只是“提供了一點史料”,“自以為是站在勞動大眾立場,并為他們而寫,究竟他做到了沒有,做到了多少?”并表示“過去的算是略為做一個交代。以后——從頭學起”。[7]
“已故作家”雖已不能發聲,但是作品中存在的問題卻不能輕易放過,于是出現了一種活著的作家為去世的作家代為檢討的現象。例如,周立波在為王魯彥所寫的序言中代為檢討說:他“沒有投身到人民解放斗爭的主流里,對于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來解放自己的可能還沒有充分的看清”,他的有些作品“帶著知識分子的一些特有的情感”,“看不見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嚴重的斗爭,看不見工人農民的解放運動的勝利的前途。”[8]孟超在《我所知道的靈菲》的序言中代為檢討說:他的作品由于“革命知識分子的階級性的限制”而表現出“羅曼蒂克的氣質”,不少小說中都體現出“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9]
作為未經歷過延安整風和思想改造的左翼作家茅盾,盡管這時已經是共和國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家協會的主席和中國文聯的副主席,這一關也是要過的。面對《幻滅》《動搖》《追求》這三部嚴重影響茅盾革命形象的小說,他解釋和檢討說,這幾部作品“是有若干生活經驗作為基礎的”,“1925—1927,這期間,我和當時革命運動的領導核心有相當多的接觸,同時我的工作崗位也使我經常能和基層組織與群眾發生關系”,但由于對革命形勢的觀察失誤以及當時思想情緒的悲觀失望,導致了作品出現種種問題。他檢討《三人行》的寫作是因“徒有革命的立場而缺乏斗爭的生活”才導致失敗。關于《子夜》這部小說,他說,寫作中本是打算通過農村與城市革命力量的對比“反映出那時候的中國革命的整個面貌,加強革命的樂觀主義”,但由于謀篇布局與寫作能力上的原因造成作品未能“表現出整個的革命形勢”。茅盾坦誠說,必須“檢查自己的失敗的經驗”,認為舊作“都是‘瑕瑜互見乃至‘瑜不掩瑕的東西”,“即使有點暴露或批判的意義,但在今天這樣的新時代,這些實在只能算是歷史的灰塵,離開今天青年的要求,不啻十萬八千里”。他還表示自己“沒有把自己改造好。數十年來,漂浮在生活的表層,沒有深入群眾,這時耿耿于懷的,時時疚痗的事”,自此以后要“從頭向群眾學習,徹底改造自己”。[10]
從茅盾這些帶有澄清、辯解性的檢討與自我批評中可以看出,在文藝一體化的進程中,作為國統區左翼作家的茅盾,其身份實際上是十分尷尬的。較之“廣泛的中間層作家”,茅盾顯然是站在革命陣營內部的立場去進行自我批判的,他在檢討過往的文藝思想的時候并未忘記自己左翼作家的身份。并且,茅盾在進行自我批判的同時也隱約表現出他意欲強調左翼作家在革命時期曾發揮過積極作用的意圖。但同時,與延安主流作家相比,茅盾又明顯意識到自己因未曾經歷延安整風規訓而具有的“革命缺陷”,所以必須在新形勢下批判舊我,改造自己,盡快以《講話》的精神作為絕對正確的標準轉變思想,跟上新的意識形態。
事實上,結合開明版選集序言可以看出,茅盾體現出的這種尷尬的身份和生存狀態,并非是他一個人,而是國統區左翼作家們的一個縮影。
二、篇目選編的用心良苦
稍微研究可以發現,茅盾在選擇篇目時就特意規避那些在序言中提到的不進步的“敏感”作品,而將《春蠶》《林家鋪子》《趙先生想不通》《微波》《夏夜一點鐘》《第一個半天的工作》《官艙里》《兒子去開會去了》《列那和吉弟》《脫險雜記》這10篇小說收入集中。茅盾做這樣的篩選,顯然是覺得這些作品具有“革命意識”,相對能夠與當時的主流文藝政策相契合,但若細致考察這10篇小說,卻發現,事實與他的預期還存在很大的差距。
首先,被選入集子中的10篇小說,只有《春蠶》以農民作為故事的主人公。《林家鋪子》中的小商鋪主人林老板,《趙先生想不通》中熱衷于投資與投機的趙先生,《微波》中的李先生以及《官艙里》中的老少兩代人都是小有產者。《夏夜一點鐘》和《第一個半天的工作》中的兩位女性則是城市平民的代表。《兒子開會去了》《列那和吉弟》《脫險雜記》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知識分子。總體看來,這些小說中的主人公幾乎都是茅盾所熟悉的“小資產階級”。從人物形象塑造這一方面來說,就形成了與當時以工農兵作為主人公的文藝“主旋律”并不十分和諧的局面。
其次,這幾篇作品的主題與內容也值得體味。《春蠶》通過老通寶養蠶豐收卻成災來表現農村經濟破產,《林家鋪子》通過林老板小商鋪的倒閉表現城市經濟破產。這兩部作品雖然內容不同,但都是茅盾“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象”[11]的嘗試,寫作主題指向“30年代城鄉經濟普遍破產時期那種復雜的社會經濟連帶關系”[12],其中卻并沒有提及和突出無產階級及其反抗行為。
《趙先生想不通》寫小資產者趙先生的投機心理,也表現出“公債市場的熱鬧,投機的狂熱,是怎樣一種病態”[13]。《微波》寫有產者李先生一家在動蕩時局中經濟境遇不斷改變直至破產。這兩篇小說以人物命運表現經濟關系,同時勾連當時的社會現實,具有諷刺意義。不過小說內容無關革命,作品主題也與階級反抗沒有聯系。《夏夜一點鐘》和《第一個半天的工作》都是對職場中女性的描寫。前者通過刻畫女性的戀愛心理,影射公司內部關系的錯雜混亂,也構成了對現代男女的諷刺;后者描寫職業女性的苦悶,并以此暴露職場內部的“社會政治生態”。這兩部作品傾向于揭示“小資產階級”女性所面臨的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困境,并未涉及階級文學中常見的“女性解放”等內容。《官艙里》通過老少兩代人之間的對話,“縮影”式地表現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生態,為讀者展現出“社會一角”[14]的真實面貌。小說雖然對時事政治、社會弊端進行暴露與批判,不過并未因此引出“民族反抗”與“階級反抗”這樣的情節。《兒子開會去了》寫少年阿向說服父母同意自己去參加市商會的群眾游行的過程以及少年去參加集會后父母的所思所想與心理變化。茅盾顯然試圖借由小說表現出群眾運動的影響力與國人的革命熱情,但他并未對運動本身進行直接呈現,也并未對革命主體進行重點書寫。《列那和吉弟》寫寄居在新疆的知識分子一家所養的兩只小狗的遭遇,借以影射動蕩的時局。小說的寫作目的如茅盾所言,是為“懷念那五位在新疆受冤被捕的劇團的朋友”,同時也為紀念茅盾故去的女兒[15]。作品雖然具有諷刺時局的意義,但其中并未涉及動蕩時局中的革命者。《脫險雜記》則是茅盾對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陷落后,自己一行文化人在東江游擊隊保護下由香港回到內地的經歷進行的速寫式的記錄。[16]小說側重于描寫知識分子在轉移過程中的遭遇、見聞以及心理活動,其中并未著力突出無產階級的“革命貢獻”。
最后,《茅盾選集》的小說文本中還存在如下一些細節處理不很“得體”的問題。像《春蠶》,茅盾雖曾表示過造成小說中農村經濟破產的原因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與國內政治的混亂”[17],但這一背景是被隱藏在幕后而未做直接描寫的。所以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曾有批評者指出“如此嚴重的經濟恐慌,猶未提起一筆追溯恐慌之成因”。[18]《春蠶》中的老通寶等農民,被刻畫為帶有傳統劣根性與愚昧色彩的人物,而非《講話》精神映照下的“英雄人物”,這一點也曾被批評者質疑為只寫“落后的農民”[19]。這樣的小說敘述方式顯然與“革命敘事方式”之間存在隔膜。再如,在表現群眾運動的《兒子開會去了》這篇小說中,參與群眾運動的少年“阿向”的父母,對于兒子去參加游行集會的行為顯然有所擔心,抱有猶疑態度。小說對群眾運動的描寫也從側面表現出運動所具有的危險性與復雜性。這樣的描寫透露出的是對待革命的遲疑態度,而不是主流話語所倡導的堅定的革命態度。而在《夏夜一點鐘》這篇小說中,還出現“她示威似的將腋下的一個紐扣揪開,隨手霍地一撩,她那累絲紗旗袍的上半截借著那鋼板一樣的硬領的重量就從胸口再往下褪,露出了她那光光兩個肩頭和小半個胸脯了”[20],這樣“露骨”的情欲描寫,體現出的顯然是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的情調”,與革命并不搭邊。
不難發現,茅盾雖然抱著迎合主流文藝政策的態度去篩選小說,但收入《茅盾選集》中的10篇小說無論在人物、主題,還是內容的細節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游離于主流文藝話語之外,有些甚至與“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主流文藝思想相互抵牾。這其中可見,茅盾雖然已經在序言中進行了檢討,并且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表示要向《講話》學習,改造自己的思想,實踐“文藝的工農兵方向”,但他對文藝政策的“個人化的理解”,[21]顯然與新的文學規范還未完全調和,他的理論言說與文藝實踐并不統一。當然,這不僅僅是茅盾這一個個體所面臨的問題,而是未經《講話》規訓的國統區左翼作家們普遍面臨的問題。
三、為迎合《講話》修改原作
“新文學選集”出版時,為使作品更加符合延安文學規范,適應“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不少作家都對作品進行了一種“迎合性的修改” [22]。像老舍將《駱駝祥子》節錄后收入選集,共刪145處,“第十章和第二十四章則全部刪去”,不僅刪減了某些“不合時宜”的內容,也將祥子墮落的結局徹底刪去。[23]曹禺對《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幾部戲劇的某些章節完全改寫,將《雷雨》的“序幕”和“尾聲”刪去,第四章整章重寫,增添大量反抗“帝國主義”的情節[24],在《日出》中“增加了一條寫革命斗爭的情節線”[25],“以階級斗爭和階級矛盾重新組織劇情”[26],將《北京人》原劇中“既原始又現代的‘北京人形象全部砍削”[ 27],以達到凸顯劇作的政治性,使作品可以最大限度適應主流意識形態的目的。
茅盾借出版的機會也對自己的作品進行了重新修改,他對文章的改動雖然不多,但有幾處卻也是頗用心思。例如《官艙里》一文,他將描寫制作假鈔的“××人”改作“東洋人”,將故事結尾“因為據說這些小小的連成的‘南瓜棚是奉命搭蓋的,用意在避飛機‘下蛋呢!”[28]改為“因為據說這些小小的連成一片的‘南瓜棚是奉命搭蓋的,用意在萬一對日戰爭這可以避免飛機‘下蛋,那就是‘防空!”[29]《列那和吉弟》一文,他將小說結尾描寫主人公去向的原文“一年以后,媽媽聽得劇團里的人們有了問題的時候”[30]改為“一年以后,爸爸和媽媽從香港逃難到了桂林,在接到兩個孩子從西北的邊區寫了信來的時候,又知道劇團里的人們在迪化出了問題”[31]。《脫險雜記》一文,他刪去描寫逃難心情的一句話“我們的‘情緒之痛快,自不待言了”[32];將描寫游擊隊員的命運的原文“抗戰后才第一次來祖國,貢獻了他的力量”[33]改為“抗戰后才第一次來祖國,投身于東江游擊隊”[34];將“惠陽城里,政治上這時可算得真空。縣政府還沒回來,國民黨黨部也沒回來,警察也沒回來。在敵人退出后的第五天,回來的只有若干老百姓”[35]這段原文刪去“政治上這時可算得真空”一句。
能夠看出,茅盾對文章的這幾處小改動,無論是對政治環境的刻畫,還是對作家面對革命時的選擇與心態的書寫,目的和用意都是明顯的,那就是將原文中批判日本軍國主義者、諷刺國民黨統治的描寫更加明顯化,以增強諷刺的力度;將涉及革命內容的描寫更加“純凈化”,力求凸顯作家本身的革命意識與政治正確,借此強調自身的進步性和革命性。通過這樣一種有意識的“意識形態性修改”,以達到迎合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目的。不過同樣能夠發現的是,茅盾的刪改雖然與政治話語密切相關,并力求使文章更具有“革命色彩”,但實際上這種用心良苦也不過是細枝末節,并不能改變作品固有的“消極主題”以及主人公于革命的動搖和幻滅情緒,或者借用一句階級話語來說就是不可避免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
當然,茅盾并未像“廣泛的中間層作家”那樣傷筋動骨地改寫自己的作品,一方面是由于其作品主人公少有工農兵、革命者,作品的內容和主題以及敘事方式也與主流文藝相距甚遠,這就決定了他的作品事實上很難被改寫成完全符合《講話》精神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1949年建政初期,主流政治主要針對的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等所謂敵對勢力,尚屬于革命陣營的左翼力量還未被納入革命對象行列。所以,自居于革命有所貢獻的茅盾,在欣然跨入體制內的同時也表示愿意改造思想和文藝觀,也就沒有過度夸張地檢討自己、修改舊作。
1949年新政權建立后,在推進以《講話》為標志的正統意識形態和文藝指導方針運動中,茅盾所遭遇的尷尬境況,并非是個案,很大程度上是整個左翼文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這一點只要認真閱讀開明版“新文學選集”便會有真切感受。
參考資料:
[1]“新文學選集”出版廣告,《進步青年》第238期,1951年8月1日。
[2] 《新文學選集·編輯凡例》,開明書店1951年。其中《瞿秋白選集》與《田漢選集》因故未能出版。
[3]《巴金選集·序》,開明書店1951年,第9-10頁。
[4]《老舍選集·序》,開明書店1951年,第13頁。
[5]《曹禺選集·序》,開明書店1951年,第8頁。
[6]《洪深選集·序》,開明書店1951年,第7-8頁。
[7]《張天翼選集·序》,開明書店1951年,第7頁。
[8]《王魯彥選集·序》,開明書店1951年,第8-9頁。
[9]《洪靈菲選集·序》,開明書店1951年,第9、12頁。
[10]《茅盾選集·序》,開明書店1952年,第7-11頁。
[11]茅盾:《子夜·后記》,《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53頁。
[12]金宏宇:《文學的經濟關懷——中國30年代破產題材小說綜論》,《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
[13]茅盾:《質疑與解答——“公債買賣”》,《中學生》第36號,1933年6月1日。
[14]茅盾:《印象·感想·回憶》后記,《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第193頁。
[15]見茅盾:《春明版〈茅盾文集〉后記》,《茅盾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391頁。
[16]參見茅盾:《脫險雜記》,《進步青年》第二號,1949年6月4日。
[17]茅盾:《我怎樣寫〈春蠶〉》,《茅盾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214頁。
[18][19]茅盾:《〈春蠶〉〈林家鋪子〉及農村題材的作品——回憶錄(十四)》,《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1期。
[20]茅盾:《夏夜一點鐘》,《茅盾選集》,開明書店1952年,第99頁。
[21]陳改玲:《重建新文學史秩序》,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105頁。
[22]金宏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版本校評》,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18頁。
[23]參見金宏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版本校評》,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132、154頁。
[24]參見商昌寶:《作家檢討與文學轉型》,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76-177頁。
[25]金宏宇:《新文學的版本批評》,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7頁。
[26]陳改玲:《作為“紀程碑”的開明版“新文學選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6期。
[27]商昌寶:《作家檢討與文學轉型》,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77頁。
[28]茅盾:《官艙里》,《申報·每周增刊》第一卷第十四期,1936年8月30日。
[29]茅盾:《官艙里》,《茅盾選集》,開明書店1952年,第125頁。
[30]茅盾:《列那和吉弟》,《文學創作》第一卷第二期,1942年10月15日。
[31]茅盾:《列那和吉弟》,《茅盾選集》,開明書店1952年,第152頁。
[32]茅盾:《脫險雜記》,《進步青年》第三號,1949年7月4日。
[33]茅盾:《脫險雜記》,《進步青年》第六號,1949年10月4日。
[34]茅盾:《脫險雜記》,《茅盾選集》,開明書店1952年,第235頁。
[35]茅盾:《脫險雜記》,《進步青年》第七號,1949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