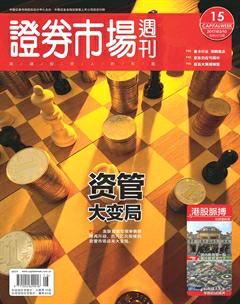中概股回歸政策不變,這意味著什么?
郭施亮
前期,有媒體傳出消息稱,證監會開始為部分借殼上市交易估值設定上限。具體而言,在海外上市中概股尋求借殼回到國內上市之際,需要確保交易估值不超過預估利潤的20倍。對此,亦有市場人士表示,這是變相同意中概股回歸的意思.但在隨后的時間內,證監會卻表示,對這類企業回歸A股市場的相關規定及政策沒有任何的變化。
實際上,在最近幾個月的時間內,關于中概股回歸的傳聞,就一直存在。其中,在今年5月初,市場早已傳出“證監會或將暫緩在海外上市的中概股企業回到國內市場上市”的傳聞,事后證監會亦傳遞出“正對中概股通過IPO、并購重組回歸A股市場可能引起的影響進行深入分析研究”的信號。
與此同時,在隨后的時間內,一系列的借殼新規以及監管趨嚴的舉措,也或多或少影響著中概股回歸A股市場的進程。或許,對于急于回歸的中概股企業,尤其是那些早已完成私有化退市的中概股企業而言,它們更是急于尋求最快的回歸方式,來達到其正式回歸內地市場的目標。
IPO發行、借殼上市、登陸新三板市場、進軍戰略新興板以及把自己出售給A股上市公司等方式,當屬時下中概股回歸內地市場的主要途徑。不過,在實際情況下,對于更多急于回歸至內地市場的中概股企業來說,它們更愿意采取借殼上市、IPO發行來實現其回歸的目的。
事實上,對于中概股企業來說,從其宣布私有化退市,到拆除VIE結構,再到選擇回歸的途徑等,都需要有不少的考慮。其中,在其私有化進程啟動之后,往往仍需要對其回購成本、法律風險等進行詳細地分析。與此同時,一旦中概股企業采取私有化退市之后,卻遭遇到突發性的風險,乃至集體訴訟的風險,則其回歸之路仍然頗顯漫長,而其回歸的成本壓力也是相當巨大的。由此可見,對于任何一家遠赴海外市場上市的中概股企業而言,它們要開展起回歸之路,確實需要相當慎重的考慮。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中概股企業得以完成其私有化退市的過程,仍需要充分考慮其后續的回歸途徑。很顯然,按照當前國內股票市場的準入門檻以及IPO堰塞湖的問題,實現私有化退市的中概股企業基本很難在短時間內借助IPO發行來實現回歸A股市場的目的。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IPO發行排隊時間過長,期間仍需要不斷補充企業更新材料,而稍有不慎,仍可能面臨重新排隊申請,乃至遭到懲罰的風險;另一方面則在于時下監管不斷趨嚴,即使企業得以進入初審會、發審會環節,仍需要對其各項材料進行審核,而其后續可否順利上市,或其最終可否獲得相對較好的估值水平,更需要緊盯當時的市場環境以及市場炒新的熱度。
對此,經歷一輪漫長而又復雜的過程之后,真正通過IPO發行得以回歸至A股市場的企業數量仍然是少之又少。在實際情況下,對于部分尚且達不到發行準入門檻的中概股企業,或許會暫時采取登陸新三板市場的方式,來完成其后續轉板的過渡。但是,對于部分本已具有一定市場規模的中概股企業來說,或許更熱衷于借助借殼上市的方式來實現短時間回歸的目的,但現階段隨著最嚴借殼新規的出爐,卻給部分中概股企業,尤其是那些已經完成私有化退市的中概股企業的回歸之路,帶來了不少的困擾。
顯然,對于中概股的回歸之路,仍然取決于政策與監管環境的寬松與否。時下,隨著證監會對中概股回歸政策的再度表態,實際上也傳遞出中概股回歸之路仍顯困難,而對于目前已經完成私有化退市的中概股企業而言,更是處于進退兩難的格局,或仍四處尋求盡快回歸的途徑。
其實,對于遠赴海外上市的中概股企業來說,上市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但其遠赴海外上市的風險與考驗卻大于其上市之后所帶來的實際機會。
一方面,中概股海外上市,實際可融資的規模很少,多數中概股企業的股票市值長期處于低估的狀態,無法真實反映出企業的真實價值狀況。由此一來,在企業估值過低,融資規模偏小的大環境下,卻會降低股票本身的投資吸引力,也對上市公司自身以及股票投資者帶來不利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在于海外過于成熟的市場環境以及高居不下的違規成本壓力,而在此期間,若上市公司涉及信息不透明、財務違規造假等行為,則容易觸發集體訴訟的風險,對企業的品牌形象無疑構成致命性的打擊。更有甚者,還需要時刻警惕做空資金借題發揮,擴大企業的負面壓力,讓上市公司自身承受著巨大的風險。
由此可見,近年來,中概股企業的回歸預期在持續地升溫,這往往體現出一種趨勢、一種方向,但更多還是體現出中概股企業的無奈之情。不過,在中概股企業回歸道路上,卻處處充滿考驗,而最終能夠真正意義上回歸至A股市場,且獲得超預期的市值擴張需求的中概股企業,又會有多少呢?